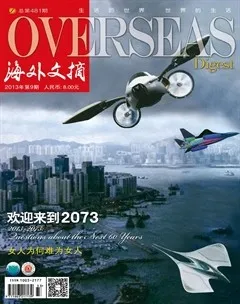走出家门,绊倒在历史之上
2013-12-29安德里亚斯·克鲁斯
2012年7月一个炙热的上午,麦纳什·福格尔携妻子和三个孩子从海边度假归来。回到柏林,驾车拐上班伯格大街,街道两边有很多古老的建筑,福格尔一家就住在这条街上。当他从车上卸载海滩上的休闲用具时,他的妻子和街道对面的一位老者攀谈起来。福格尔回忆说:“那个老人用英语和所有的路过者交谈,看起来有些神经质,可实际上他只是情绪太激动罢了。”于是,福格尔穿着人字拖也走了过去,聆听他们的对话。之后半个小时的交谈,改变了他与这条街道、这个城市以及它的历史和现在之间的关系。
那位老人名叫霍华德·沙特纳,来自加州,和福格尔一样,是一位犹太裔美国人。二战爆发前,沙特纳一家就住在班伯格大街3号。1938年,沙特纳的父亲和两个叔叔逃离德国,他的祖父和姑母留了下来。1942年9月,纳粹来到这里将他们强制带走。见到福格尔一家之前,老人沙特纳在班伯格大街3号的人行道上找到了纪念自己祖父和姑母的两块“碑石”(stumbling stone,英文中是“绊脚石”的意思)。它们是两块铜质的牌子,分别镶嵌在两块十公分的水泥板上。每块铜牌上都刻着一个大屠杀受害者的生命细节,不管他们是谁,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就是在这些铜牌所在的地点上度过的。上面的信息非常简洁,如沙特纳祖父的纪念牌上这样写着:
沙姆·沙特纳曾在这里居住
出生于1867年
1942年9月22日被强制运送至
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
1943年12月20日被杀害
一位美籍犹太人的经历
在遇到沙特纳之前,福格尔就在柏林各地发现过这样的纪念牌。柏林有很多纪念大屠杀的场馆和碑石,但对于福格尔来说,这些镶嵌在行人脚下的“绊脚石”,才使回忆更加真实、感人和可触。“纪念馆里的陈设早已让人麻木,但在这里,一个纪念牌代表一个具体的生命和他的家,你可以想象每个受害者曾经在此处的日常生活。”
一开始,福格尔还以为这些纪念牌是某个官方主持的公共工程(如今在欧洲,共计有四万块这样的“绊脚石”,大多位于德国),直到老人沙特纳告诉他,这些牌子全部是一位名叫君特·达姆尼希(Gunter Demnig)的艺术家的私人行为。福格尔说:“虽然柏林大街上已有不少这样的纪念牌,但如果真要让所有的受害者都被纪念到的话,把柏林街道全铺满都不够。我才意识到,原来有这么多受害者早已被我们遗忘!”
就这样,纪念牌激起了福格尔关于在德国居住的复杂情感。虽然是犹太人,但福格尔一家四代以前就在美国生活,所以并没有亲人在大屠杀中遇害。可他仍然是犹太人。现在福格尔不仅居住在德国,还在拜耳集团(Bayer)工作,在大屠杀期间,拜耳是法本化工厂(IG Farben)的一部分,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生产过齐克隆毒气(Zyklon B)。
不过,福格尔已不再为自己选择效力的公司而纠结。作为一名信息技术工作者,他倾向于理性和逻辑思维。“我的左脑凌驾在我的右脑之上,德国开诚布公地面对大屠杀的历史,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当代德国也在环境、治理、企业等各个领域取得了最为卓著的成绩。”
然而,历史依然存在于此处,沉淀在每一个地方。通过与老人沙特纳的交谈,福格尔意识到,安放一块纪念牌是一种承认现在与过去之间那种令人不安联系的积极方式。而这种方式又如此容易实现。对自己居住地发生好奇的外来者、第一次独立完成一份调查报告的小学生、大屠杀受害者幸存的亲属或者任何一个对那段历史感兴趣的人,都可以查查某个受害者身上发生的悲剧,然后将这些信息托付给艺术家,支付一笔小小的费用,就可以等待纪念牌的安装了——每一块纪念牌都由达姆尼希亲自安放,由于需求较大,往往要等六个月的时间。
但是,这一切又该如何开始呢?福格尔决定从自家的住址开始,探寻这里是否曾经居住过大屠杀受害者。他首先向自己的房东打听,后者的祖母就是被纳粹强制带走的。接着,福格尔开始查看地址薄、旧电话本、政府的数据库——各种信息不断堆砌起来,有价值的却不多。不过,福格尔说:“我绝非一个轻易言败的人。”
他比较了从1936年到1943年的地址簿。其中,任何一个用他家地址登记过的人,只要其姓名没有在次年的地址簿中出现,都有可能是受害者。然后,他再将这些名字录入专用以纪念大屠杀受害者的《联邦德国档案纪念册》中。通过这种调查,他发现了一个名叫马克斯·纳特尔斯基的人。
《纪念册》中列举了纳特尔斯基在柏林不同地方的居住地点。随着福格尔研究的一步步深入,一个家族的谱系图出现在他的电脑屏幕上——整个纳特尔斯基家族的受害者、幸存者和他们如今的后裔。最终,福格尔联系到一位名叫艾弗林·纳特尔斯基的女士,她真的是那位曾经生活在他的房子中的马克斯·纳特尔斯基的亲属之一。艾弗林的回忆使福格尔的追查霎时间鲜活起来。
福格尔说:“我现在知道了,马克斯是一个单身汉,有一辆白色汽车,和自己的兄弟一起经商,专为西装生产商供应布料;他有可能是同性恋,我现在的卧室很有可能当年也是他的卧室。”
达姆尼希的历程
达姆尼希将自己的工程称作“社会雕刻”。软呢帽和狩猎装的经典搭配让他看上去就像走下荧屏的印第安纳·琼斯。他说话的声音不大,甚至有些迟疑,仿佛总在探寻与思考。每一块纪念牌都在他的监管下手工制作。在他看来,任何大规模机器生产的形式都会使他想起纳粹分子在集中营进行的机械化谋杀。
达姆尼希出生于二战刚刚结束的1947年,他的父亲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虽然父亲从未向他谈及那场战争,但现在他明白父亲当时是站在法西斯独裁者弗朗哥一方的。对此,他深感不安,并通过反叛和艺术发泄自己的情绪。
1981年,他在伦敦的街道上用动物的血液画了一条宽4厘米、长达680公里的线,总计用了250升血液。1990年,正值纳粹第一次大批驱逐吉普赛人五十周年,达姆尼希推着自己设计的绘画车(轮子可以在路面作画),走遍了科隆,在人行道上印满了“1940年5月——1000个罗姆人和辛提人”的字样。可字迹颜色总会褪去,这时,他开始有了制作纪念牌的想法。
一开始,这个念头仅限于一种艺术构想,在达姆尼希看来,在整个欧洲镶嵌600万块纪念牌的想法近乎荒诞。后来,他与一位神父谈及此事,后者说:“你虽不能铺设600万块纪念牌,但是作为象征,你可以先从几块做起。”1996年,达姆尼希开始在柏林安装这些纪念牌。三个月后,他已经安装了51块。由于有些牌子恰好在一处政府工地上,引起当局的注意,想要移除这些纪念牌,但建筑工人们拒绝了这一要求。一些官员开始介入调查,达姆尼希的纪念牌最终被合法化。
不过,这些牌子总是伴随着各种争议。有时,他会遇到一些不愿被人强加那段回忆的房主。一些极右翼分子更是对此恨之入骨,达姆尼希已经收到过三次死亡威胁。即便那些愿意回忆这段历史的人,也有人不赞同这种纪念逝者的方式,认为让受害者的名字被踩在行人脚下,缺少对死者的尊重。有人建议达姆尼希将这些牌子嵌在墙上,但他从来都不赞同这一建议。首先,这需要获得每个房东的同意,让过程更加麻烦。其次,他觉得走路时,人们不一定会留意那些嵌在墙上的牌子,但低头看看脚下却是经常发生的动作。
关于踩踏这些姓名牌,达姆尼希的看法是:“踩得越多,对死者的敬意也就越多。”他最初的想法是,通过踩踏,行人的脚步将不断打磨这些铜质的纪念牌,让它们更加光滑鲜亮。谁知结果正好相反,出于对它们的敬意,人们往往绕过这些牌子行走。这使得这些金属物不断氧化,光泽不断暗淡,看起来仿佛无人问津。不过,一些住户会不时走出家门擦拭它们。一位女士就常在居住街道的纪念牌上点燃蜡烛,在上面放朵白色的玫瑰。
在不经意间与这些纪念物相遇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其中一位15岁男孩的话在达姆尼希看来最为精彩:“在踩上它们的那一刻,我们不是脚被绊住了,而是心灵和思想被绊住了。”对于这些孩子而言,没有什么比每天在自己行走的道路上踩过受害者的名字更能使大屠杀的历史具体化,这是常规教育无法做到的。另外,达姆尼希说:“最妙的是,当你想要阅读这些纪念牌上的文字时,你不得不为逝者弯下腰来。有时,我往窗外望去,看到的正是行人们在垂首阅读纪念牌上文字的情形,那是最美的画面。”
跨越沟壑的纽带
当沙特纳的石头抵达班伯格大街的时候,达姆尼希正在国外安装纪念牌,他的两个学徒前来完成镶嵌工作。沙特纳情不自禁地拿起锤子,和他们一起劳动起来。达姆尼希回到柏林后,沙特纳追随了他数日,手持摄像机,记录下他们的工作。
“通过上个夏天的经历,我完全改变了对德国的看法。”沙特纳说,“那里的人们友好而又乐于助人。一方面,我怀有这样的幻想——在轻轨上随便碰到的一个德国人在另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可能会杀死我。而另一方面,我又发现和普通德国人的相处能愈合历史的创伤。有一次,一整栋楼房的全体住户行动起来,资助安放一块纪念牌。和这群德国人的交谈是我最感动的时刻之一,他们和被纪念的逝者没有丝毫关系——除了他曾在此居住。人们以发自内心的热情来做这件事,令我感触甚深。”当时,沙特纳挨个紧紧拥抱了这些人。德国人本不善和陌生人有身体接触,可这些拥抱却来得如此自然。
由此,这也见证了这些“绊脚石”搭起的另一架桥梁:它们不仅在居民和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之间、在学童和他们祖先的历史之间(他们的祖先酿成了这段历史,而现在他们却不知如何理解),也不仅在寻常的行人之间(他们会在此驻足沉思,开始一段对话),还在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关联。
“作为一个在柏林生活的犹太人”,福格尔说,“我觉得应该在私人的层面上去理解大屠杀的历史。没有什么能比与那些死难者分享同一个生活空间更为私密和个人。”他的追查现在已近尾声,很快就能看到由自己资助的那块纪念牌安放在自家门前。那上面会写着:
马克斯·纳特尔斯基曾在这里居住
出生于1888年
1942年8月15日被强制运送至
里加
1943年8月18日被杀害
[译自英国《智慧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