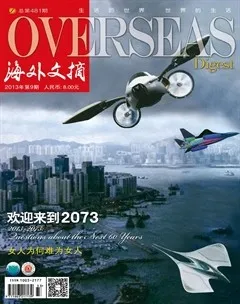该死的美国日托
2013-12-29乔纳森·柯亨
现在是早上5:30,肯尼娅·麦尔俯下身来,看着在婴儿床上熟睡的宝贝女儿肯迪尔。20个月大的她刚能说清楚一个个单独的词,比如,对着身边的布娃娃喊“宝贝”。小肯迪尔昨晚睡得不好,麦尔很想打电话给公司,说自己晚一点上班,好让女儿多睡会儿。但这天是麦尔开始新工作的第二天,她迫切需要这份工作(休斯敦一家石油公司的接待员),不能给公司留下不好的印象。于是,她能做的,只能是轻手轻脚地洗漱、准备早餐,让女儿多睡一分钟是一分钟。
6点半时,麦尔总算把肯迪尔哄骗起床,为她穿上紫色小衫——紫色是女儿最喜爱的颜色,再把一条紫色条纹弹力裤放进背包备用。一通忙碌过后,早上7点,她们坐上车,前往麦尔新近找到的一家照看肯迪尔的日间托儿所。
那地方名叫”杰基托儿所”,经营者是一个名叫杰西卡·塔塔的22岁姑娘。从经营证件上的注册信息来看,她是德克萨斯州人。日托所是一幢木质房子,位于安静平和、具有中产阶级人文气息的街区。常在这里被照看的小孩包括伊莱亚斯,一个矮胖的小孩,16个月大,走路时腿还站不直;还有19个月大的伊丽莎白,当妈妈要放下她离开时,她总是又跳上妈妈的腿。2011年2月那个温暖的早晨,当麦尔回到车上时,她注意到肯迪尔在日托所门口徘徊不前——看起来有点睡眼惺忪,还有点好奇,向日托所里面张望。对于自己的离开,麦尔有点不安,这仅是肯迪尔来这家日托所的第二天,她对塔塔还不太了解。过了一会儿,麦尔打电话给塔塔,确认孩子是否安好,塔塔向她保证平安无事。
午饭刚过,麦尔的手机响了,是塔塔打来的,她紧张的说:“发生了火灾,所有孩子都被送到了医院,检查他们是否吸入太多烟尘。” 麦尔尽量让自己镇静,告诉自己没事的,送去医院只是为了“检查”而已。手机又响了,这次是朋友发的短信:“之前你说肯迪尔去了哪个托儿所?” 麦尔立刻打电话过去,后者正在观看休斯敦托儿所的火灾电视直播。窗户和屋顶的通风孔冒出滚滚黑烟;消防员怀里抱着瘫软的孩子,从房子里冲出。麦尔的朋友说,其中一个小女孩梳着麻花辫、穿着紫色小衫,看起来像肯迪尔。麦尔冲向汽车,不断告诫自己:别惊慌,不会有事的。
最近几十年来,在美国,尽管工作和家庭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切实的儿童保健体系仍不完备。当然,如果你有足够的钱来支付费用,并有幸找到合适的托儿所,那么孩子会安全些。但总体说来,托儿所的资质参差不齐、缺乏监控,条件简陋,堪比狄更斯笔下的悲惨时代。
麦尔之前曾把肯迪尔送去一家名叫“奶奶之家”的育儿中心,那里整洁亮丽、环境温馨,并有专业人员照料,但收费昂贵。由于经济不景气,麦尔丢掉了工作,不得不把肯迪尔从育儿中心接回来。应聘到石油公司上班后,为了工作,麦尔必须把肯迪尔送去托儿所。她联系了十几间育儿中心,所有地方不是太贵,就是没有空名额。
接着,解决方案出现了。麦尔的妈妈在塔吉特百货商场购物时,一位名叫杰西卡·塔塔的女人递上名片,介绍自己的日托所。为了打动麦尔,塔塔承诺会通过读《圣经》和祈祷的方式,教给孩子们基督教的价值观,麦尔对此颇感欣慰。最重要的是,塔塔似乎很喜欢孩子。
令麦尔进退维谷的困境曾经让几代美国家长(尤其是单身母亲)苦苦纠结。一直以来,美国社会极不情愿让孩子离开家庭、到外面受教育,究其原因,不得不追溯到美国人对女性和母亲双重角色的理解上来。组织完善的日托体制从未被视为一种社会理想。
直到二战爆发,当时,由于男性当兵参战,女性进入社会,填补劳动力的空缺。女性外出工作首次得到了社会认可,或者说至少被接纳。但其中许多妇女无法离开年幼的孩子。她们采取了孤注一掷的措施——将车停在厂区停车场,把小孩锁在车里,车窗打开,用毯子盖住后座。只有在这种时刻,幼儿的保育问题才在美国政坛成为国家的当务之急。1940年,国会通过了《兰哈姆法案》,以政府为中心,建立起育儿中心体制,为各收入阶层家庭的10多万儿童提供服务。
但立法委员只是将育儿中心视为战时应急机制,因为如果日托能让妇女继续在工厂上班,退伍军人便难以找到工作。因此战争结束后,《兰哈姆法》失效。
20世纪60年代,一项旨在帮助职业女性,为所有有需求的孩子提供保育服务的法案在美国国会通过。但尼克松总统否决了该法案,他说,不希望政府插手 “公共”保育活动。过去几十年间,除了增加儿童抵税额和补贴之外,美国联邦政府的育儿政策几乎一成不变。
但是,美国人的家庭生活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约有三分之二的年轻母亲在外工作。
起火那天,房间中浓烟四起,杰西卡·塔塔拨打911报警。在电话录音里,她尖声喊叫:“孩子们快死了,我什么都看不见,甚至找不到他们。请赶快过来,我的天哪!”
塔塔在休斯敦西区一个并不富裕的尼日利亚裔家庭长大,16岁时,她成了一名基督徒,并开始在教堂里志愿提供日托服务。2010年,塔塔扩大经营规模,开办了杰基托儿所。
第一批救援者到达现场时,塔塔告诉他们,起火时她正在盥洗室,找不到任何孩子后,她只有自己跑了出来。一名邻居试图安慰悲痛欲绝的塔塔,却注意到消防员和抱出来的孩子们浑身黑灰,可塔塔的白衬衫、樱桃红马甲和配套的针织贝雷帽却一尘不染。还有邻居表示,那天中午,有人看到塔塔开车从外面回来。稍后,一名消防部门的调查员从门后发现塔吉特超市的购物袋,购物发票开具时间在火灾发生前不久。
事发第二晚,塔塔返回满目废墟的家中,翻出护照,坐上飞往尼日利亚的航班,但最终还是被国际刑警组织的特工抓获。
25分钟后,肯尼娅·麦尔赶到医院,现场一片混乱。家长们焦急地打听消息,但工作人员无法立刻确认所有孩子的身份。随后一名护士来到等候区,手里拿着一条紫色条纹弹力裤,裤子上满是烟灰,已碎成布条。麦尔几乎是被搀进了急诊室,进到房间,看见肯迪尔像洋娃娃一样平躺在桌子上,一名医生正在用力按压她的胸部。接着一名护士把麦尔拉到一边,告诉她,他们已经尽力了。
那天在托儿所的七个小孩中,四个不治身亡。小伊丽莎白在妈妈赶到医院之前就离世了,她的妈妈贝蒂·卡约是一位老师,通过教堂活动认识了塔塔。伊莱亚斯被送到特殊呼吸室,以排出肺部的烟雾。当时,他的妈妈凯夏·布朗刚结束杂货店新职位的培训,才听说托儿所着火的消息。第二天,伊莱亚斯死在妈妈怀里。
蒂凡尼·迪克森的两个孩子都在塔塔的托儿所:两岁的马卡亚和三岁的索马利。蒂凡尼是休斯顿西部医疗中心的护士助理。那天午饭后不久,她从对讲机里听到了消息:“紧急救助,P.D.,P.D.”——P.D.是儿科的简写。蒂凡尼当时还一无所知,直到数分钟后她给托儿所打去电话,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上帝啊!蒂凡尼,你的孩子在急诊室!”同事告诉她。马卡亚死里逃生,索马利则不幸身亡。
在许多国家,托儿所的管理一般被视为重中之重,而非事故发生后才亡羊补牢。比如在法国有一整套国家体系规范,值得效仿。婴儿和蹒跚学步的小孩可送到托儿所,它属于公众卫生体系的一部分。学龄前儿童可以送到幼儿园,而这属于公众教育体系。在托儿所,至少一半的看护人员是从儿童保育或者心理学相关专业毕业,而且有儿科医生和心理医生随时待命。总体而言,法国政府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用于儿童保育,是美国的两倍多。
在2012年7月的一次讲话中,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说,在儿童生长初期进行大规模投入,将使美国经济获得更大收益。今年,奥巴马总统提出“学前儿童教育”的议案,为每个州提供配套资金,便于各州为3、4岁的儿童建立相应机制,同时,适度为婴儿和学步儿童加大政府补贴。这项计划将在十年内耗资750亿美元,这笔钱将通过提高香烟税来获取,这意味着它将面临无比严峻的政治阻力。
自19世纪30年代社会保险诞生以来,美国已经经过进展缓慢、杂乱无章的过程,伴随着痛苦,逐渐建立起一套福利体系。儿童保育事业是该项目中尚未完成的主要部分。可以说,缺乏质量高、价格合理的日托所已成为美国女性在工作场所实现完全平等的最大障碍,并很可能使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永远无法获得出头之日。这也是其他发达国家很久以前就把儿童保育作为集体责任的原因。
2012年11月,塔塔被控犯有包括重大谋杀罪在内的多项罪名而出庭受审。她的家人和一些老顾客纷纷出面证明她对孩子们的疼爱。一个名叫尤朵拉·沃尔科特的护士称,塔塔是一流的看护人员,可以让小孩子停止尖叫,“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她是总为孩子们着想的一个。”但是,一位2010年曾与塔塔短暂共事的年轻女士作证称,塔塔有时会让她一个人照看一大群小孩长达数小时,有时她早上来到托儿所上班,发现尿布扔得满屋子都是。一位邻居说,她曾有几次敲塔塔家的门,无人回应,却能听到里面有孩子的响动。
检察官调出了火灾前在塔吉特超市拍到的监控录像,画面显示,塔塔在超市逛了逛,接着进了一家星巴克咖啡店。店里经理作证称,他请塔塔接受一项顾客调查,但她说没时间,因为家里的火炉上还煮着东西,孩子们还在睡觉。
塔塔的代理律师麦克·德格瑞并没有否认她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的行为,他称,虽然塔塔犯有判断失误罪,但她没有蓄意伤害任何人。“这是一起严重的意外事件”,德格瑞告诉法庭,“而不是谋杀事件。”第二天,陪审团判决塔塔有罪。现在,她在州立监狱服刑,刑期为80年。
[译自美国《新共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