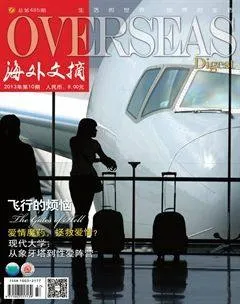沙之魔力
2013-12-29瑞贝卡·威利斯
合上眼,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你漫步在蓝天阳光之下,身体一侧椰树婆娑绿意盎然,另一边是蔚蓝的大海,而赤脚之下则是沙子,洁白的沙子——细滑如丝,柔软亦且牢固——踩上去时会下陷,继而又将你紧紧包裹。一种感官上的刺激从脚到头直涌而上。
现在换一幅画面。将你脚下的沙子换做砾石,让它变得粗糙些,锋利些。找不到感觉了,是吗?原来,美景的关键是沙子。即使周遭的色彩不那么亮丽,哪怕右侧的椰林换成了峭壁嶙峋,左边的海水色青如钢,你脚下的沙子依然会令你想要脱去鞋子,将脚趾探入其中。
自《鲁滨逊漂流记》问世至今三百年来,人类心目中的海滩已是沧海桑田。彼时,海滩还是一处杀机四伏、令人生畏的不毛之地,危险性仅次于茫茫未知的海洋。海滩上遍布着遇难船只的残骸,海盗时常出没,渔民不得安生。而如今,海滩却成了人们趋之若鹜的圣地,在旅游业者眼中更是闪耀着黄金的光芒。不知是巧合还是刻意,总之越是美丽的沙滩,就越是遥远,越需要耗费精力与金钱才能到达。于是无数有钱人甘愿忍受长途飞行之苦,不远千里而来,只为与沙子亲密接触。这就是现代人类社会的特点,我们想要的东西,或者说被鼓动起来的欲望,总是与金钱不离左右。
银白的海沙或许是最为人们喜爱的,但其实,任何色彩的沙子都会触动你我的感官;我们想触摸它、塑造它、把玩它。依据伍登-温特华斯粒级划分标准,直径为0.0625-2毫米的被称为沙,直径更大的物质是砂砾,直径更小的则是淤泥。由于该标准适用于所有颗粒物质,这就意味着,从技术层面而言,盐和糖都属于沙粒。想想看,如果海滩是由食糖铺就而成的,现代人会多么欣喜若狂!
在地球上所有的颗粒物质中,沙在水中的流动性最好。泥浆太黏稠,石头则太重,只有沙才是颗粒家族中的旅行者,随波逐浪,御风而行。而且,与旅行者一样,沙也有满肚子故事要讲。这种通常远离发源地的矿物大有神通,可以协助人们找出罪犯的蛛丝马迹。沙粒的形状表明了它的由来路径——沙漠中的沙比水中沙更圆,因为后者沉积在水底。沙还能提供年代数据:对于无法借助碳测法断定年代的考古发现来说,利用照射或断代措施,根据沙子所受辐射量的多少即可得出结论。例如在澳大利亚,人们采用上述方法,测定出洞穴壁画的历史长达六万年,是现存最古老的人类图像。
世界各地不乏喜好收集沙子的人,因为沙子的确可爱,它具有一种特殊属性——自分类性:同样大小的沙子会自动聚集在一起,这样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沙子跟随潮汐涌上海滩后,会排列出色彩各异、精致纷呈的图案。干燥的沙粒好似液体,走在上面的感觉犹如穿行于水中;可一旦被打湿,沙子又能变成坚硬的固体。而且,一旦陷入其中,多种物质会毫无例外地也变成沙粒——在诺曼底登陆的发生地诺曼底海滩上,可以找到大量与沙子大小相当的钢铁碎片。
在全球沙子总量中,建筑用沙以及海滩沙(热带海滩除外)约占七成,它们由石英构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硅,经历数百万年的冲刷及冰蚀后研磨和风化而成。热带海滩的沙子则截然不同。它们属于“生物制品”,或曰生命过程的产物,主要成分是碳酸钙,是贝壳、珊瑚和海洋生物骨骼遗骸的聚集物(众所周知,鹦嘴鱼被称为“制沙机”,因为它吃下珊瑚,排出沙子)。沙子的颜色为什么有差异,从中可以得到简单的解释,所以说,即使同样受到太阳照射,英吉利海峡的沙子也不可能像旅游手册中的热带沙滩那样,呈现出银白色。

别小看那些细沙,海滩上的微观生命着实令人震惊,细沙之间生活着多种微型无脊椎动物。毫不夸张地说,在海滩上,捧起一把湿漉漉的沙子,就如同擎着一座迷你动物园,沙粒间生物的多样性甚至胜过了雨林。这些小动物维持着海滩的生态系统,让坏细菌不至于泛滥成灾、臭味熏天。
有些人不满足于让沙子从指间渗落。到怀特岛的阿勒姆湾,或内盖夫沙漠的游客可以买到一罐罐的沙,里面的沙子层次分明、颜色多样。作为一种嗜好,铁杆“沙迷”会收集不同外观的沙子,或者加入国际沙子收藏家协会。不过再爱沙的人,也不愿看到有些地方进了沙:鞋里,眼里,床上(无论你打算在上面做什么)。
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伦敦的摄政公园,游乐场上一派喧嚣。孩子们忙着爬上攀登架、在单杠上悠来荡去、溜下滑梯,兴奋地大声喊叫。但在沙堆附近,却是另一幅景象。他们安安静静、聚精会神,把小桶装满沙子,再倒出来,堆成巨大的沙堆,垒砌城堡,挖掘地道,时不时地,有个把孩子发觉扔沙子很有趣,这时,一位家长会走上前来加以制止。但总体而言,一切都在平静中进行。
幼教专家认为,沙子对孩子的情绪有舒缓作用。水也有同样的效果,与所有色彩艳丽的塑料玩具相比,天然材料更能让孩子安静下来。孩子们喜欢探索沙子的特性,在这个年龄段,玩和学本来就是一码事。玩沙子是开放式的,不设定目标,所以,孩子会更有信心。
在海边,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场面:一家人花上几个钟头,全神贯注地堆砌沙堡、沙坝,或挖坑,又或者把沙子堆到某个人的脖颈上“活埋”他。在一些旅游胜地,还会有组织地引领人们玩沙,例如举办沙雕比赛,将城堡垒得和房子一般高。
沙子也能用于治疗。沙盘疗法运用了荣格的无意识理论,让患者在沙盘中创作一幅画,以影射其内心世界。治疗师会在桌子上摆两盘沙,一盘干的,一盘湿的,患者可以随意选择作画。治疗师在一旁观看,如果患者愿意也可以进行交谈,但不是非得交谈不可。许多病人得到过这种疗法的帮助,从深受婚姻问题困扰的成人,到在意外事故中受伤的孩子。沙子能直接作用于人的潜意识。你可以塑造它,往里加水,用它构筑东西。它使人感到放松、自由。
在沙滩上漫步会感觉很自然。出生时我们就光着脚,而我们的祖先也并不穿鞋,更没有平整的马路可供行走。从生物力学的角度来说,走在柔软干爽的沙粒上好处多多,因为它不会向我们的骨骼发送冲击波,是地面在迎合我们脚部的角度,而不是相反。当我们行走的时候,沙子也在按摩我们的脚部,还可以去角质。
浪漫的人喜欢在海滩上与大自然交融一体,就像他们爱在有山有水有瀑布的地方,从各个层面,体会令人敬畏的自然世界。印象派画家也被热闹的人潮和闪烁的灯火所吸引,来到海滩,布丹、马奈等大师纷纷毗邻大海安营扎寨,与微风为友,在遮阳伞和海边小屋的掩映下,面向连绵不绝的乳白色余晖,恣意挥洒才情。
对于聚集在城市的工人而言,工业革命和蒸汽机的发明提供了前往海边度假的交通手段。在维多利亚时代,为普通人而建的度假村风生水起,配备了华丽的酒店、赌场和漂亮的明信片,托马斯·库克(注:英国现代旅游业创始人)开始组织周末短途旅行。
人们的泳衣也越做越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维多利亚时代的最后一丝余韵在水中飘然远去,社会的变化已不可逆转。1920年代早期,到海滩上玩耍更成为医治战争创伤的解药,中午日头最高的时候海滩上挤满了人,数不清的脚丫子翻动着每寸细致柔滑的沙子,不同国籍的人们躺在上面,身上被太阳晒出了泡。延续至今的海滩阳光浴文化就此拉开序幕——尽管现在有了更多的健康警示。
在沙漠里,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沙丘永远在随风移动,一场沙暴能吞噬整个村庄;地球也许是固态的,但地表的一层总在移动。岩石侵蚀而成的沙粒被降雨和河流裹挟着涌向海洋,沉积在大陆架上,并随时间、潮汐、风和水流形成沙洲、堰洲岛和海滩……人类总希望沙子臣服于自己的意志,可沙子还是像“星期四出生的小孩”,它会走得很远很远(注:英谚中,星期四出生的孩子要离家远行,这种说法在英语国家中流传广泛)。
正是由于沙子流动、短暂与多变的性质,使它充满了象征意义。我们知道,是亿万年的风雨磨砺造就了它的细微与光滑,经历了亘古久远的地质年代它才得以呈现,这一点纵使山高如许,也难做到。因此,所谓“时间之沙”并不只是一种隐喻,而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沙漏最初出现在14世纪,以沙粒的流动昭示时间的流逝,被用于在航行期间推算航位:在绳上每间隔一段打上一个结,将绳投入海中,当30秒沙漏里的沙子流尽时,海水冲走了多少个绳节,就说明船速是多少“节”。此外——不同于后来取代它的各种计时器——由于沙漏衡量的是一个时间段,一段短暂的生命,所以很快成为死亡的象征。作为死亡的符号,沙漏出现在了墓碑上,有时,甚至与去世的主人一同被放进棺材里。
大多数人都知道,沙子是由岩石风化而来,但是,沙子还能变回成为石头,这一点却鲜为人知。它们可能经过积累、埋藏,自然而然地粘在一起,岩化成为一块沙岩。当这种过程完成后,沙岩暴露出地表,受到风雨侵蚀,沙粒又会离析出来,重获自由。整个过程循环往复,无休无止。据估计,地球上所有石英沙粒中,半数已经经历了六次(从沙到岩石,再从岩石到沙)这样的轮回。
地球的真实年龄很难计算,但对我来说,沙的六次轮回远比讲什么千年万代都更容易理解。岩化与离析构成了地球上生命的循环,不是尘归尘,而是沙变沙。1803年前后,当英国著名诗人威廉·布莱克写下“一沙一世界”这样的诗句时,也许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有多么接近真理。
[译自英国《智慧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