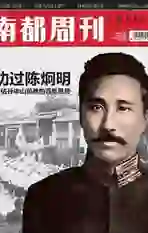骆以军:文学的中原时间
2013-12-29黄修毅魏晗宇

台湾作家。作品以小说为主,代表作有《底片》、《红字团》、《第三个舞者》等,曾获联合文学巡回文艺营创作奖小说奖首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推荐奖、时报文学奖小说首奖等。
台北大学城一带盘曲的小巷里,酒肆咖啡馆隐没其间。与骆以军的相会就约在这样一家咖啡馆,距他的住处不远。
赶至之时,茄苳树下的茶座,只剩烟灰缸里几根刚刚掐灭的烟头,服务员柔声细语地让“稍待”。果不出半分钟,小巷里影影绰绰闪出一只胖子,手里多出了一包新启封的香烟。去年八月的一次小中风,让他看起来还经不起剧烈的腾挪。
但话一启口,滔滔雄辩像额角层层渗出的汗珠,细密澎湃,思辨之灵活让人惊诧于和这尊略显笨重的身体形成的反差。作家回到了他笔下那个骆以军,严谨的逻辑在中气十足的长句裹挟之下,以一种客观但非冷感、宏大却又轻盈的方式吐露出来。
正如在大陆引进他的作品时所标榜的,“台湾作家六年级生的带头大哥”,骆以军繁复到有些呛人的文风,好像昭示着文字游戏的“更新换代”。而老练的文学读者,仍能从他的文字里,嗅出朱天心那几个“第二人称”小中篇,或是张大春早期短篇的味道。他自己对此也并不讳言。
让他错愕的是,五年前游历北京中国文学馆时的见闻。底层大厅里,陈列的是“郭鲁茅巴老曹”,他戏称为“共和国开国的北斗七星”;到了二楼的细分展馆,终于在一个非常狭促的柜子里,找着了“港台澳文学”。陈列品里只见陈映真、黄春明,连张大春都没有。
生活在大陆之外的中文作家被插上“地域化”标签,他们的书写隔着“身份”的滤光镜才得以窥视。这让骆以军这样一个台湾的“外省二代”(父母从大陆迁居台湾)感到近乎本能地不适。他们因此被文学版图的主流排向“边缘”的位置,后者更在不可见的某处深刻地左右着两岸的文学写作,骆以军谑称之为“硬调出一个文学的中原时间”。
在台湾绵延六十年的战后现代文学书写中,代际的传承与突围,已成了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前辈作家对新人的关注、筛选和提携,是约定俗成的。和骆以军同辈的黄国俊、袁哲生等人“出道”,当年都须过张大春这一关。
现如今,骆以军又被自然添加进各项文学奖的评审名单,对更小一辈的七零后作家创作动向,他都如数家珍。他更愿意把书写的游戏看作一场世代绵延的无国界篮球比赛,“就算自己打得烂,也想和一帮高手同场竞技,好像跟马尔克斯、昆德拉什么的,斗斗技”。
说到动情处,骆以军那双被朱天心形容为“核爆似的巨眼”,腾起层层云雾,对烟灰的明灭掉落也无所察觉。
南都周刊 骆以军
大陆硬把文艺拉进领导班子
南都周刊:在北京中国文学馆一游,让你吃惊的是什么?
骆以军:大陆有个问题就是官员没文化,在设立这样的项目时只能找被认定是作家的人。还有比方在搭建平台、设立两岸作家对话的时候,不管是出于市场还是个人文学趣味上的考虑,首先考虑到的是所谓够重量级的人物,现在大陆出来就是莫言、王安忆、余华,台湾就一定是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
其实比方说,张贵兴在华语文学界有极大贡献,可他是马来西亚华人。作品真正重量级,并且可以上溯到五四传统,应和整个中文的剧烈变化,可以和莫言、余华、韩少功、张大春、天文、天心等并行讨论的“马华”,一般是三个: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他们的中文文字教养可能比大部分中国作家还要好。他们三个又有不一样的同心圆,李永平是老华侨,最认同“自由中国”。张贵兴用华文书写的诸如《猴杯》、《群像》,类似康拉德的东西,是想在蛮荒中找到一个古代中国的神话。
南都周刊:这种文学版图认知的差异,是不是大陆、台湾与马来西亚的现代中文语境的差异造成的?
骆以军:其实我期待的是城市和城市,比如北京和台北、上海的文学互动。比如说到台湾的“乡土小说”,那你必须非常耐烦与愿意接受这六十多年来台湾社会的物种演化,才找得到密码读进去。但像韩松的科幻,主要是刻画官僚体制的黑暗面,可以与香港作家董启章的《天工开物》和《时间繁史》放在一个语境里解读。王德威就很聪明,把它们拉回到20世纪初的启蒙小说、晚清科幻小说的系谱里。这样解读下来,就可以感觉到族群认同与历史不同的照应,无论你北京、台北还是上海,都可以谈得起来。
就像英国的大本钟硬要调一个中原标准时间,文学史也是,偌大的地方,莫言、王安忆、余华这几个都是天才,可他们最后还是被调教成同样的时间。我们期待这个国度能够更有自信或者说愿意把它内部的时钟调成不同,但这太难了,因为存在所谓国度内外的概念。像余华、格非这都是因此而变动比较剧烈的作家。阿城就很聪明,他知道在这个国度里面,你想要当马尔克斯是不可能的,很清醒地开始控古物 (玩古董)。现在大陆的一系列微妙的东西,反而可以从清代的奏折里面看清话语应该怎样协商、怎样交涉。而这一整套本来也是西方新历史主义移来的。
南都周刊:西方现代主义对大陆、台湾的中文写作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是不是跟引介输入的时差有关?
骆以军:张大春的后现代性质以及嬉耍方式,和莫言他们不一样。他不是在讲一个魔幻故事,他把《百年孤独》变成了一个个体的东西,父亲和儿子都挤在时间感里面形成的暴力,在那时几乎垄断整个台湾文坛。朱天文、朱天心之所以后来能和张大春平起平坐,是因为她们的文学底子深厚,又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姐妹在语言上把握着复杂性。
台湾那时就是家国覆灭,文学上进行各式各样的实验。后来的十年台湾产生了一个变化,本土化的论述在建构,这个过程中张大春等人都逐渐退居二线。之前在台湾,不同的痛苦和对抗一直存在。印度、阿拉伯、拉美的小说家都是非常痛苦地去处理这个过程的,表面上还是谈我的殖民母国的大传统,但事实上是在扭造过程。我们有真正发生这400年的事,这一空间里所有的暴力和伤害,其实和西方发展的现代主义小说的概念是相通的,都是用现代技术处理当下百年的历史。
南都周刊:很多文学史论家注意到,就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生的这批作家而言,大陆中断了的现实主义传统反而在台湾得到了继承?
骆以军:有一次和香港的老前辈吃饭,他们讲到一个共同经验就是,关于阎连科写的“三反”“五反”、大跃进、大饥荒的作品,都是真正在五十五到六十岁上下的人的记忆里活着的,讲出来是带有丰沛感情的,而且是有气味有颜色的。其实在台湾同样的,大春、天文、天心、苏伟贞他们在一起时,谈论的是洪范、尔雅这些上一辈的小杂志,或是解严前台湾一些很棒的媒体带来的共同回忆。但这些现在都断掉了。
大陆比台湾更重视“人民文学”,硬把文艺拉进领导班子,但在台湾你不会想到张大春、朱天心有一天会变成省长。大陆现在这些大作家又刚好存在于国际上的“中国热”中,国际上想看“文革”、“毛中国”,那他们也就会回去写那个年代的心态。台湾其实在不那么小说的世界里面,所谓的文体通常是杂种式的,这跟日常生活,跟你每天在咖啡屋的聊天或是课堂上学院内的讨论,再或者是媒体网络充实你的脑袋有关。
南都周刊:你现在是否还紧盯西方现代作家的写作?
骆以军:用黄锦树的话来讲,你不要小看那些西方的大哲学家大作家所达到的高度。我是很认同的,就像我最近在看维勒贝克。鉴于维勒贝克是20世纪末的小说家,很多东西让我们开眼了,不管是泰国嫖妓、国际色情、嬉皮的杂交派对或是科幻。其实在维勒贝克的东西里,很大的把人撕扯掉的、让人变得很脆弱或是失重的力量,是全球化的结果。但卡夫卡的文字里还有非常沉郁的国家对个体的剥夺和剥夺背后故意的荒虐,这是一个共享时差的事。八十年代我还觉得这个状况非常好,可现在大陆的控管更专业,把这个时钟一直在调,我觉得这很可惜。站在国家的立场,这是非常浪费一个文明本来更复杂的题材的。
南都周刊:用西方现代主义技巧写当下,是否会跟现在的读者脱节?
骆以军:很多拉美或者莫言那个时代的小说,现在看来并不稀奇,那个年代需要。大陆除了内部监控外,还有一个就是集体疯狂,几乎身边没有一个人类是可以信任的。我们必须要英国式的传统,我有一个咆哮山庄,我有一个教养、阶级、贵族,文学是这个贵族形成的升值游戏。但中国大陆没有这种土壤。如果五十年后大陆完全开放,你也许读《四书》会感到文学的力量是薄弱的,但现在你会给它加上很多附加值。在台湾很多本土派作家的作品,在当时都是对抗国民党的,但他们本身没有足够的东西去转化,这都是需要几代人的事。
南都周刊:当下台湾年轻作家的生存状况如何?
骆以军:台湾这十五年的翻译书是市场大书,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翻译书不是这么爆炸式地热卖。比如在国外谈一个作家的版权,国际的基本喊价并没有那么高,但经纪人会发觉喊价最高的两三家出版社都是台湾来的。他们互相喊价,而其实那些书很多都是B级书、二流货,以致于市场上多是这一类书,这就把本土作家全都排挤到只剩两三家会出。因为现在是买方市场,即使是最好的创作者,出版社也可以开很便宜的版税,这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