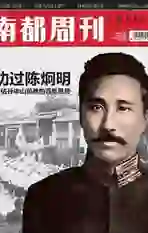科幻与现实,不忍细看的落差
2013-12-29廖伟棠
那天看见我关注的科幻作家韩松在微博上说:“明天就要去涞源,希望工程发源地。要给小学生讲科幻。纠结了一天也不知怎讲……近年涞源希望小学学生去广州,对广州孩子一日三餐不理解,因他们只吃一顿。前年有北京人去涞源学校在食堂吃饭,孩子们都回家吃了。问为什么,答因你们来了,提高到一人三元标准,孩子们吃不起。”
读罢我和韩松说:“你只能讲刘慈欣的《乡村教师》了。”科幻与现实的落差,没有比在中国更大的。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粤西农村读小学,看到一本描绘日本的连环图,画了摩天大楼、玻璃幕墙、小型飞机穿梭,我以为那就是科幻小说里讲的未来世界。长大才知道,那是同时代现实存在的日本。后来我更知道了一个与我的幻想相类似的情节:苏联大导演塔科夫斯基拍摄他唯一的一部科幻电影《飞向太空》,那些未来的场景直接在日本城市取景,不用特技,毫无违和感,骗倒了一批生活在苏联的观众。今天涞源希望小学的孩子,如果看一部珠光宝气的《小时代》,也会怀疑自己在看科幻片吧?如此极端的生存状况,怎么可能发生在同一个时代?
好吧,我说的是苏联而已,一个号称美好新世界的国家,率先进行宇宙探索,比美国还要早把宇航员送上太空的先进大国,它的国民不知道电影里的未来实际上早已在他们批判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实现了,在翘首期盼未来的同时,还要依配给制每天冒雪排队买一块黑面包。我没有去过涞源,这个位于河北历史悠久的山区县,百度对它的介绍网页没有一个字提到贫穷,尽是各种辉煌往事与招商开发旅游等等。然而一位网友在给韩松的微博留言道:“图片上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涞源的人民,冬季用麦秸烧土豆一天一顿,条件好的加点自腌制的酸菜,唯一的粮食是高粱面,吃不习惯的会拉破嗓子。”
从韩松的配图可见,这些涞源的孩子起码还能上学,有课桌,有微笑。毕竟那是一个希望小学,网上寻找一下“贫困山区教育”,比这凄惨得多的学校有的是,有老师带领攀缘绝壁翻山上学的,有吊绳溜滑轮渡江上学的,有坐在石头轱辘上课的,有全班有桌无凳站着听讲的,那些寄宿学生生火做面糊糊当饭—不必描述下去了,更细腻的描写就存在于中国科幻大家刘慈欣的短篇名作《乡村教师》里面,读之使人鼻酸。
写于2000年的《乡村教师》是刘慈欣最特别的一篇科幻小说,在“作者附言”里刘慈欣说:“我不敢说它的水准高到哪里去,从中你将看到中国科幻史上最离奇最不可思议的意境”。“意境”二字令人有点难受,这部小说就文笔、构思而论,意境的确高超,非常现实主义,但相较它内容的沉重和悲悯,意境不算什么。
因为这部科幻开篇是我们最贫瘠的现实,在西北山村里,一个乡村教师走到了生命尽头,他强撑病体给孩子们上的最后一课,是讲述牛顿的三大定律。文中描述的山村学校和师生生活细节栩栩,至今依然重现在微博和报纸对农村教育的报道里。
与现实之痛并行的是刘慈欣拿手的宏大科幻场景,在宇宙深处,一场进行了两万年的银河系星际大战接近了尾声,碳基联邦为隔锁对手硅基帝国,要熄灭猎户座旋臂的大量恒星,以制造一条500光年宽的隔离带。除非该恒星系内有智慧文明能通过他们的智慧测试,才会逃过被摧毁的命运。当碳基战舰来到太阳系,恰巧抽取了地球中前述中国这个山村的学生为测试对象,智慧测试的题目恰巧就是牛顿三大定律。小学生们答出了正确答案,地球人类文明因此被碳基文明确认为智慧文明。这个死去的乡村教师,拯救了世界。
“他们有一种个体,有一定数量,分布于这个种群的各个角落,这类个体充当两代生命体之间知识传递的媒介。”小说里的高级文明这样形容地球的教师,这篇小说其实是歌颂这些不问后果的传承人。谁也不知道这些孩子、这个国家、这个文明能否获救,将以什么形式获救,但只要有人传递知识,后者才有获救的希望。
所以反理想主义的犬儒社会,更需要科幻,尤其是当现实荒诞到了奇幻的地步,才需要科幻的明朗理性之力来树其正气。
廖伟棠
香港作家、诗人。曾出版诗集《野蛮夜歌》、《八尺雪意》等,文集《衣锦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