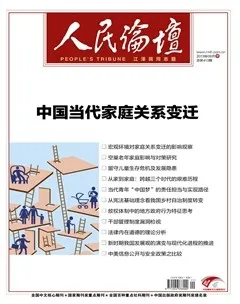游荡于自由与保守之间
2013-12-29杜霞
【摘要】中国社会现实的改造能否容纳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实现现代转化,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学人思考的关键问题。政治立场上的保守与自由之争旷日持久,其争论展开的范围和达到的思想深度值得关注,而不同知识分子在这两派之间的左右摇摆也颇耐人寻味。文章通过讨论保守与自由之间的暧昧关系,重现政治思考的哲学背景及人类现代性生存的整体困境。
【关键词】自由 保守 主体性
近代中国的自由与保守之争
从五四时期的“科学、民主”口号的盛行到对“科学、民主”实质的反省,成为社会思潮变动的基本轨迹,由此也产生了不同的派别,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这三大主流派别的争论显得尤为引人注目,特别是后两者之间的争论展开的范围和达到的思想深度值得关注,而不同知识分子在这两派之间的左右摇摆也颇耐人寻味。
保守主义是由梁涑溟、熊十力开其端,经过张君劢、贺麟、钱穆诸人阐扬,在大陆易帜后复经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努力而大行于港台及海外。自由主义则是在胡适、雷震、傅孟真、殷海光等人的宣传中得到很多的支持。双方论战的主要阵地是《民主评论》与《自由中国》两期刊。而争论的焦点始终集中在两点:第一,中国要现代化是否必须先扬弃中国传统文化;第二,政治自由是否必须预设人之道德主体性。
从中可以看出,相比严复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而言,之后的自由主义者对于自由的形上学根据有了自觉的寻求,而他们找到的最终根据是西方传统中的“天赋人权”论、理性主义等,并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缺乏这样的资源就必须进行自我检讨,从而树立西方那样的观念,这样才可能在中国实现自由主义理想。问题是保守主义的代表们也同样在进行着形上学的反思,并指出中国本有的文化传统可以提供更为高远深弘的人性根基作为实质自由建立的最终依据。
自由与保守之争的形上基础—主体性哲学
具体说来,对于西方近代以来的民主与科学,牟宗三等被视为保守主义者的新儒家,强调中国文化依其自身之要求应当伸展出的文化理想,是要使中国人不仅有其心性之学,以自觉其自我之为一“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当求在政治上能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①这显然已不同于五四时期对于科学与民主的片面理解,而是试图寻求其内在的根基,这就是人的道德心性论基础。
牟宗三的学说更多地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形而上学阐释,相比之下,以徐复观和殷海光为代表的保守与自由之争构成了这场政治思潮的主要内容。就其所达到的深度而言,他们对保守与自由的理解几乎等同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别。②自由派所倡导的自由是单子式的、不受限制的个人自由,并由此种消极自由的优越性推导出西方民主政治应置换中国的现有体制;而保守派所保存守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所提倡的“道德性”,并用道德作为填充积极自由的实质内容,然而保守派最终的政治诉求与自由派却并无二致,也是民主政治的建立。这种问题意识不仅是在制度建构层面的,而且直接涉及“人”的根本问题—对人之自由性的理解。学者们形而上的探索有其进步之处,但仍可以追问的是,无论是保守派所说的“道德性”,还是自由派所宣称的“个人自由”,其本质仍是未逃脱现代哲学“主体性”视阈的思考。我们可以质疑“主体性”这样的基本前提是如何可能的,这便构成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至于对“主体性”之挺立,是消极自由更重要,还是道德自觉更根本,其实是就主体的属性产生的分歧。两派的论述基于完全一致的形而上学前提,这恰好同西方近现代哲学关于“个人如何可能是自由的”争论接榫,或者说两派学说均是西学东渐的一个结果。价值判断来自于认识判断,知识论背景下的讨论大都从此处做起,其结论是怀疑论成为自由主义的平台。首先考察我们的认识历程,笛卡儿有作为理性主义者和怀疑方法的创立者的两重身份,由他的确引出了之后西方认识论的两条不同路径。我怀疑和怀疑本身不可怀疑,这两句话只能显示其存在论预设,即:怀疑是作为一种确定性的存在,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但怀疑论给我们更多提醒的是我们自身这种处境,即并不是我们理性不能理解的就可以取消其存在的资格。
价值选择的偶然性若不是单从理性层面可以理解的,那它是与特殊文化中的个体对德性的要求相关吗?按此思路,现代港台新儒家所确立的道德主体性是在一种传统文化内部的描述中完满充实地显示人的自由能力确有其重大价值。但由于这种描述中所带有的西方“现代性”的色彩,而使其保守身份仍晦暗不明,或屡屡遭到质疑。因为很难说对于道德主体的开显以及包含在其中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等诉求,在多大程度上保守了儒家的传统。笔者认为,港台新儒家的“保守”和胡适、殷海光等宣讲的“自由”其实是“殊途同归”,显示出两派言论共有的形而上学基础—现代哲学的“主体性”视阈。③
自由与保守之争的形下纠结—革命与否
就西方思想史而言,保守主义思潮直接针对的是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以来关于人的哲学认知。理性启蒙以来使人们乐观地相信:世界的存在是有序的,人们凭借自己的理性可以认识世界秩序,并在此基础上改变这些秩序,只要改造了不合理的社会秩序,罪恶与痛苦就会最终从人类社会消失。这一观点迄今仍是所有激进主义的基础。
保守主义思想更多地带有传统基督教关于人性的悲观观点。他们反对以政治的方式—政府的或群众运动的方式—寻求社会的根本变革。保守主义者认为,基于不完美人性论之下的人类行为并非都是理性的,甚至会是盲目的。政治行为尤其如此,只能允许它制定关于社会行为的一般规则,而不能将某种具有实质意义的行动计划强加于人类社会。保守主义的最根本特征是强调政治的有限性,就本质而言,只能期望政治行动为人们追求自己选择的目标提供某些工具。
西方的保守主义以攻击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为己任,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理性主义乃是各种自由主义最深层而隐秘的理论前提。保守主义者认为,过分相信理性,信奉形而上的超验的政治理论必然会导致用抽象的理论指导现实政治,从而导致激进的革命。就中国近代历史而言,自由的理想往往成为引导革命的最鲜活的口号,保守则常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保守与自由在中国的争论就简化为要不要革命的问题,而整个来自西方的两种“主义”之争的话语背景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
依前文所言,保守主义并非简单地反对革命,而是强调尊重传统,他们认为社会是有机体,是自然生成物,而不是人为设计的产物。因此应尽量避免为保守主义理论寻求一个统一的哲学基础,就西方而言,在保守主义阵营内部有不同的哲学作为基础,比如:基于神学或道德哲学基础上的原罪论或人性恶的学说;或者基于历史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是历史演化的产物,任何时代的人仅仅具有相对的有限的理性能力;或基于怀疑主义,质疑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④
就美国而论,怀疑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在保守主义传统中是主流。保守主义基于其怀疑论和实用主义背景,认为把政治安排的理性基础与对其认识过程的可错性结合起来才是最不坏的选择。这与自由主义提倡的尊重个人自由,允许各种不同政治意见之间的博弈,有一致之处。
以港台新儒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更接近西方的自由主义,只不过用了个“中体西用”的招儿,试图在理论上将自由理念引进中国。而今在大陆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则难逃如下两种选择:一是以怀疑主义、实用主义为基础的改良主张,一是原教旨主义地宣扬儒学的新保守主义。尤其是后者对于古典儒家美德的认定和对社会现行政治的不满,使得他们排斥价值多元论,更带有与激进派相似的“革命”特征,成为所谓的“保守的革命派”。这种原教旨保守主义当然斥责一切怀疑论和虚无主义者,因为他们认定在传统的文化中对于善、价值等有完整的说明,然而其理据却不足以服人,其表现往往是一种顽固的不宽容态度。至于以怀疑主义、实用主义为基础的改良主张为基础的“保守主义”,则一部分人尝试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论相调和,另一部分人多混迹于后现代的种种思潮之中描述中国的“现代之痛”。
结语
自由、保守、革命等政治思潮的标语有极其复杂和暧昧不清的关联。“现代性”的生存境域使我们置身于两难之中。现代哲学“主体性”视阈思考的最大成就是“理性主义”的扩张,怀疑论却一直是如影随形的理性主义的幽灵。只要还处在“现代性”的思考视域之中,政治立场上的选择:保守还是自由,便成为我们的游荡之所和栖息之地。
(作者单位:成都大学政治学院)
【注释】
①牟宗三等:“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载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0~12页。
②[英]以赛亚·伯林:《自由四论》,陈晓林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③黄玉顺:“现代新儒学研究中的思想视域问题”,载易小明主编,《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
④李强:“保守主义的内涵与价值”,《读书》,2012年第5期,第17~22页。
责编/边文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