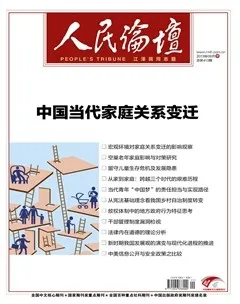康德“哥白尼革命”意义新探
2013-12-29张贵银
【摘要】从伦理道德思想和道德信仰方面来看,康德“哥白尼革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批判形而上学而在于重建形而上学,康德批判形而上学、限制人类理性,是为了给道德信仰留地盘,是为了使人成为真正不同于动植物的,真正有尊严、有价值的人,从而使康德“哥白尼革命”具有了人本主义的意义。
【关键词】康德 “哥白尼革命” 自由 人本主义
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关于他的研究论著也很多,但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康德最重要的著作是认识论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是伦理道德著作而《判断力批判》是美学著作。似乎不同的书在不同的领域讨论的是不同的问题,于是康德哲学被分割成关于真、善、美三部分,却很少有人从整体上全面探讨康德哲学的主旨,真正理解康德哲学的思想精髓。
哲学认识论领域的“哥白尼革命”
康德在1781年发表了《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他在第一版序言中将该书说成是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他发动这场革命主要为了解决哲学面临的危机。他指出:“曾经有一个时期,形而上学被称为一切科学的女王,并且,如果把愿望当作实际的话,那么她由于其对象的突出的重要性,倒是值得这一称号。今天,时髦风气导致她明显地遭到完全的鄙视。这位受到驱赶和遗弃的老妇像赫卡柏一样抱怨。”①笔者认为,康德“哥白尼革命”的意义在于重建形而上学,把形而上学改造成一门科学,他限制科学、限制知识,其目的是建立一种道德世界观、宗教世界观。实际上,《纯粹理性批判》是“未来”形而上学的导论,《实践理性批判》才是康德重建形而上学的目的和核心,他意欲建立一个以自由为基础的道德伦理和宗教世界观。而《判断力批判》则是前两部著作的综合,把人视为终极目的。
康德所处的时代面临的难题,首先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如何可能?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把理性看成是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而本质则是认识的客体、对象,认为一切知识必须符合对象,所谓“客观性原则”。康德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对理性的批判,首先在哲学认识论领域发动了一场“哥白尼革命”,康德也实现了知识与对象之间关系的倒转。他指出:“到现在为止,大家都是认定我们的知识必须依照对象,在这个前提下进行了多次试验,……可是这些试验统统失败了。那么我们不妨换一个前提试一试,看看是不是把形而上学的问题解决得好一些。这就是假定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这个假定就比较符合我们的期望,我们正是盼望能有一种关于对象的先天知识,对象向我们呈现之前,就确定了某种关于对象的东西。这个设想同哥白尼当初的想法非常相似。”②康德的这一倒转,形成了他关于对象的所谓的“先天知识”即“先天综合判断”。所谓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意思是对象只有通过理性先天的认识形式才能被我们所经验、所认识,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即源于此。
很显然,康德是想调和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矛盾,避免了经验论和唯理论各自的片面性、极端性,而且形成了新的哲学观念:我们的知识不仅仅来源于经验,也不仅仅来源于理性,而是感觉经验和理性认识形式相结合的产物。康德的这一“哥白尼革命”在哲学认识论领域意义重大,他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解决了经验论与唯理论长期争论不休而解决不了的难题。从表面来看,康德“哥白尼革命”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彻底的,有力打击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康德以后,传统形而上学确实难以立足,正如康德所说,他的“哥白尼革命”的直接后果是“消极”的,因为既然不是知识符合对象而是对象必须符合知识,那么对象必然被划分为两个方面即“现象”与“物自体”。就理性自身的缺陷而言,它在认识上“永远不能借这种能力超出可能经验的界限”。③它只能认识经验的现象世界而不可能认识超经验的“物自体”世界,一旦它想超越,就会马上陷入“二律背反”,即正题反题都成立,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争论不休之中。这让我们看到了理性的无能,在理性与“物自体”之间有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一切知识只能限制在经验范围之内,一旦超越了经验,理性就毫无用武之地。这样看来,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对于形而上学来说是“消极”的,康德为了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牺牲了形而上学。
然而,《纯粹理性批判》仅仅是“未来”形而上学的导论,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包括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两个方面,《实践理性批判》才是康德重建形而上学的目的和核心。康德对于形而上学的态度既是批判的又是建设的,因此,康德“哥白尼革命”也有其积极的意义。
伦理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
重视理性、理性主义一直是西方哲学的一条主线,给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可是,启蒙思想把理性理解为一种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把科学精神和方法贯彻到人类社会的所有领域,其结果是:为了自然必然性而牺牲了人的自由和尊严。科学理性使得伦理道德以及宗教衰落,当科学理性作为工具理性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时,否定了人的自由,消解了人的价值和尊严,形成了一个非人的机械决定论的科学世界观,它摧毁了宗教价值观,却无力建成一个新价值观。启蒙理性在历史上、思想史上起过积极作用,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局限性以及面临的困境。特别是20世纪以来,科学的发展、物质的丰富并没有使人类道德和精神一同进步,人类社会多次回到黑暗、迷信和野蛮的状态。从表面看,康德是调和的、折中的,好像很软弱,实质上其思想却很深刻。康德不仅不反对理性主义而且他的“哥白尼革命”还继承和发展了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他把形而上学看成是一种道德理想,从而使他的“哥白尼革命”具有了伦理道德意义和人本学意义。通过他的“哥白尼革命”,伦理学获得了独立。
在《实践理性批判》导言中,康德把理性区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在理论领域,理性是无能的,而到了实践领域,理性才有了用武之地,康德所说的实践指的就是道德实践。康德把科学理性转变成了一种道德理性,用“德性就是力量”取代了“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理性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其本身只有相对价值,而道德理性就弥补了科学理性的不足和缺陷,道德理性具有最高价值,为人类理性找到了发展的出路和方向。康德指出:“善良意志具有绝对的价值”,他发现:“技艺、甚至科学,并不给他带来幸福,而只加重他的负担理性的真正目标,就它是实践的,即能够影响意志的这方面来说,必定是要产生一个善良意志”④,这里涉及到伦理学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动机和效果的问题。道德必须是自觉自愿的而非被迫的“行善”,只有自由的行为才有道德价值,被迫做的事情,就没有道德价值。进而康德提出了“绝对命令”、“意志自律”的思想、道德的普遍立法原理,善良意志为自己立法,自己守法,这就形成了人心中的道德律、形成了伦理学的一条黄金规则:你要别人怎么对你,你也要这样对别人。
康德关于意志自律的思想,无疑在伦理学界也引起了一场“哥白尼革命”,传统伦理学面临一个难题,即自由与道德法则的问题,他们主张德性在于符合自然的本性,而最终受制于外在的必然性,因而许多伦理学家都陷入了决定论的泥潭,否认有普遍的道德规律和道德法则;康德反其道而行之,认为意志自由是道德的前提条件,道德法则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绝对命令”。在康德看来,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首先,人作为自然万物之中的一种存在,像物一样,他也时时刻刻要受到自然法则的限制,不能违反自然法则,因而是不自由的;其次,人又与万物不同,他的确具有认识能力,具有超自然的属性即“理性”,虽然人的理性也是有限的,可是实践理性有能力使人能够自由地按照理性自身的法则规定自己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人又是自由的。人为自然立法,理性为自身立法,人是最终目的。他说:“你行动时,应该把人性,无论是在你自己身上或者是在另一个人身上,总是作为一个目的,而永远不只作为一种手段来使用。”⑤德性不在于符合外在的必然性,而在于自觉遵守内在的必然性即我们心中的道德律,通过“自律”,完全出于自身的法则而行动,他认为不能把自由理解为不受法则和规律的限制而应该把自由看成是“自律”,自由意味着责任,而非想做什么做什么、想说什么说什么的任意胡为,把道德法则看成是实践理性或意志自身的内在必然性。
可见,康德的这一颠倒乾坤的“意志自律”和“自由”的观念,的确是伦理学领域的一场“哥白尼革命”,其不仅解决了传统伦理学面临的困境,而且凸显了人的价值、人的意义,使得康德的这一场“哥白尼革命”具有了人本主义的意义。
宗教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
康德在宗教哲学领域也发动了一场哥白尼革命。康德有句名言:不要用《圣经》理解道德,而要用道德来理解《圣经》,他从理性的角度来研究宗教、理解《圣经》,就把事情倒过来了,不是从宗教信仰来理解道德,而是从道德来理解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而不是道德建立在宗教信仰上。对那些根本不讲道德的人,宗教对他们也没用,但多数人是讲道德的、有良知的,宗教信仰就可以保证有道德的好人有好报,德福统一,达到“至善”。
如前所述,康德的“绝对命令”只是一种“应当”哲学,我们应当那样做,可是许多人不一定能那样做。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类并不自由,人的道德和人的幸福往往是对立的、矛盾的。康德认为道德与幸福的统一就是“至善”,这是最理想的人生,既道德高尚又能够享受幸福生活,如果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却生活不幸福,总是遭受种种不幸和厄运,这样的人生是有缺陷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在今生今世,人们常常会发现:道德高尚的人总是难享俗世的幸福,而大奸大恶之人却总能呼风唤雨,享尽人间荣华富贵,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总是不能让人信服。当然,如果行善是为了图好报,那么动机就不纯粹了,就不是“善良意志”,其行为也就没有道德价值。康德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今生今世是不可能实现道德和幸福的统一了。只有设想在彼岸的理想世界,“至善”的理想能够在那里得到实现,有三个“道德悬设”即意志自由、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所谓“悬设”,康德把它理解为“一种理论上的但本身未经证明的命题,只要它不可分割地与某种无条件地先天有效的实践法则联系着。”⑥在康德看来,自由是道德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自由,道德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假设有一种摆脱了感觉世界的限制而依理智世界的道德法则决定自己意志的能力即自由,否则至善就不能成为实践理性的对象”,⑦对“至善”的追求是必然的,“至善”被悬设为必然的,由于道德法则中没有至善的根据,因此我们必须假设一个并非自然同时又是全部自然的原因的东西,这就是凭其理智和意志按照自然原因创造世界的造物主,即上帝。“只有在上帝存在这一悬设之下,我们才能想象,我们生存于其中并谋求幸福的世界状况能够以超自然的理智世界的道德法则为前提,并且与之协调一致,否则至善就是不可能的”。⑧有人认为,康德哲学发展到这里体现了神学的不彻底性,这种看法未免肤浅,实则不然,康德建立“悬设”的目的不在于宗教信仰而在于道德信仰,悬设是为道德服务的,是为“至善”提供必要条件,康德把上帝存在作为“悬设”,其用意仍然在于道德而不在于宗教。在他晚年的著作中,康德写到:“上帝概念是理念,它是作为道德存在的人自己,通过把一切为绝对命令所限制的责任看做来自于它的命令,而造就的一个与正义原则相关的最高的道德存在”⑨,上帝不是存在于我之外的一个实体,而是存在于我之内的一种道德法则、道德律,上帝就是为自身立法的道德实践理性。
康德始终都坚持上帝的存在是不可知的、是无法证明的,道德既不依赖自然也不依赖上帝,康德始终都宣称他限制知识、限制科学的目的就是为道德信仰留地盘,就是为论证人的道德与自由开辟道路。康德发现,科学技术只是人类自然力量的增长、延伸,并没有在本体意义上完善人性,相反,人性越来越沦丧、堕落,同时,康德也意识到传统的宗教信仰也无法真正解决人性的问题,人性的修复只能够通过道德救赎才能实现。人心中的道德律是一种普遍立法,对人的行为起指令和监督作用,和传统宗教不同,道德律的普遍立法是出自于人性的内在力量,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的突显,是在自由的前提条件下,人出于义务而作出的自觉自愿的行为。真正的道德信仰是自主的,自由的,依据自己对生命、对社会、对历史的理解和体验,成为自我创造和自我完善的表现,从而实现人真正的自由;而传统宗教信仰,是通过宗教教义、上帝权威或者教会的意志,命令人们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对人的行为的约束是外在的、无力的。人们把自己的存在和本质依附于外在于自己的上帝造物主上,人也就失去了自我本质,丧失了自由。康德认为:人性的堕落使人必须皈依基督教,但不是传统的基督教而是经过改革的基督教,也就是他倡导的道德神学,真正实现人的自由。通过“自律”,实现对自己和他人的尊重,可见,康德的这种道德救赎、道德神学,洋溢着一种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
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论”中,康德写到:“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⑩康德完成了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妥协,既不像18世纪的启蒙思想那样只要理性不要信仰,也不像中世纪一直到16世纪那样只要信仰不要理性。康德还是偏重理性的,他警告人们,如果陷于感官而遗忘了理性,这两大原则就会变质为占星术和狂热迷信。
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注重科学、经济的发展,却忽略了道德信仰的建设。如果我们长期坚持把宗教等同于愚昧无知、迷信欺骗,拒绝人的生存和目的的宗教答案,缺少敬畏和感恩的心,不仅无助于自身修养的提升,更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星空的人,有一些注重内心道德自律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
(作者为贵州师范学院经济与政治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③[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页,第171页。
②《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41~243页。
④⑤[加拿大]约翰·华特生:《康德哲学原著选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93页,第210页。
⑥⑧⑩[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8页,第126~128页,第220页。
⑦[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35页。
⑨[德]康德:《康德全集》(第22卷),普鲁士科学院版,第105页。
责编/王坤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