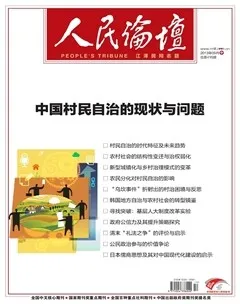追寻民主政治的历史印记
2013-12-29王恒
【摘要】民主政治在联邦德国的确立几经波折,1849年的“法兰克福宪法”初步使德国民众体验了民主政治的生活。1919年的“魏玛宪法”虽然被誉为当时最具民主特色的宪法,但是其本身的制度设计缺陷却没有使魏玛共和国长期存在下去。直至战后,制定与实施“基本法”后,联邦德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才最终确立下来。
【关键词】法兰克福宪法 魏玛宪法 基本法 历史印记
“法兰克福宪法”与德国民主政治制度化的开端
回顾德国历史,让人感慨万千。它产生过康德、莱辛、歌德和贝多芬这样的文化巨匠,对世界文明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它也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使人类遭到浩劫,而且酿成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德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矛盾体根源于其特有的历史和文化。一方面,历史上德意志存在深厚的专制统治传统和由此培养的社会对于秩序与权威的向往,正如郭少棠所指出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封建体制为德意志民族留下难以清洗的传统烙印:一种自卑的情结,一种‘双重性’的权威观念(既是专制的,又是开明的)和自由观念(自由中有包含着不自由的倚重)。”①另一方面自近代以来,德国这块土地上又不乏民主、自由的种子。
在德意志的民族兴起过程中,它承载了很多的历史包袱,其中最大的、对其产生致命影响的是它长期处于一种封建割据的状态。也即当19世纪自由和民主在西方兴起并取得飞速发展时,德国人却仍在为他们的统一而奋斗。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统一与建立国家远比自由和政治民主更重要,这样就导致德意志民族在发展过程中自由、民主观念比较淡薄而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却大行其道。但是,受法国启蒙思想的洗礼,德意志还留下了另一份遗产,那就是坚持自由、理性与民主的思潮。在德意志的历史上出现了像歌德以及莱辛、席勒等古典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大师,他们反对封建强权统治和封建制度,提倡个性解放。
德国自有史以来,民主思想在人民中间和受过教育的阶层中,一直有着深厚的根基,但却难以外在成为政治制度,而1848年革命的进行及1849年“法兰克福宪法”的制定使民主政治在德国有了初步的外在化表现。
1848年,随着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欧洲爆发了一场近代史上最大规模和范围的资产阶级革命。德国的普鲁士与奥地利这两个保守主义的邦国被迫卷入革命的漩涡之中。在革命过程中,两个邦国的自由主义者与革命群众冲击了专制王权,推动了民主改革与民族统一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的革命成果,主要表现在法兰克福国民会议的举行与“法兰克福宪法”的制定。在国民议会上,由自由主义者推举产生了一个中央政府,并决定由它管治一个即将出现的统一国家。国民议会草拟了一份宪法,并在1849年3月完成,这就是统一的德意志的第一份宪法:“法兰克福宪法”。宪法肯定了人身自由,信仰、言论、出版、行动等自由,法律平等,给予公民结社和集会等的权利。1848年的革命经过两年的努力最终破产,革命群众运动受到镇压、国民议会亦被解散。
追究革命失败的原因,很多学者都把责任归咎于自由主义者身上,认为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与背叛导致德国在追求民主、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道路上未能成功。如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的说法很具有代表性:“在这一时期的德国,最没有行动能力的显然就是相当于资产阶级的那个阶层。”②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过分苛求,在那个时期,德国的政治现代化需要进行的工作太多,实在是没有哪个政治群体足以完成这些沉重的任务。
随着国民议会的解散,“法兰克福宪法”也被抛弃,但是它并不因被废止而销声匿迹,在德国政治民主化的历史上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法兰克福宪法”使得德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主、自由与理性的思想突破了内在的概念化,它们真正地表现在了外在的制度设计上,使德国民众初步体验了政治生活上的民主。其次,它为德国以后的制宪提供了准绳与方向,正如赫尔穆特·施泰因贝格所说:“1849年宪法对现代德国民主宪法产生了其他宪法都无与伦比的影响:它第一次提供了国家统一的完整的宪法概念。俾斯麦的1867及1871年宪法中的主要联邦因素;1919年魏玛宪法,1949年的波恩基本法,都可追根溯源到1849年宪法。1849年宪法的原则和观点,诸如基本权力、民主代表、法治、宪法至上、司法审查也一直渗透到20世纪德国的民主宪政中。”③
1919年“魏玛宪法”与德国民主共和国的体验
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进,1871年在俾斯麦的“铁血政治”谋划下,德国最终实现了统一,建立了第二帝国。为避免一触即发的国家内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一系列矛盾,同时为了实现大德意志帝国的目标,以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为首的德国统治阶级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正是这次大战,德国人民在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的鼓舞下以及美国总统威尔逊宣称的“为民主与自由而战”的口号影响下,发动了一场真正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推翻了历经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1848年革命与1860年宪政危机而屹立不倒的德国王权,建立了以社民党与中央党、德意志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开始了现代议会民主政治。
革命成功以后,1919年2月,国民议会的代表在象征着自由的歌德之故乡—魏玛城制定宪法,并于8月11日正式颁布“魏玛宪法”,体现了民主共和国的胜利、立宪主义者们的胜利。虽然“魏玛宪法”是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最晚的一部宪法,但它把欧美各国宪法的精华兼收并蓄,因而成为当时最具民主特色的宪法,被普遍视为“二十世纪最值得注意的宪法之一”。
“魏玛宪法”从法律上肯定了资本主义民主议会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相对民主的国家,给公民适当的权利。表现在:确立了人民主权的原则,宪法中明确写出“德意志联邦为共和国政体,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同时宪法赋予了人民较之早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更多的权利:规定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主张公民享有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信仰自由等权利,取消等级特权和贵族称号,所有公民都享有同样的地位。在政治制度安排上,选择了议会民主制:确立国会是最高立法机关。国家的元首为总统,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元首的权力范围,主要职权是:可以任命国家总理和各部部长,可以下令解散议会和进行新的选举,有紧急处分权。比起德意志皇帝的专制统治,宪法对国家元首的权力做出了限制,这明显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魏玛宪法”的先进性并没有使魏玛共和国长久存在下去,后者仅仅存续了14年便被纳粹政权以合法的形式篡取政权,建立了第三帝国。因此这部宪法也遭到了不少诟病,很多学者认为共和国生活与专制王权统治相比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形式上皇帝的权力转予了总统而已。“魏玛宪法”遭到批评说明它本身是存在问题的,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这部宪法的制定和通过是专制传统与民主力量公开妥协的结果。
魏玛共和国被第三帝国取代,在政治方面表现是宪法中确定的政治制度不完善。最大的弊病在于赋予总统以巨大的权力,史学家将魏玛共和国的总统称为“无皇帝头衔的皇帝”,这体现在宪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上:总统在认为国家有被扰乱或危害时,可以采取包括使用武装力量在内的紧急措施,有停止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条款的权利。④这导致权力上议会与总统的均衡关系向总统方面倾斜,议会难以有效实施其权力。“自1930年兴登堡再度被选为总统后,魏玛共和的内阁已被架空,总统制成为魏玛共和政治运作主轴,这为希特勒担任总统后独揽大权开辟了一条‘合法之路’。”⑤同时还有选举中实行的比例代表制,致使议会内部多党分裂局面,导致内阁不稳,客观上有助于纳粹党的发展和削弱了议会对总统的反作用力。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废除了议会民主制,以纳粹帝国取代了魏玛共和国,并且彻底摒弃了“魏玛宪法”。这部宪法虽遭受很多诟病,但其中很多不乏社会民主主义的规定成为以后“基本法”的蓝本,“基本法”不仅继承了“魏玛宪法”的传统,而且还把其中某些条款作为自身的组成部分,使之继续有效。
1949年“基本法”与联邦德国民主政治的最终确立
1948年2月至6月,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外长在伦敦举行会谈,讨论未来建立的西德政府问题,形成《伦敦建议》,为了贯彻落实这一文件的精神,7月美、英、法三国军事长官向西占区的11州的代表递交了《法兰克福文件》,要求西占区召开制宪会议,着手制定宪法。1948年9月,在波恩组成的议会委员会以“魏玛宪法”为基础,开始进行“基本法”的制定与审查工作。“1949年5月8日,议会委员会以52票赞成、12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基本法》,12日,《基本法》获得西占区三个军事当局的批准,23日,由议会委员会予以公布,同时获得除巴伐利亚州以外的10个州议会的批准,24日,《基本法》正式生效。”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德国)的宪法,正式名称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简称《基本法》。联邦德国立宪人所以要选择这个名称,目的在于使《基本法》作为过渡性和临时性宪法,待德国重新统一后,再制定“最终宪法”。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德国统一时,德国人民没有再制定一部新的适用于整个德国的宪法,最终使“基本法”成为一部永久性的宪法。“基本法”是一部受到世界各国关注并借鉴的规范化的模范宪法,对于这样一部具有生命力的宪法,德国人民选择继续保留适用、放弃改弦更张似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从“基本法”的形成过程来看,它与西方盟国的影响和作用是分不开的。西方盟国对“基本法”的指导思想、民主原则、制宪程序以及政府结构组成等都予以详细的规划;同时在战后经济形势恶化,德国人民仍倾向于建立一个集中的政府的情势下,如果没有西方盟国的坚持与干涉,联邦德国是否还能够形成稳定的民主政治体制就是一个疑问了。但是我们还应该明白,这部宪法能够在德国生根发芽、延续至今,这么强的稳定性更多的是受本国民主经验与立宪传统的影响。德国的制宪工作经验丰富,1849年的“法兰克福宪法”、19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后的“德意志帝国宪法”、1919年的“魏玛宪法”,这些丰富的立宪经验与传统,为联邦德国制定“基本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立宪者最基本的动机是反思魏玛共和国时期纳粹暴政上台的原因,充分汲取魏玛共和时期种种宪政经验教训,更改“魏玛宪法”上一些错误结构和缺陷,保留民主规定性的条款,因此1919年民主的“魏玛宪法”既发挥了榜样作用,又充当了反面教材,“基本法”不是腾空出世的,而主要是来自于“魏玛宪法”并站在“魏玛宪法”的肩膀之上。
民主的确立与巩固需要在制度设计上处理好“人民主权”原则与国家权力运行机制之间的关系,既要尊重人权,又要防止民主权力的滥用;既要控制权力,又要防止国家权力陷入瘫痪或无所作为,在权利与权力、自由与权威之间达到一种平衡。
而“基本法”做到了这种平衡的要求,具体而言,其首先体现在对公民基本权利保护方面,公民的基本权利部分被置于宪法的首端,这样传统的公民对抗国家的防御权就得以确立;与之相联系,公民的基本权被设计成为直接的主体性权利,这些权利是可诉的,可以通过法院来予以保护;同时公民的基本权利不仅仅能约束行政,同时也能约束立法和司法。其次,其开创了宪法规范政党制度的先河。把政党入宪,实现了政党民主法治化,政党作用得到了发挥,同时保证了政党在国家民主制度框架内中活动,使国家制度决定政党,而不是政党决定国家制度,既防止了再次出现纳粹政党建立法西斯专政的现象,也巩固了民主政治。第三,其在制度设计上产生了一个有机结合体的议会,以及转变了政府的尴尬地位,赋予了总理实权,保证行政的有效性与稳定性。
“基本法”自1949年颁布至今,越发显示出它的稳定性,联邦德国民主政治也越来越巩固,“1951年,德国民众中认为民主体制比威权体制好的比率仅为2%,1953年不到10%,1962年比率迅速上升到62%,1970年表示支持民主体制的人占到80%,1972年,高达90%的公民表达了对民主的欢迎。”⑦这显示出从19世纪开始,在德国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困难的进程才被建立起来的民主统治终于在基本法中找到了一种稳定的存在形式。
结语
从德国民主宪法的历史梳理和民主化过程的曲折发展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传统”与“现代”不是两个截然分割的历史阶段或社会形态,现代的因素正是传统慢慢发展与转变的结果,正如德国从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发展至路德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兴起、1848年革命前后自由主义的冲击、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实践最终到战后民主国家的重建与巩固。第二,从传统到现代化不是一个直接、单线的转化,而是必须经历不同的经验和价值的接触、碰撞、斗争、融汇,成功的转型依赖很多合适的条件,甚至包括历史机遇。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实事求是,勇于探索,抓住机遇从而找到一条适合本国政治改革和发展的道路。第三,民主的发展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政治的改革道路充满荆棘与坎坷,没有哪个历史进步不建立在痛苦与失败之上。我们需要做的是鼓起勇气,迎难而上,在跌倒的地方找到失败的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前行。第四,民主化没有固定的发展道路,没有完全可以复制、粘贴的模板,民主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走一条自己特色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把民主制度活生生地演绎出来。因此我们在吸收别国先进的经验的同时,必须继承和保持本国文化中的有利因素,以取得平衡。在这点上,二战后的德国民主政治建设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中外政治制度专业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郭少棠:《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②[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德国的浩劫》,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120页。
③Schwabe Klaus, Woodrow Wilson, Revolutionary Germany, and Peacemaking, 1918~1919: Missionary Diplomacy and the Realities of Power,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5, p263.
④⑥陈志斌:《德国政体教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3页,第94页。
⑤王云飞:“从魏玛宪法看魏玛共和的体制性弊端”,《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91页。
⑦David P.Conradt, Changing German Political Culture, Gabriel A.Almond and Sidney Verba, ed,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989, p223.
责编/许国荣(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