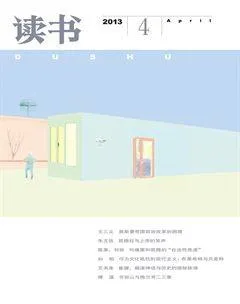立法者、医生与良法之治
2013-12-29韩伟
柏拉图在西方哲学史中的地位,大概只有中国传统学术谱系中的孔子堪与之相比,其深邃的思想,广博的知识,长期以来受到西方学界的关注,学者们撰写、出版了大量对柏拉图的解释、注疏文集。但是,正因为他在哲学史上的巨大影响,使得哲学性偏弱的《法义》(有的版本译作《法篇》)一篇,长久以来受不到哲人的青睐,但是,《法义》在哲学上同样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它讨论的有关法律与美德、宗教、政治等等错综复杂的关系,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也正是卡斯代尔·布舒奇投入极大精力对之做导读的原因。柏拉图的《法义》中,曾对立法者与医生做了一个有趣的比较,他借用雅典人的话说:“大部人需要立法者,因为立法者建立了大众自愿接受的法律,这就像人们需要体操老师或医生那样,因这些人说,他们可以让患者的身体舒舒服服地获得完全的治愈!”立法者与医生的比较,实质上是指,应由好的立法者制定出良法,这种法律更易于被人们所接受。于是,自然就生发出相关的两个问题,什么是好的立法者,什么又是易于被接受的“良法”?
在柏拉图的描述里,雅典人通过类比医生的方式,已经初步指出了真正好的立法者应具备的特征。首先,好的立法者应该像好医生与病人一样,建立起一种真正的“亲密关系”,能切身地体会一般民众的情感,以极大的耐心细致地对待民众,设身处地,并且推己及人地为民众考虑,温和甚至富有诗性地说服民众。在谈到作为自由人的医生时,《法义》谈道:“他们对病人进行细致入微的探询,依自然的法理追根究底,并把病人看成自己的亲人。他们对病人极尽耐心,尽可能地就病人的健康状况收集信息,除非征得病人的同意,否则他们是不会开方子的。”这里自然包含的意思是,立法者需要深刻地了解民情,就像医生先追根究底地探究“病情”一样,在了解民情、社情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开出合适的立法“药方”。其次,立法者应采取一种循循善诱的方式,说服民众主动地遵守法律,这一方面是一种态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一定的技艺。好的医生不应该以一种令人痛苦的严方来治病,在《法义》中,医生尽可能地将愉快和效果调和起来。柏拉图借雅典人之口,批判了不结合说服的立法:“当他们在立法的时候,他们不是将必然性与说服结合起来,而只是诉诸简单和纯粹的强制。”这显然不是好的立法者应有的态度。当然,这种说服也包含有“技艺”之意,在与身体有关的层面上,体操(预防)属于医术(改正),而在政治的层面上,立法(预防)属于司法(改正),它们本质上都是一种通过说服,达到某种效果的技艺。这与中国传统的“以刑弼教”的法律观具有某种可比性,“刑”不是目的,而只是在“说服”、教化无效时,才不得已而为之,最好的情形是:“法令所行,可以使土偶奔趋;惠泽所浸,可以使枯木萌蘖;教化所孚,ADA7b165ncwrk3zdz6B/pg==可以使鸟兽伏驯;精神所极,可以使鬼神感格。”(《呻吟语·圣贤》)
由此,不仅可以理解柏拉图对立法论述的中心,也可以进一步理解“良法”的核心。正如A.Laks所述,《法义》寻找的是如何让不需要强制的非理性达到理性化的可能。可以看到,正是“说服”构成了柏拉图论述立法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要求。那么,为什么要说服?或者可以继续追问,说服所求助的是一些纯粹的理性看法呢,还是需要公民认同并接受他应采取的信仰理性?说服是否包括非理性的手法?用另一种说法就是,什么使说服具有意义:是说服通过缓解法律的强制性,发扬它的内在理性而达到的共识,还是其他可资利用的理由,例如可能产生效果的“欺骗性宣传”?事实上,理性说服会遇到两种局限,一是以简单和纯粹的方式所取消的强制并没有消失,一旦说服不起作用,威胁和暴力就会应运而生;二是谎言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考虑的,尽管柏拉图认为这种伎俩是一种小恶。柏拉图并没有提示过,在可能用某种理由说服某人时,就去利用一切办法,甚至用不合理的手法加强这种理由,仅仅因为那样更为经济。起码可以说,具有理性的说服为公民的善是本质性的,这样的说服对他们有许多益处。说服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公民的幸福,好的法律“使遵守它的公民获得幸福”,这与埃德蒙·柏克所谓的法律的基础是“普遍的公众的功利”异曲同工。《法义》指出:“法律本身的作用乃在于,或者通过说服,或者通过力量和正义来惩罚那些不听从说服的人,以便使我们的城邦在诸神的喜乐中获得幸福和富裕。”这意味着,良法是为了公民的幸福,而达致良法之治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说服”,说服只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良法本质的目的。在现实性上,问题是“怎么说服”?“说服”需要有一些技艺,也需要为知识所引领,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宣传,或者说是教育。说服以及作为说服最终目的的幸福在根本上都离不开教育。通过说服,教育在事实上将情感到理性的不同环节串联起来。柏拉图只是强调了“说服”在良法中的重要性,他并非完全排斥强制,只是二者境界不同,这与西塞罗的观点也颇为类似:“仅仅出于恐惧而遵守法律,这种想法不仅会让一个有学识的人感到脸红,甚至也会使一个头脑简单的乡巴佬感到脸红。”所谓“圣人不强人以太难”,一定是诉诸主体的自觉。而说服,正是将这种外在的恐惧,转化为内在的自主性动机。
就立法中的“说服”,柏拉图特别强调“法律序言”的重要作用。柏拉图说:“我深信,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凡是用竖琴奏出的歌及所有音乐作品,它们的‘律—调’都以一段经过精心制作的序曲作开场白,但是却从来没有人将真实法律的某一部分成为序曲。”甚至,在本质上起说服作用的,是序言而不是法律。其中部分的原因在于,序言是某类“不易被归为一种相同模式内的”表述,它允许各种相异的定义,暂时放弃使用统一的概念来确定特定的形式,因此,它更适合使用温和的、亲切的语言,来阐述立法的关键理由,并达到“说服”的目的。这里类似谈话“开场白”的法律序言,可以激发信任,并在信任的帮助下使某人更容易地懂得别人可以通过他来学习的东西,以便使命令,也即立法者赋予法律的人所接受,它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全部谈话(即法律)的目的所在。类似于音乐中的序曲,或对话的“开场白”,通过这样亲切的方式,将人们自然地带入法律这一“情境”当中。在根本的意义上,法律序言与医生的劝诫,都涉及“自由”,两者最终都诉诸“接受者”自由的决定,而不是强制。医生诉诸病人的同意,与法律的序言所要凝聚的共识完全一样,均落实为某种形式的谈论,并以一种谈论的伦理为前提:“法律序言,即使不利用柏拉图的对话方式,无论在内容上还是程序上,涉及的无非是一些相类关系。”它最终保障和推动的,正是那些被称为个人自由的事物。正因为“序言”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故任何单独的法律都不应与序言分开来读。
借由对“说服”之立法的理解,我们可以继续探讨什么才是“良法之治”。毫无疑问,这里首先需要具备的一个前提就是“良法”,也就是由好的立法者制定良善的,符合促进“公民的幸福”之目的的法律。这样的法律,本身应该包含有“说服”的因素,它亲切地对待民众,体察他们的疾苦,耐心地倾听他们的呼声,探究社会民情真正的“病症”所在,并附之以具有“开场白”性质的“法律序言”,使得整个立法本身就是充满温情的,是符合大众情感与习俗的,因而也是为大众所愉悦地自愿接受的法律。有了良法,就需要探讨如何实现“善治”。我们同样可以经由前述对立法者与医生的比较来做出分析,“医生不但要在医疗上措置得当,而且要使病者和看护他的人树立正确的应对态度”。可见实现“善治”最为关键的是两点:一是立法者(包括法律实施者)应该“措置得当”,即使用得当的方法,这里的“得当”当然可以做诸多解读,但是最基本的,应该是该方法本身包含了正义、公平等要素。当然,尽管“说服”的作用极为重要,但并不是说可以忽视强制性的方法,只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不应该脱离上述“得当”的基本要求。当然,不可忽视的另一面是,作为法治的对象,民众自身对法律的理解,及其主动地守法,积极地用法,形成正确的法律观念,同样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这些品质的养成,起到重要作用的,仍是作为医生的“立法者”。而且,只要民众真正意识到法律的本质属性是良善的,其目的是为治愈社会这个拟制的有机体之“病症”,是为了人们自身的安全,为了生活的安宁和幸福,那么这种“说服”就更易于达成,法律自然更容易获得普遍的、自觉的遵守,就像他们乐意舒舒服服地获得好医生的治疗一样!
(《〈法义〉导读》,卡斯代尔·布舒奇著,谭立铸译,华夏出版社二零零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