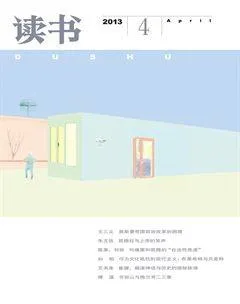奥斯曼帝国政治改革的困境
2013-12-29王三义
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大张旗鼓地改革始于一七九二年,即塞利姆三世当政的第四年。而局部的革新,比如引进西方的技术、购买西式武器、创办技术学校,前任苏丹阿卜杜·哈米德一世就尝试过。至于学习欧式的建筑,模仿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在“郁金香时代”(一七零三——一七三零)就开始了。奥斯曼帝国改革的大体路径与其他后发国家的改革并没有差别,首先是军事改革,接着技术引进,稍深入就是经济改革,最后是政治改革,即仿建西方的政治制度。改革目标是富国强兵,改革内容是学习欧洲经验,改造传统社会。虽然富国强兵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但军事改革和经济改革多多少少都有成果,社会习俗和年轻人观念的变化之快,更是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改革遇到问题的还是政治改革,因为政治改革远比技术引进和经济改革的难度大。
政治改革是改变制度,改变制度意味着权力再分配,一般情况下,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总是最激烈,所以政治改革总是阻力大,改革幅度小,难见成效,而且风险大,弄不好要出乱子。不过,奥斯曼帝国政治改革的具体情况却有所不同。塞利姆三世(一七八九——一八零七)在改革军队方面做了努力,没来得及进行其他改革就被废黜。马哈茂德二世(一八零八——一八三九)的军事改革、经济改革均取得成效,政治改革只迈出第一步,把帝国各级衙门改换成西欧模式的政府部门,设立咨询和审议机构,并致力于革除官场陋习。可惜,由于希腊人闹独立,埃及总督挑战苏丹权威,俄国军队入侵,帝国的改革让位于维护国内稳定、保卫国家主权。一八三九年马哈茂德二世病逝,新苏丹阿卜杜·麦吉德上台,立即颁布改革法令——“古尔汗法令”,高调门向本国臣民和欧洲使节宣示:奥斯曼帝国要掀起一场全面的改革运动。随之产生了一个专门术语“坦齐马特”(指一八三九年开始的改革和整顿)。十几年之后(一八五六)又颁布新的帝国改革法令,这个法令比第一个法令更具有可操作性。奇妙的是:帝国政治改革一开始遇到的阻力并不大。改革派代表如雷希德帕夏、富阿德帕夏都是实权人物,了解西方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也是实干家,说改就改,行政管理、财政、军事、司法、教育,几乎就是全面铺开。以前的改革总是受制于旧军队,如今帝国的新军(一八二六年取代旧军队)是欧洲式的军队,军事将领大多属于新派军人。资料显示,宗教界权威人士也没有反对。广大农村和牧区是否欢迎政治改革,不得而知,但城市里的市民在“古尔汗法令”颁布后表现出欢欣鼓舞。不管出于何种理由,至少说明“人心思变”,政治改革顺应了部分“民意”。欧洲人希望看到保守的奥斯曼帝国出现政治变革,所以对“古尔汗法令”一片叫好声。
“古尔汗法令”和一八五六年的帝国改革法令中,关键的内容,一是明确宣布保障所有臣民的生命、荣誉和财产安全;二是承诺颁布维护人民利益的新法律,宣称新法律对所有的臣民——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是平等的;三是在纳税、服兵役等具体方面,各阶层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当改革家描述改革前景时,上自苏丹,下至普通穆斯林都感到帝国富强和进步有希望,恨不得马上就改出个名堂来。一些人甚至认为,法令要是早点颁布、早点推行,许多难题早都解决了。等真正实践起来,好处并不怎么明显,缺点倒是暴露无遗,于是连起初支持改革很坚决的人,也起来攻击改革,几乎要把事情整个儿推翻。“坦齐马特”时期三十七年,两任苏丹阿卜杜·麦吉德和阿卜杜·阿齐兹全力以赴支持改革派搞改革,除了打仗(克里米亚战争)和借债,从未轻言放弃改革,而支持改革的臣民逐渐减少。由于国内矛盾加剧,一八七六年五月,阿卜杜·阿齐兹在政变中被废黜,一年内连换了两位苏丹,后一位苏丹就是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一八七六——一九零九年在位)。
新苏丹刚一上台,政府就宣布实行宪政。一八七六年,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颁布,接着推选代表,召开议会,像模像样地搞了一场欧洲式制度的演练。经过前面几十年的改革实践,奥斯曼土耳其人逐渐明白,西欧国家的强大不仅仅靠经济和军事实力,奥斯曼帝国仅仅学习西方的技术还不行,还要模仿英、法等国的政治制度。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尽快在奥斯曼帝国实现欧洲宪政呢?说立宪就立宪,说选代表就选代表,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一八七六年八月登基,十二月就颁布了宪法,第二年就召开了议会。不过,到第三年就解散了议会(总共召开了两届议会),在一九零八年革命之前有整整三十年(一八七八——一九零八)再没有召开议会,经济、文化领域的改革没有停止,而政治上回到苏丹专制。
总体来看,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改革,无论出现挫折还是倒退,问题并不是遭遇反对派的强大阻力,也不是“改革不彻底”(比如没有发动民众等),不在于改革派软弱不软弱。恰恰相反,政治改革的起点高:一八三九年破天荒地要把“权利”、“平等”以法令形式固定下来,一八七六年快速地制定宪法,雷声才响,雨点就落下来(议会召开了)。奥斯曼帝国史相关资料显示,几乎各阶层都支持改革,看好改革。我们很难猜测,奥斯曼帝国各阶层怎么那么容易达成“共识”?我们知道,奥斯曼土耳其人后来成功地走上西化道路,主张西化的一派坐了江山,对历史上的改革有所夸大。不过,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对改革达成“共识”的情况也是有的。比如一七九二年塞利姆三世提出要改革军队,那一次的御前会议上各个政治派别确实达成“共识”,臣民也是支持的,因为俄国人已经打到黑海了,此前奥斯曼帝国与俄国打了一个世纪(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末)的仗,没有赢过一次,再不改革军队,就要亡国了。一八三九年和一八七六年的政治改革实践,我们排除史料夸大的成分,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奥斯曼帝国国内形势很严重,外患迫在眉睫,非改革政治制度不可;国内各阶层的利益都在受损,不支持改革不行。
不管怎么说,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改革启动势头很猛,最高统治者苏丹本人决心大,改革派大臣支持强劲,反对力量弱,但是,随着改革措施的展开,情况就发生了微妙变化,不支持的多了,反对的意见多了,改革渐渐停顿,最后的结果,不是苏丹被废黜(如阿卜杜·阿齐兹被废),就是苏丹驱逐了立宪派(如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做法)。
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为什么仅仅推行了两年宪政就停了呢?理由很简单:建立议会,实行选举,就是要让议员们参与国策;政府发挥独立行政职能,政府首脑就要行使国家行政权,宫廷就不再是整个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了。这也就意味着,国家大事,不能由苏丹一个人说了算。苏丹此时才明白,原来所谓的宪政,就是限制苏丹的权力,国家的权力中心要从皇宫移向政府、议会所在地。这怎么行?苏丹无论如何不能忍受议会、政府与皇宫的并行,不能忍受苏丹本人与议长、政府首脑之间权责的划分。于是这位苏丹解散议会,推行独裁统治三十多年。
其实,自马哈茂德二世的政治改革起步,到后来的“坦齐马特”,前后几位苏丹都面临着同样的困惑:不引进西方的制度,单纯的技术引进和局部改革不足以富国强兵,但西式的制度就要限制君主的权力;倘若苏丹权力弱化,行省和属地就会闹独立,苏丹必然失去权威;只有加强中央集权,才能防止地方势力分裂割据,但这样做与西化的目标背道而驰。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几任苏丹的办法是:改革要进行,苏丹的权力不但不能受限制还要强化。结果是,经济、法律、教育改革取得许多“标志性成果”(编制国家预算,建立国家银行和私人银行,废除包税制,改革土地制度,发展商业;设立混合法庭,颁布民法典、商法典;颁布教育法,开办新式中小学和大学),但政治上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比改革前更加集权,以至于被后人批评为“独裁式的现代化”。
再看奥斯曼帝国各阶层对待政治改革的态度。就算各个阶层起初都支持改革,并且热情很高,为什么后来又变得不热心甚至反对呢?首先,帝国改革的两道法令涉及政治权利方面的东西,并没有落到实处。改革派描绘的改革蓝图,依然停留在纸上。经济、法律、教育等领域的改革,得到实惠的毕竟是少数人。理想与实际的反差,浇灭了一部分人的政治改革热情。其次,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西方人和后来的土耳其人评价很高的“进步原则”(法令中提出的“权利”、“平等”)倘若落到实处,有多少人需要,有多少人欢迎?
“坦齐马特”时期的法令颁布后,享有特权的穆斯林的反应是:非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等)怎么能和穆斯林平起平坐呢?有的穆斯林认为把特权给予非穆斯林是不合适的。穆斯林知识分子援引“沙里亚”(伊斯兰法)说,把权利让给基督教徒,是与神圣的伊斯兰法则相违背的。落实改革措施的过程中,宗教界人士也必须纳税(本来除了宗教义务“天课”外不向政府纳税),政府坚持征收人头税,宗教界人士严厉指责改革。在旧制度下独享特权的穆斯林包税人、商人也批评新政策。连那些普通穆斯林青年,也觉得让基督教徒加入政府军队不合适。服兵役是穆斯林尤其土耳其穆斯林的神圣权利,新法令宣布“服兵役是帝国所有臣民的义务”,土耳其穆斯林不乐意接受。传统奥斯曼社会的臣民划分是:穆斯林、迪米人、非穆斯林、外国人。改革引进新的社会群体划分方式,不以宗教信仰来划分民众,而以“奥斯曼人”取代传统的划分,也让特权阶层不高兴。
法令宣称提高非穆斯林(如基督教徒等)的地位,也没有使他们满意。他们的愿望,并不仅仅满足于在法令上与穆斯林平等,他们需要与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地位,哪怕保持旧制度也能维护特权。比如希腊基督教徒,在奥斯曼帝国多年的“米勒特”制度下,他们在基督教社区中享有特权,一旦“平等”,优势和特权就丧失了。所以,非穆斯林的真实愿望,要么是保持传统特权,要么取得新的特权,总之要保持优势地位,维持“不平等”才对他们有利。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就不甘心当帝国境内“平等成员”中的一员,欧洲国家不停地向苏丹施压,要求“妥善处理帝国境内基督教徒的地位问题”,民族主义者在煽动“自治”和“独立”。
对企业主、商人而言,新政策确立了新规则,限制了他们获取利益的途径。以前他们通过寻求上层“保护伞”来获取垄断利益,往往不存在这个“准许”那个“规则”的,一旦失去特权,他们的利益会受损。另一方面,改革法令允许外国人在苏丹管辖的范围内持有、购买、处理不动产,这也冲击了国内富有阶层的“固有领地”。
可见,政治改革的目标没有问题,但改革的措施真正推行时,不仅特权阶层反对,连普通民众也有意见,因为大家发现:“平等”原来不是个好东西!事实上,“平等”并不是所有人的愿望;每个人真正的愿望是自己始终高出别人、优越于别人。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在土耳其人的皇权统治下生活了几百年,等级固化,意味着利益分配方式固化,这就是一八七八年之后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推行独裁三十年的民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看来,“限制君权”,苏丹不高兴,实行“平等”,各阶层有意见,那就只能退回到皇权时代,维持“不平等”,大家相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