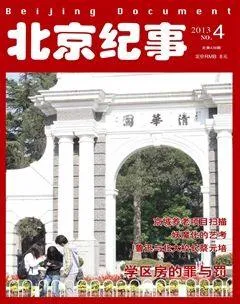陈长芬:在艺术的世界里醉生梦死
2013-12-29易浠
他坦率爽朗,脾气有点暴躁,他爱喝啤酒爱听音乐爱登山爱打高尔夫,他的一生几乎都在山川日月中穿梭,在艺术的世界里醉生梦死。他说:“人只有在大的空间下,才能学会爱社会与自然。”他是一位70岁的古稀老人。他是“中国长城摄影之父”——陈长芬。
时光如一把锋利的刀,打磨着岁月的痕迹,蹉跎着一个又一个有梦的人,后起之秀便如雨后春笋般冒出。50多年过去了,岁月的淬炼下,任何人可以被淘汰,然而老爷子陈长芬却立于摄影界数十年不倒,犹如他镜头下的万里长城。
自1959年起,陈长芬便与摄影有了不解之缘。1965年,他开始拍摄长城,近30年里,数十幅作品被国外收藏。他是第一个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华人,为纪念摄影术发明150周年被评为世界十大摄影名人之一。“在中国摄影界,一幅作品能够拍卖至40万,大抵也只有陈长芬了”。一位著名评论家这么说。
此时,雪莱口中的春天悄然来临。老爷子陈长芬头戴印花纱巾,梳着小马尾,眼神流露出逼人的光芒,“按照我说的方向走就能找到这个地点”,他边走边大声说着,步子迈得极大。他是一个时尚的小老头,也是一个脾气有点暴躁的老爷子,更是一位倔强执着的老人。这个阅历丰富的70岁古稀老人,别具一格的思维——对艺术的执着,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
以镜像与光影迎接“绿问”
自1977年开始,陈长芬将世人眼中具有封建韵味的长城用镜头语言表现出来,震惊了当时的中国摄影界,进而撼动了世界,他带着中国长城走向了世界。外国人对于中国长城的最初印象,就来自于这一系列以长城为题材的作品。他的作品恢宏、大气、逼真,被誉为镜像与光影的完美结合。
1989年8月,为纪念摄影术发明150周年被评为世界十大摄影名人之一,陈长芬的肖像被刊登在美国《TIME》杂志的特刊封面上。对长城给他带来的荣耀,老爷子不屑一顾:“我追求的早已经不是物质世界,而是凌驾于物质之上的精神境界。”熟悉老爷子的人都知道,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去一次长城,几乎风雨无阻,拍摄长城早已由爱好变成了一种责任。
自1965年至今,陈长芬拍摄长城整整47年了。当被问及“长城这个题材还会继续拍下去吗?”时,陈长芬的表情不容置疑:“毫无疑问!”长城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积累与沉淀,他的责任就是赋予长城更多的艺术内涵,改变长城在人们眼中的固有形象——封建,“我想让长城在我的镜头下变得丰盈起来”,陈长芬说。这种精神境界,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人类的大爱——爱社会,爱自然”。
有了这个想法后,他渐渐不满足于长城题材,而是将触觉伸到了多个领域,诸如最开始他就涉足的山川、树木,甚至是类似纪实摄影的作品。当然,老爷子并不将拍摄诸如丢弃烟头在长城如此场景当作纪实摄影,他多次提过,也不会简单地界定“风光摄影”与“纪实摄影”。他说对于这两种摄影形式,难得糊涂的状态才是最好。可是,能表述他的“人类大爱”情怀用这样一件事可以证明——
那一年,他重新回到多年前就已经去过的一个地方,准备取景整片树木,兴冲冲地来到印象中树木成荫的场地。却不料,树木仿佛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询问当村居民得知,树被砍伐了,为了某种用途。眼前空旷的场地,萧瑟凄惨,透露出一股静谧的悲凉。老爷子愤怒了,怎么这样对待它们呢!于是,他去找当地的相关负责人理论,甚至投诉到当地政府。“它们也是有生命的!”老爷子沉默了一下,说道。
在老爷子的认知里,自然与人类原本是相依相存的,你给予它多少伤害,它将会给予你多少惩罚。此事对陈长芬触动很大。随后,这样的场景成为他艺术的一部分:树木的年轮,大雪过后的城市,甚至过火树的瞬间等。以陈长芬一人之力当然不能阻止毁坏自然的发生,他想用他的作品去警醒世人:这就是人类所做的事。2000年,影展《绿问》横空出世。当有人问他为什么取名为《绿问》,而不是《问绿》时,老爷子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没有资格问绿,绿受害了,只有绿有资格问我们!”
“也许今天这些事情都被我们忽略了,左边右边脚下的东西也自行省略,但我会看着左右,兴许还会倒着看,站在旁边看,这样我才能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与众不同的摄影人。”对于他关注大自然思维的形成,陈长芬总结道。
艺术至上的“诗人”情怀
老爷子陈长芬毫不掩饰他对海南的喜爱,尽管他说他在海南有未完成的事业。但这个事业随着他所谓“个人英雄主义”——“别人没想到的事,我愿意干,但别人想到了,我就不想干了。”——在作祟而不了了之。对于“个人英雄主义”这一可称为缺点的形容,老爷子满口赞同。
说艺术是陈长芬的生命这话还不妥,说艺术至上才贴切。自2009年开始,陈长芬就在写数码日记。有人嗅到了商机,找到老爷子,商量着出书。行,出可以,但不能带任何商业性质,老爷子拍板了。随后,第一本《陈长芬数码日记》横空出世,获得了良好反响。
然而,等到第二本的wWuFQSMIMLCVRoNud1YHFzwI8y3KqeRhJ6V8m0AGl3s=时候,老爷子写好了,版式弄好了,他却被出版商要求加文字,原因无外乎书的畅销、利益的驱使。这下老爷子说什么也不同意,“你们找错人了!”果断否决了对方的提议。“我没有那个时间,也没有那个意愿去弄这件事,还不如将这些时间放在我的摄影上,我成不了作家。”老爷子提高了嗓门。他说他写的都是打油诗,是概念性的东西,不成诗句,但他承认这样的文字也能产生思考和魅力。尽管老爷子认为自己成不了作家,也不想成为作家,却有闲情逸致为自己的摄影作品写诗。
2011年底,在《左右贰仟年》画册上,他这样写道:“坐在电脑屏前凝视着南齐时代的弥勒大佛,鼠标器将菩萨头上、肩上的尘霾修掉,结果已不再是我相机里的菩萨了,于是我用‘不覆盖’的方式还原了图像的本来面貌,菩萨又笑了……”这是真的艺术,抑或艺术的真?两者都是。“不覆盖”的方式,老爷子的性情活脱脱地一个“不覆盖”。他可以为艺术写诗,绝不为商业屈膝低头。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老爷子就用简单清新的语言,在画册《魅力三亚》中,将他的诗人情怀昭然若揭。海南在他的描绘下,犹如诗歌一般既绝美又写实,有海滩、椰树、模特儿、天涯海角……《魅力三亚》中生动的镜头语言挣脱了禁锢的枷锁,华丽丽地跳出了画面。陈长芬用诗人的情怀追求着艺术的至高境界。至于艺术家如何修炼才能成为艺术家,老爷子坦言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不同的意识形态里,不同空间,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对于艺术家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他认为,这是个可以讨论的话题,但不能定义这个事情。否则,会耽误事,贻害人。
“真假大师
只有自己能区别”
自年轻时候开始,陈长芬往返于各地,他在50多年里跑了世界70多个地方。“这个问题当初谈恋爱的时候都已经说好了,”老爷子说早已经与家人达成共识。当然,他领略了各地风光的同时,还带老伴一起四处旅游,事业家庭两不误。
70岁的古稀老人,说话声如洪钟,句句掷地有声。找不到采访地点时,老爷子在电话里的暴跳,面谈之后的平和,就是真性情的陈长芬。他的爱好不符合这个年纪,他说他爱喝啤酒爱听音乐爱登山爱打高尔夫球,想提醒老爷子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可健谈的老爷子丝毫不给你插话的机会。
他表达自己对时尚摄影的理解,他不认为时尚摄影是对传统摄影的冲击,“做艺术从来不怕被取代。”他说,艺术是相互促进的,时尚能给传统带来活力,带来思考,并为传统增加一些现代元素,比如时尚,比如可读性。“任何事物的成功都是互相促进、刺激、碰撞的结果,任何类型的摄影,都具有时尚性。”
真实修行品学盖世的大师如凤毛麟角,特指在某一领域有突出成就、大家公认并且德高望重的人。外界称老爷子陈长芬为“真的大师”,老爷子听闻,只说了一句:“真的大师与假的大师只有自己能区别,别人没法区别。”还想再继续追问下去,老爷子已经不想多谈。
陈长芬的一生故事颇多,问他为什么不出自传?答:“这些都是无所谓的东西,人生越简单越好,让大家来留吧!”于是明白,老爷子早已不在乎名利,只在乎他所钟爱的摄影。
编辑/王文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