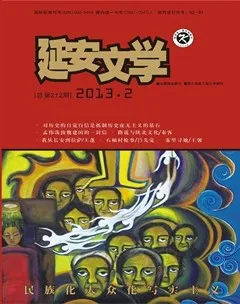愿每一个人都不被抛弃
2013-12-29古慷
隆冬季节,灰色的暮云压在头顶上。在县城各种车辆挤挤扎扎的街道边上,我接过了胜国的小说稿《我的前世今生》。我把稿子带回家,同时就好像把小说中的人物也领到了家中,无论我站着坐着,还是躺着睡着,这些人物总围在身边,想赶也赶不走——事实上,有些人物我想驱赶他们,而对那些可怜的人我却不忍心,好像留下他们我能给他们什么安慰似的。
在不少人做着中国梦的时候,作者却醒着说事,把生活的光鲜包装撕开,让我们看生活中的另一面。
这的确是一个特殊的区域。
小窑沟,是一个不遇大路但离县城并不很远的山村。一村人走得剩下两个人了,村里的小学没人了,墙塌了,厨房的锅拔了,学校大门上的锁锈得不成样子了,从前用来抽水上山的柴油发电机如今没用了,里面的柴油用来撒路灯埋人。一车又一车城里的建筑垃圾倒在小窑沟,小窑沟似乎和垃圾一起被人们抛弃了。
不过,小窑沟也有被人们关照的时候,在那个塑造形象的节点上,会有人来下乡送物送温暖什么的,送来个“火车头”,上面刻着“法律明白村”、“无污染村”等等荣誉。这些形象工程就像垃圾袋里拣出一瓶未开封的过期药,短暂情感波动后,免不了要被扔掉。那么,小窑沟以及类似小窑沟的村落会被“火车头”带向哪里?对小窑沟新来的“火车头”,小说有一段深刻的描述:“上面坡上有一溜儿破房子,跟火车头一搭配,恰恰就像一列拉着许多破烂东西的火车,也许是因为火车头放错了方向,整列火车看上去就要一头扎到沟里去了。”
这是一个被抛弃的群体吗?
小窑沟的老十石和老百石,是肯卖力,努力想走在人前的两代人,两个人都是老光棍,他们有着相同的命运。老十石搞过迷信,曾被政府严厉地管教过、“政治”过。后来天气变了,放开了自由,但他也老了,他已经走不动了。除过同病相怜的老百石,村里其他人离开他不记得他了,只有逢年过节回家上祖坟时,遇到他,才给他分一点儿祭食吃。他的干儿子办喜事,他托人赊得二斤猪肉去送贺礼,而干儿子并没有请他去吃喜。他也得到过上面来的救济,但上面更注重送物这种过程,至于什么人受用了物倒变得次要了。
老十石的存在人们是承认的,而对于老百石,人们连他的存在也不承认了。尽管他分辨说他是老百石,老十石和老百石是两个人,但人们仍然叫他老十石,人们似乎把他俩的名字当做穷老实疙瘩的两种符号,意义指向是一样的。到后来,连他自己也觉得他就是老十石,以前老十石做过的事也就是他老百石做的事。别人抛弃了他,连他自己也把自个儿抛弃了。
老百石也有被人们记起被关心的时候。下乡干部问他“对国家、省市县当前和未来的发展有何看法和想法,你——当然不是你一个人,而是你们村你们乡乃至整个全国人民,当前到底需要什么?今后到底需要什么?”但答案已给老百石拟好了:“国家都好,给村里修一条路,建一座桥。”在这里,群众路线只是舞台表演的道具,实际做事中,“路线”存在着,“群众”却被抛弃了。而面对如此的关心,老百石这样的人民群众只想说“我难活哩!”“我明天也难活哩!”
老百石和小窑沟一起被外面的人记起了,给他规划个美术写生基地来改变他的生活状况,看起来他明天不“难活”了,然而,美院教授要的“原始环境”和领导要表现的“秀美山川”能不能“和谐”很难说,小学校属小窑沟全村所有,盖一个章收十块钱的村长是什么态度说不来,老百石又太实在,更何况还有一大堆令人“难活”的问题会来,靠“基地”度日和靠老天吃饭没太大区别。
这篇小说我已读了五遍。如果阅读者仅仅对一个区域的状况和一些人物的命运慨叹同情,我想作者也未必满意,我们也轻看了作品的价值。作为读者,当隆冬的暮云压得更紧的时候,我开始了对我们今天农村乃至更大区域的反思:我们在哪里?我们往哪里去?无论我们走向哪里,愿每一个人都不被抛弃!
我喜欢胜国的《我的前世今生》,因为它是有用的文学,而不是无用甚至有害的文学。
栏目责编:张天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