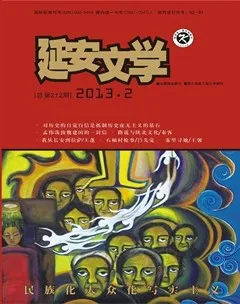眺望汉朝(外一篇)
2013-12-29孟澄海
孟澄海,甘肃山丹人,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散文》《福建文学》《延安文学》《山东文学》《西部散文选刊》等。
那个朝代远去了,两千年过去,滚滚的逝水长河足以湮没一切。当年的长城早已坍塌,当年的烽燧早已陷落,当年的城池早已变成废墟,当年的陵墓早已是寒鸦点点,芳草萋萋。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站在岁月的岸边,我们只有眺望,在眺望中聆听历史的回声,怀想大汉王朝的梦里河山、英雄气度。
汉朝的开国皇帝是刘邦。司马迁在其巨著《史记》中给了很高的评价。从他母亲身怀六甲,一直到他履践九尊,一生充满了神秘色彩。楚汉战争时期,他虽然没有项羽那种惊天动地的豪气,没有那种英雄美人、杜鹃啼血的浪漫情怀,但他凭着理性和智慧,打败项羽而平定天下。尽管有兔死狗烹、逐杀功臣的败笔,总体上还是任人唯贤、体恤黎民,不失为一个好皇帝。
我一直在想象刘邦黄袍加身后,荣归故里的情景。那应该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汉天子刘邦带着他的随从,仪仗威严,华盖摇摇,一路迤俪而入沛县。秋风萧萧,白云飘飘,他骑在马上,不时地抬起头来,仰望着空旷的蓝天,走着走着,突然就唱了起来:“大风起兮云飞飏,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不是诗,应该说是从他灵魂中飘出来的呐喊。铁马秋风,剑影山河,一切都成为过去。从此,华夏大地上,那个朝代就写上了一个“汉”字,中华民族也就有了辉煌灿烂的姓氏。就此而言,农民领袖刘邦的那几声呐喊,完全可称得上千古绝唱。
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从西汉到东汉,白云苍狗,星移斗转,近四百年岁月,汉朝先后有二十多个皇帝君临天下,虽然有作为的并不多,但大多还算勤勉,平庸却不昏庸。有汉一代,最伟大的皇帝就算武帝刘彻了,他的贡献不在于屯兵扩边,平定六合八荒,而在于用儒家思想统治人心,使社会走上理性的轨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近似独裁的做法,虽然扼杀了学术自由,但为封建社会的统一奠定了理论基础。另外,汉武帝还是一个有着开放意识的帝王,在他执政期间,多次派使者出使西域,把异国的物产、文化带入中原,也把中原的珍宝、技术、精神思想传播到西方。东西方文明互相碰撞,在武帝时期,闪耀出最绚丽的花朵。
认识汉朝,不能不说丝绸之路。这条从长安开始,一直辐射到欧洲的通道,第一次把中华民族同阿拉伯民族,乃至西方诸多民族连在了一起。通过丝绸之路,我们输出的不仅仅是精美的丝绸、锋利的铁器,得到也不仅仅是羌笛琵琶、胡麻胡萝卜,物产的交换,文化的交流,给华夏民族带来了蓬勃的生机。一条丝绸之路,有长河落日的壮美,有驼队马帮的悲歌,而漫漫的黄沙古道,浩浩的西风流云也总是张扬着一个朝代、一个民族的器量和胸襟。
民间传说,汉武帝夜宿未央宫,梦见天马行空,降临长安,翌日命方士占卜,言其马在西方,乃朝廷大吉大利之兆,于是武帝便派人去寻找,在敦煌渥洼池附近找到了一匹汗血宝马,汉武帝还为此写了一首“天马之歌”。民间传说无稽可考,我们可把它看作是一个隐喻。在汉武帝的精神世界里,他要经历的,是几十年时光的潮涨潮落,八万里河山的朝霞夕晖,当然也少不了异域他国的天地星辰,宝马香车。一代帝王的精神意志,有时候可以推进和改变历史的进程。
去河西走廊的武威,走进博物馆,我站在那个玻璃橱窗前,久久凝望:那个铜奔马,那个马踏飞燕的造型,以飞扬的姿势,体现出一种惊世骇俗的美。汉代的燕子,汉代的骏马,给人以无尽的遐想。两千年之前,也许是秋风萧飒的黄昏,也许是春雨霏霏的黎明,一个战士的坐骑突然抬头看见了一只飞翔的燕子,它仰天长啸一声,便追了上去。燕子凌空翻跃,骏马四蹄生风,那一刻,大地和天空上的两种动物,互相展示着自己的敏捷与矫健,比赛着速度和力量,流动的线条、和谐的韵律就那样定格在蓝天大地之间。
我还到过西安,去拜谒霍去病的陵墓。那一天,天空中飘着蒙蒙细雨,八百里秦川笼罩着淡蓝的雾霭,微风吹过,野草野花发出簌簌之声,如梦如幻。一代雄杰骠骑将军就长眠于此。墓地的周围是辽阔的田野,小麦刚刚抽穗,向日葵抚展开肥硕的叶片,金色的花蕾犹如灯盏,照亮那苍茫的岁月。
在武帝时期,霍去病和卫青是抗击匈奴的著名将领。霍去病曾带领汉军从中原一直深入到大漠边陲,跟匈奴打了几十次战役,在胭脂山下逐杀单于浑邪王及妻子阏氏,俘获其祭天金人。那一次战斗,使匈奴失去了美丽富饶的河西走廊,他们在歌中唱到:“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这是那个民族留下的最后一支惊天悲歌,千载之后,读罢令人怆然泪下。
霍去病17岁领军征西,死时才23岁,短暂的年华像流星划过天际,留下了绚丽的光华。他病逝以后,皇帝以最高的规格将其陪葬于茂陵。霍去病的陵墓仿祁连山建造,高大巍峨。墓前有马踏匈奴的石雕,还有石人、石象、石马。几千年过去了,这些石像依然守候着将军的忠魂,在岁月的风尘中凝望远去的英雄。我沿着墓道走过去,用手轻抚着那些冰凉的石雕,仿佛一下触到了大汉王朝的梦,看到了它的灵魂。那高大雄伟、状如雪山的坟丘,那浑然天成、不事雕琢的石像生,象征的是汉朝气象、汉朝的雄魄啊!就一个亡灵,就一个墓地,让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朝代的朗朗乾坤,以及云卷云舒、自在大气的景观。
翻阅史书,最喜欢看的就是司马迁的《史记》。我总是想,那个受过宫刑的文弱书生,是以怎样的意志完成了那部煌煌巨著?漫漫长夜,耿耿秋灯,他是怎样手握七寸竹管,蘸着心灵的血,描绘汉朝的大地生灵?后来查阅有关司马迁的资料,我突然明白了,是的,他是汉朝人,正是那个朝代的天地灵气,哺育了他杜鹃啼血、长虹贯日的精神气魄。一部书浓缩了一个朝代的历史,也张扬了个人的灵魂。鲁迅说《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既是对司马迁的肯定,也是对那个朝代的赞美。
那个朝代远去了。
那个朝代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精神奇葩:汉赋、乐府民歌、神话传说、壁画雕塑、琵琶曲、胡旋舞……
更重要的是给我们留下了恢弘磅礴的大汉气象。
我们是汉人,理应珍视那个朝代的民族精神。
黑河:深秋或初冬的影象
我坐下来。黑河从面前悄然流过。秋天,准确说是晚秋,流水很平静地映着祁连雪峰、云朵、鸽群、阴郁而伤感的杉树和白杨。衰草连天,冷风萧萧。一条河在黄昏的影子中缓慢前行,穿越田野荒漠,然后消失,像一个梦境,或者是留在梦境里的灰色飘带,轻盈、魔幻,迷迷茫茫。
面对黑河,我总有一种置身远古的幻觉:金橘般的夕阳从褐灰色的冈峦上滚落,点燃了河谷里的芦苇,绯红的火焰笼罩着水波。一棵胡杨撑开满身灿烂的黄叶,摇曳,闪亮,飘洒,坠落,让蝴蝶似的叶片覆盖刻有咒语的陶罐和铜镜。芦花飘荡的河岸上,月氏的女萨满赤身裸体,挥舞着剑,一边舞蹈,一边吟唱祭奠水神的歌谣……
风吹过来,风声很大,像有人在吹埙。幻觉中的事物没有轮廓。我看见一弯月牙,忧伤地挂在对岸的峰顶。月色下,只有起伏晃动的野草和灌木。一只狐狸在不远的地方蹀躞,偶尔抬起头,朝我张望,目光暗淡苍凉。商人?秦人?月氏人?鞑靼人?匈奴人?也许,狐狸就是先民的一个幻影,一个亡灵,从古到今,默默地守候着河岸,在这里等待那消逝的家园。月光回溯着以往的宁静,狐狸在暮色中渐走渐远。河床里的红柳雾气氤氲,暗影幢幢,恍若鬼魅。从胡杨树丛里望过去,我发现有一块巨大的页岩横卧河心,流水漫过石头,溅起隐隐水花。苍老的岸,苍老的石头,苍老的山河树木,那么,水呢?水流激石的时候,会不会有苍老的皱纹跌落在波心?
我不能描述黑河。黑河就石黑河,一条流淌了数亿万年的河,一条大西北普通的河,一条没有木船帆影的河,一条缺乏审美意义的河。黑河之于我,完全是偶然的机缘。若干年前的一个初冬,我从偏远的故乡出发,走进了祁连山北麓的荒原。我是来这里寻找诗歌的。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唐人留下的苍茫意象,给我心灵以巨大的震撼,使我第一次靠近雪山和漠野,第一次目睹了蛮荒而粗砺的沙滩与河流。那个冬天有雪。蝴蝶般的雪片落在荒草中,落在黑河边,落在石头上,但没有一瓣能落进我的心湖。热爱诗歌的我始终是干涩的,犹如长满枯草的河岸。我漫无边际地向前走着,在黑水国遗址,遇到了几个考古工作者。他们来自遥远的省城,一直驻扎在这里搞丝路文化研究,据说挖掘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物。在他们眼中,一片残陶和木箭,一个瓮棺和陶罐,一支鸣镝与箭镞,都能构成极富内涵的人文立面。而我苦苦寻觅的诗歌意象却杳如梦幻,甚或连一句在场的句子也没有酝酿成功。暮云合璧之际,我看见了平静如初的黑河,还有河边闪着磷光的鬼火,以及坟场,坟场中被风吹响的枯骨和骷髅。
秋风白露的季节,我又一次来到黑河边。这一次,我已经远离了诗歌和激情,内心的视角开始转换。不再多愁善感,见落日而伤情,闻秋风而伤感,怀古的幽思一点点崩溃、坍塌,如芦花草叶,随烟尘飘远。黄昏的天光里,黑河无声无息。在我目力抵达的地方,有几个农民正在拉运玉米秸,车子嘎嘎做响,人和牛都弓着腰,一副拖沓疲惫的样子。而他们的后面则跟着女人和孩子,还有毛茸茸的小狗,似乎在吵嚷着什么。从他们的头顶望过去,高处是庄园,比庄园高的是雪山,更高的就是天空和云朵。苍凉空阔的背景下,卑微的生命亘古如斯。这里似乎没有诗意的景象,除了艰辛苦难的农人之外,剩下的只有沉默的河,以及岸边的枯草老木。河滩被挖沙的民工占领,到处是心疼的伤疤。在我的面前,只有零星的野菊花在秋风中摇曳,瑟缩颤抖,若孤魂般幽怨。
我曾经在一本民间刊物上读到过一则故事:很久的年代,一个村姑恋上了黑水国的王子,但由于门庭相差悬殊,她无法走进那个深宫大院,后来相思成疾,卧病不起,死时便化做菊花的种子,随风飘进宫墙。从此,年年岁岁,在黑水国的土地上就有了深蓝或黑紫的花朵,经秋不衰,直到初冬才开始凋零。我一直不喜欢野菊花,因为那幻若月亮的花盘有太多的阴郁和伤感。相比之下,更钟情黑河岸边的蒲公英,即使在晚秋,那些洁白的伞盖依旧于风中闪烁、盘旋,让人想起白衣飘飘的剑客侠女。
距离黑河最近的城市就是张掖,那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风华绮丽,热闹非凡。元朝时,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游历河西走廊,曾驻足于此,用一双蓝眼睛打量张掖的异域风情。那个年代,佛教盛行,梵天净土的云朵擦拭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当然也不乏世俗生活的温情与浪漫:驿站、会馆、赌场、妓院,戍卒、商贾、诗人、嫖客,所有的场景和人物汇聚纷纭,构成别样的景观。但马可·波罗并没有留恋这里的风烟阜盛,在他的笔下,出现最多的词汇,依然是黑河,是黑河两岸破旧的茅舍,衰落的村庄,以及无家可归的乞丐和流浪汉。也许在他看来,河流是历史的记忆,千古兴亡之后,只有苦难的黎民百姓,才能洞见黑河亘古的永恒和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