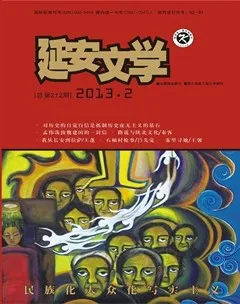雾里寻她
2013-12-29王馨

王馨,陕西清涧人。作品散见于《延河》《延安文学》等,著有散文集《秋在室杂记》。
朱淑真是我国古代唯一能与李清照并称的女作者。她生存的年代有北宋说和南宋说两种,据说她的作品“百不一存”,但仅凭《断肠集》收录的三百多首诗,三十多首词,她仍然是我国古代作品最丰富的女作者。
知道朱淑真的人并不是很多,除了从事专业研究的人和一些诗词爱好者,朱淑真,的确不在普通中国人的视野里。
其实,即使在朱淑真生活的那个年代,她也只是一位默默的写作者。
首先把淑真的作品辑录起来的是一个叫魏仲恭的人,这个魏仲恭同样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只知道他生存的年代与淑真相近。魏看到淑真的作品时,淑真已经不在人世了,而她的诗词却在民间传播开来。魏因爱淑真之才,惜淑真之逝,便下决心把这些流散的作品收集整理,“聊以慰其芳魂于九泉寂寞之滨”。因为淑真诗词中多处出现“断肠”二字,便取书名为《断肠集》。
遗憾的是,魏仲恭并没有为我们留下更多淑真的生平资料。他在《断肠集》的序中说,当时已有人为淑真作传,所以他在序中就省了笔墨。然而,他提到的这个传记,却并没有流传下来。
于是,朱淑真辞世不久,她的生卒和她的经历就成了谜。
不过,我们应该都熟悉这样一首词: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透。
《生查子·元夕》
这首词就出自朱淑真的《断肠集》,但也收录在欧阳修的文集里。自古至今,人们一直在考证它的作者。不过从词的风格和意蕴来看,它应该属于淑真。
生于寻常巷陌
宋朝是文人的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文化气息的朝代。从宋朝开始,士大夫阶层的闲情逸致得到极大地拓展,逐渐形成了诗、书、画、印一体的文人艺术,也诞生了一批伟大的艺术家。这对于当时的社会无疑具有极大的影响和带动力量。
朱淑真出身于寻常人家,这可以从《断肠集》序和朱淑真的诗词中看出来。当然,她的家境应该不错,父亲可能有点儿官职,也属于当时的士阶层,所以她才有可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精诗词,擅绘画,通音律。她的诗词有韵律美感,适于吟诵:
淡红衫子透肌肤,夏日初长水阁虚。
独自凭栏无个事,水风凉处读文书。
《夏日游水阁》
她的丈夫也是一个小官吏,夫家生活是比较优裕的,所以她出嫁以后不用为柴米油盐耗费心神,才有可能整日吟诗赋词,留下丰富的作品。
但是,正因为她出身普通,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史上,她反而成为一个特殊的个体。
她和班昭不同(没有谁可以和班昭比)。班昭是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她替兄长班固最后完成了《汉书》,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最著名的一位女历史学家。不仅如此,她在世时与东汉皇室联系密切,备受皇室的推崇和尊重,不仅参与政事,还被奉为师表。她撰写的《女诫》,被誉为《女四书》之首,是万世女则之规。千百年来,班昭以女圣人的形象,成为女界典范。
她和蔡文姬不同。文姬的父亲蔡邕是东汉大文学家、书法家,与曹操是挚友,文姬因此受到了曹操的关注,而曹操的关注使得文姬和她的故事得以流传。
她和李清照不同。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是北宋大文学家,号称苏门“后四学士”,官至礼部员外郎。其夫赵明诚之父赵挺之,官至吏部尚书、右丞相。李清照、赵明诚门当户对,诗文俱佳,兼为金石学家。所以李得以结交达官贵人、文人雅士,诗词应酬,青史留名。
她当然更不同于薛涛、鱼玄机。她们可以以自己特殊的身份,自由地穿梭于男性社会,借着频繁调迁的官吏和四处游历的文人,也借着与他们演绎的缠绵悱恻的情爱故事,她们得以艳帜高张,才名远播。
纵观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踪迹的女性,不外乎两类人。一类是名门之后(包括宫室后妃),一类是青楼倡优。只有她们,才有条件接触闺阁之外的世界,与上层社会的男性诗词交往,虽然她们中有人最终的成就已经远远超越了她所依仗的男性,如李清照,但在当时,如果没有男性的支持和宣传,她们不可能被男性社会发现、认识,最后载入史册。
即便是这些女性,也绝少能留下完整的生平记录,很多人只有寥寥数首作品传世,姓名也是“某夫人”,一个模糊的姓氏符号而已。
平民身份的女性作者的名字被频频记录,似乎是十七世纪才开始的。明末清初,随着弹词小说的盛行,在中国江南,第一次出现了女性创作群体。她们像男性文人一样,结社、聚会,互相交流,互相鼓励,形成了女性自己的文化圈。女性作者终于走出了闺阁,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作品向社会展示。她们开始怀着明确的目的,自己刻印作品,使之得以传世。对某些女性而言,写作,再也不仅仅是女红之余的游戏和排遣闺怨的手段,而是能带来经济收入的职业。职业女作家开始走进历史,中国有史可查的才女文化第一次有了普遍意义。
但淑真不能等到那个时候。她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一个寻常人家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凡夫俗子,过着庸碌的生活。她真切的身世背景虽然已经模糊,但毕竟,和千百年来被完全湮没的无数民间才女相比,她还是幸运的。
人们大概还是更希望淑真有一个显赫的出身,平民阶层的女性,似乎连姓名也不应该被铭记。因为她籍贯浙江钱塘,又是朱姓,便有人把她考证为朱熹的侄女。年代倒是相近,却太过牵强攀附了。
我宁愿相信,是平凡的出身让正史遗忘了淑真,让时间模糊了她的身影。但她不平凡的思想和情感,她卓尔不群的行为和品格,最终使她的名字、她的作品流传下来。让千百年来爱她的人们为她流泪,为她感动,为她辨白,为她拨开重重迷雾,让她重现人间。
吟尽千年孤独
第一次读淑真的诗词,让我触目惊心的,不是多次出现的“断肠”二字,而是一种浸透心肺、深入骨髓的孤独。
独行独坐,独倡独酬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轻寒著摸人。
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
《减字花木兰》
五个“独”字的连用,只属于淑真。是绝世的文采,也是绝世的孤独。
一生孤寂的淑真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悲剧的起因是:“早岁不幸,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乃嫁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郁不得志”(《断肠集》序)。
世上有几许婚姻是情有所归的?更何况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人世间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忍与不忍,幸或不幸,同样的际遇,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结局。而在淑真,这是她一生孤独的开始。
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
东君是与花为主,一任多生连理枝。
《愁怀·其一》
就像把鸥鹭和鸳鸯同池喂养,天公乱点鸳鸯谱,把本不同类的人儿硬拴在一起。若是真有司花的神灵,花儿应该都是连理而生啊。
然而纵便是奇花异葩,也不见得人人欣赏。从淑真的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的丈夫并不以有一个才女为妻感到欣喜。所以淑真只能无奈地自责:
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
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
《自责·其一》
闷无消遣只看诗,又见诗中话别离。
添得情怀转萧索,始知伶俐不如痴。
《自责·其二》
她是遇到了一个怎样愚鲁无趣的人啊,以至于让一个冰雪聪明的女子,恨自己“伶俐不如痴。”
有人说,淑真所嫁之人乃一俗吏,整日处心积虑为前程奔忙,根本无视淑真的存在。也有人说,此人宦游离家,淑真长年独守空房。但这些应该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在我国古代,丈夫为科考为仕宦为经商长年离家,数年没有音信,以致孩子没见过父亲,夫妻相逢不相识,都是平常的事。淑真不是耐不得寂寞,她的心志,绝不低于李清照。李清照有诗:“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淑真也有诗:“劲直忠臣节,孤高列女心。四时同一色,霜雪不能侵。”同一时代的两个女子,不一样的人生际遇,但都是才自清明志自高,也都因了绝世的才情而招致后世的非议。“自汉以下女子能诗文者,蔡文姬、李易安失节可议。朱淑真者,伤于悲怨,亦非良妇。”(明·董榖《碧里杂存》)便是文姬、易安,也要因为再嫁屡屡遭人非议,何况淑真?
淑真的婚姻是不幸的,不幸的婚姻让人生变成了一杯独饮的苦酒。同床异梦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她的丈夫宦游离家了,或者,他们因为矛盾激化而分居了,或者,如某些考证所说,淑真最终离婚独居了。总之,我们从淑真的诗文中,读出了她的孤独。
背弹珠泪暗伤神,挑尽寒灯梦不成。
卸却凤钗寻睡去,上床开眼到天明。
《无寐·其二》
熟读诗书、吟风弄月的淑真是倔强的,既不甘心与庸夫俗吏厮守一生,也没有抛掷了笔砚,收敛了性情。只身孤影的外在处境,寂寞无助的内心世界,让淑真从此以文为友,为我们展示出一个极其细腻的闺阁世界。孤独,成为她文学创作的最大动力。
也正是因为婚姻的不幸和欠缺,在“独行独坐,独倡独酬还独卧”的日子里,淑真一直怀着一份渺茫的情感寄托。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不仅仅在于它是一份不被认可的感情,更严重的是,这件事最终被迫公开了。
淑真婚姻之外的感情际遇,也是历代做研究的人,在她生平之外最感兴趣的问题。
清代大学者纪昀在《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断肠集》中为淑真辩解,说《生查子·元夕》的作者不是淑真,而是欧阳修,所以淑真是贞洁的。
我相信纪昀是因为爱淑真的文采,怜淑真的苦情。在他看来,淑真的这段感情,无疑是大逆不道的,所以,他想以舍弃一首传世的佳作来为淑真作掩饰。
但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之外,淑真的情仍充溢在字里行间,不是不想掩饰,而是性情使然。
淑真确是在婚后发生了一段即使在今天也不会被看好的恋情。
她遭遇了一个怎样的人呢?
门前春水碧于天,坐上诗人逸似仙。
白璧一双无玷缺,吹箫归去又无缘。
《湖上小集》
春景宜人的三月里,我与那个可以诗词应和的他相会在花厅水榭。水天一色的背景下,坐在我对面的他,像仙人般俊朗飘逸。无意间的一低头,我看到了水里的影子,我和他,就像一对白璧无瑕的玉人,映衬这湖光山色,令人心驰神往。这是多么美好的画面啊!可我们缘分仅此而已,我们的分别是命中注定的啊。
人都说纳兰容若是用情至深的公子,但他在诗词中对意中人仅有一句描述:“天然绝代”。知道朱淑真的人,都知道她是为情而死的痴女子,她对恋人的描述也只有一句:“坐上诗人逸似仙”。情到深处反无言。
这个被淑真像神仙一样尊崇珍爱的人,是值得淑真悖逆封建伦常、付出生命代价的人吗?
斜风细雨作春寒。对尊前,忆前欢。曾把梨花,寂寞泪阑干。芳草断烟南浦路,和别泪,看青山。
昨宵结得梦夤缘。水云间,俏无言。争奈醒来,愁恨又依然。展转衾裯空懊恼,天易见,见伊难。
《江城子》
如此难得相见的恋人,是环境使他们不能相见?还是他们之间的爱并不平等,淑真之于他还不够珍重?
尽是刘郎手自栽,刘郎去后几番开。
东君有意能相顾,蛱蝶无情更不来。
《西窗桃花盛开》
无望的等待,不尽的惆怅。
一段没有结果的恋情。
最终,淑真选择了赴水而死。时年约40岁。
淑真的死,有人说是因为私情终于被揭露。在那个时代,死是唯一的选择。还有一种可能,那个她一直守候的人,最终背叛了她。淑真,为了一个始乱终弃的男人,了断了对尘世最后的牵挂。
一切都只是猜测。没有人能知道淑真遭遇了什么,承受了什么,她是在什么样的境况下毅然诀别了人生。
她的父母,在她死后,不愿女儿再遭人诟病,一把火焚烧了她的文稿。所幸有喜爱她诗词的人已经口口相传,致使部分作品流传开来。
“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传者,百不一存。”(魏仲恭·断肠集序)
一个女子,被命运安排,在不适宜的时间,遇上一个她以为最是适宜的人,于是注定了一场不适宜的爱恋。
世间什么样的人最孤独?心里有爱,相见无期。
我相信,因为这份爱,淑真从内心彻底放弃了已有的婚姻,放弃了世俗的生活。也正因为此,注定了她一生外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完全孤独。
犹见女儿本色
据说淑真是美丽的,和她的诗文一样,本色自然。这个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女子,她独立的精神,不同流俗的品质,她对爱的牺牲精神,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加矫饰的本色女儿,她的经历和诗文都有着更鲜明的女性符号。
喜欢淑真。一个痴情的女子,一颗至真至纯的女儿心,还有着对爱完全付出的勇气。她曾写过一首极放任极可爱的词:
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
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
《清平乐·夏日游湖》
这样的清新自然,并不输于李易安前期的词,大概只是因了不合礼教,才流传不广。
也喜欢她毫不做作的女儿气。古来爱诗文的女子,多有刻意学男儿状,回避脂粉气的。可淑真不然。
巧云妆晚,西风罢暑,小雨翻空月坠。牵牛织女几经秋,尚多少、离肠恨泪。
微凉入袂,幽欢生坐,天上人间满意。何如暮暮与朝朝,更改却、年年岁岁。
《鹊桥仙·七夕》
秦观说“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千百年来,不得长相厮守的人,就用这一句豁达的空泛的“长久”的许诺,来安慰自己,放弃对现实感情的需求和渴望。但一个真实的女子对爱的期盼,却恰恰就是“朝朝与暮暮”。不想知道明天,不敢寄望于未来,只想紧握此刻。旦夕的拥有,比虚妄的“永远”要幸运,那才是真实的,确切的。也只有“朝朝暮暮”的相守相伴,才能创造年年岁岁的永远。
所以,自古就有人评价淑真与其他女性作者不同。即便婉丽如李清照,因为有较强的社会参与意识,所以作品更具男性文化特征。而淑真,即便她“浅弱不脱闺阁之习”(《四库提要》),但她具有典型意义的痴心女子的形象。她纯粹的毫不功利的自我表达的创作目的,和对女性内心世界极其深微的展示,让我们相信,她更具女性代表意义。
怜惜淑真。一个美丽的女子,一个“颜色如花命如叶”(《断肠诗集》序)的女子,连明月都怜她孤寂一人:
山亭水榭秋方半,凤帷寂寞无人伴。愁闷一番新,双蛾只旧颦。
起来临绣户,时有疏萤度。多谢月相怜,今宵不忍圆。
《菩萨蛮·秋·其二》
读她的诗词,仿佛看到这个宋朝的女子,正一个人行走在生命的旅途中。一个人填词,一个人吟唱,一个人出行,一个人归宿。她是爱恋世俗生活的,春花秋月,湖光山色,都在眼底。只是形单影只,无人相伴,她不得不风雨自担,风景独品。
夜半不眠时,听更深漏残,倚窗望月,泪湿清梦。
哭损双眸断尽肠,怕黄昏后到黄昏。
更堪细雨新秋夜,一点残灯伴夜长。
《秋夜有感》
谁家横笛弄轻清,唤起离人枕上情。
自是断肠听不得,非干吹出断肠声。
《中秋闻笛》
这是淑真真实的生活。远离了俗世的喧嚣,也远离了俗世的温暖。让人心痛。
而淑真心中那个“逸似仙”的不知姓名的男人,他在淑真赴水之后应该还活了很多年,也许还福禄双全,儿孙满堂。
值与不值,都是淑真自己的选择。她爱过,想必也恨过。她争取过,她也付出过。在她,名誉和生命并不是最重要的。
敬佩淑真。一个生活在千年之前的女子,在大理学家朱熹的时代,在传播“存天理,灭人欲”思想、把封建儒学推向顶峰的时代,她的诗文纯真,诚挚,深婉,细微,她的表达本色自然,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性真情的女性角色:
初合双鬟学画眉,未知心事属他谁?
待将满抱中秋月,分付萧郎万首诗。
《秋日偶成》
那个时候的她,尚待字闺中,还是一个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少女。她是勇敢的,敢于用白纸黑字描绘自己美好的爱情理想,想象自己未来的伴侣,和一份佳偶天成的诗意生活。只是,这样的理想和希冀,也注定了她悲剧的一生。
她有清醒的自我意识,那些专为女性设置的规则,不能埋葬她对爱对生活的憧憬,在那个时代,她无疑是一个叛逆者。当发现执子之手的那个人,不是她才华横溢风采照人的萧郎,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以飞蛾扑火的姿势,迎接了这段恋情:
火烛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
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
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
赏灯那得功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
《元夜·其三》
虽然一般人们关注的都是她为之断肠的感情,但她的作品不仅仅局限于闺阁。她的悯农诗在古代女性作者里也是比较少见的:
日轮推火烧长空,正是六月三伏中。
旱云万叠赤不雨,地裂河枯尘起风。
农忧田亩死禾黍,车水救田无暂处。
日长饥渴喉咙焦,汗血勤劳谁与语?
播插耕耘功已足,尚愁秋晚无成熟。
云霓不至空自忙,恨不抬头向天哭。
寄语豪家轻薄儿,纶中羽扇将何为?
田中青稻半黄槁,安坐高堂知不知?
《苦热闻田夫语有感》
她生命的光彩,我们只能从她百不一存的诗词中窥得一二。这个生在宋朝的女子,对于后世的人们,是一个永远的谜。
相对于她的生,她的死是真切的。纵身一跃,随水而逝。
一个“才也纵横、泪也纵横”的美丽女子,一段不寻常的情感,一个不寻常的结局,在当时,一定是具有轰动效应的街谈巷议的话题。于是,她的诗文才得以口口相传,留存民间。所以她的幸运,是源自她的不幸。
断肠诗词被收集成书不久,很快又被浩瀚的文字典籍湮没。直到数百年后,明朝人杨士奇在整理古籍时偶然发现了它。于是,《断肠集》第一次被收录在《文渊阁书目》中。这,也是自宋以后,后世的人们第一次知道朱淑真。
又过了很多年。我在翻一本词典时,无意中注意到朱淑真的几首词,便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女子方可有文集取名“断肠”?
我开始寻找她,在旧书店尘封的角落里,在历代文集和诗评里,寻找她的各种文本和关于她的哪怕只言片语的文字。
浩瀚的书海里,她只是一滴水珠。
便是那一点零星的记载,也只是后世的揣测和想象。隔着久远的年代,我只能看到她朦胧的影子,如同雾里看花。真真切切的,只有她的诗词。
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千年的毁誉,只是从她身边轻轻地掠过。她留下了足够的空白和缺憾,给我们无尽的遐思。
读她的诗词,想她的故事。
仿佛看到她,伫立在千年的秋色里,绝世孤独,绝世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