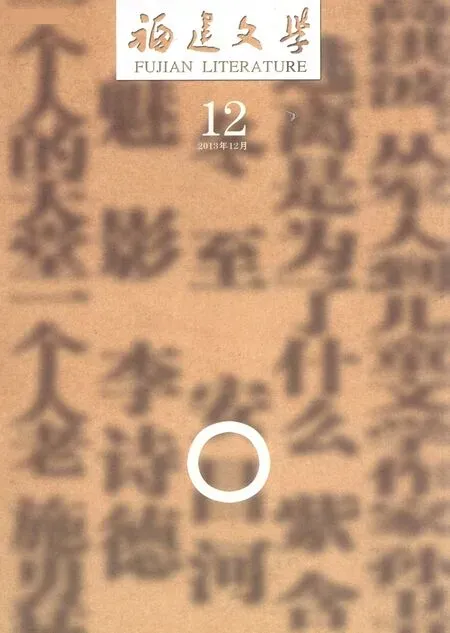逃离是为了什么——读爱丽丝·门罗小说《逃离》
2013-12-15□紫含
□ 紫 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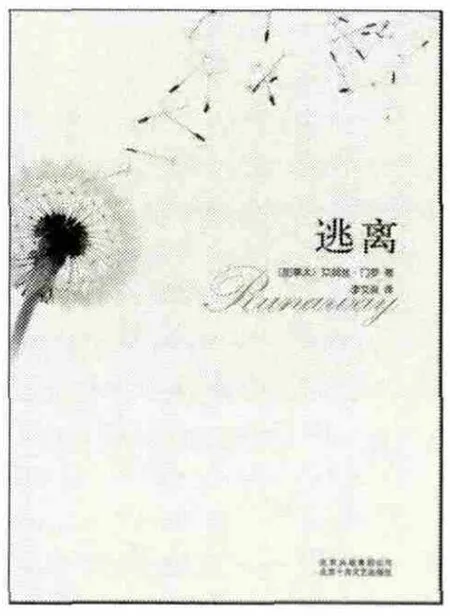
2013年10月10日下午17点45分,我在微信朋友圈分享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空间》,并写下“我希望获诺奖的是她”这样的话。一个多小时后,门罗获奖。
意外的惊喜冲击过后,涌上来的是长长的欣慰。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件与我无关的事,即便我许下的愿望奇迹般地得以实现,我仍然无法抹去写下这个愿望时不报希望的真实心态。
然而门罗获奖了。然后一切突然有了变化。我望所归,小W说,彼时我们正一起吃晚饭。三年前,他向我推荐爱丽丝·门罗。三年后,我们聚在一起,为门罗获奖干掉了杯中的酒。
仅仅用“笔触简单朴素,但却细腻地刻画出生活平淡真实的面貌,给人带来真挚深沉的情感”描述爱丽丝·门罗的小说是有些随意的,这样的标签可以贴在任何一个成熟作家的身上,而抹去门罗作品的真正价值——真正回归传统的英文小说。如果说小说创作最能代表文学的意义,那么所谓的文学的意义,或者说本质到底是什么?
时隔三年,我依然可以清晰地记起门罗小说里的主人公,几个小镇的女性,有姑娘、已婚的妇人、单身的大学女老师、安静的小镇护士,她们出现在一本叫做《逃离》的中短篇小说集里,这也是获诺奖之前门罗在国内翻译出版的唯一一本小说集,全部写于2004年门罗七十多岁时。她们总处在逃离的渴望中——已经谈婚论嫁的姑娘突然和一个陌生的男人出走了一个下午;单身的大学女老师仅仅因为一封信,一个火车上遇到的男子,便去了他的小镇;一个从母亲身边逃离到丈夫身边的女人,有一天突然坐上车子,想再一次逃离;去城镇观看了歌剧回来的小镇护士,每天都要熨烫一次那天她穿过的绿色连衣裙,她答应那个歌剧院边上一家小店里的男主人,要再穿着这件衣服一起再去看歌剧,她去了,回来了,没有再离开过小镇,可也没有停止熨烫她的衣服……
可是逃离是为了什么呢?
现实生活不仅是平淡的,还夹杂着不宜察觉的扭曲,或者说,处于平淡中的人们不愿意正视扭曲。毋庸置疑,现实远比小说惊悚,比小说变态,比小说精彩,可为什么人们从现实中得到的直观感受,远不如将事件本身进行再创作后更能带来心灵的震撼和思索呢?一个成熟的作家,要做的,不正是通过语言和架构,引导人们走入原始的蛮荒之地,从那里回过头来,借助那股黑暗烛光般的温暖和微亮,深切地看到、触摸到自己和外界的关系,感受到在波涛一般的人与人之间,有着相通的一种东西?
我们微妙地连接了,相联系,却又清晰地彼此分开——人生就是如此荒谬,却又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温暖,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荒凉,可荒凉之地又处处是令人心荡神驰的美丽风景——生活是用来长久的深长的回味的,所以生活不管怎样都始终透露着温情,哪怕再诡谲再扭曲,都有其存在的独特性和共性。门罗小说给我的感觉,正是如此,一次次的逃离,自觉地,不自觉的,其实不是为了寻找,为的都是回归。
从这个意义上说,门罗的获奖也是一次文学根本的回归吧。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买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小说,翻开,读几页,放下,又翻开,又放下,我觉得那些过于庞大的叙事和架构,有关人类、国家、社会命运的宏大主题,不仅让我这样的平凡阅读者难以深入,产生望而却步的畏惧,更无法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抵达我的心灵,让我真切感受到我和这个世界到底有着怎样的一种纠缠?
逃离,抑或回归,只是门罗这本小说集所要告诉我们的,因为没有阅读过她早期的中期的小说,我无法得知她全部的思想和创作全貌,但是回归传统,回归到一种人性深层次的渴望,回归到温暖的意义,应该是整个人类追求的终极吧,一只蚂蚁也好,一个蝴蝶也罢,不都是这样平淡而惊心动魄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吗?普世的,一定只有阳光,而阳光下,所有的一切都散发着只属于自己的光芒——对普通人来说,这是最小,也是最大的归属。
《逃离》中的女性都生活在小镇,如同门罗自己一生生活在加拿大一个安静的小镇一样。《逃离》中有一篇小说写的是一个母亲总是在寻找自己的女儿,女儿总是会在某一个生活过的地方留下蛛丝马迹,但当母亲到达那里时,女儿又去了另一个地方。是什么使她们害怕见面?见面又能改变各自有着自己生活的她们什么?母亲明知道女儿不愿意现身,可还是固执地细心地找寻着她的气息……这样的故事能说明什么呢?这样的事情也许一生也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可是,读着读着,是不是就有那么一根弱得像游丝一般的、几乎不存在的线,轻轻地从我们的心上划过?就像小说《逃离》里,从母亲身边逃离又从丈夫身边逃离,最终又回到农场,和丈夫一起经营的卡拉一样:“她像是肺里什么地方扎进去了一根致命的针,浅一些呼吸时可以不感到疼。可是每当她需要深深吸进去一口气时,她便能觉出那根针依然存在。”
这样的感觉,你敢说你从没有过吗?
但门罗并不仅仅是以身边的许多女性写就一部部小说,现实远比小说精彩,门罗的小说并没有太多的曲折故事,她并不关注发生了什么,她关注的是事件发生的各种方式——换句话说,她的小说每篇都有着精心而精妙的安排,这其中甚至包括段落间的空隙——她很少使用我们常见的数字分节,而是用一些段落之间的空隙来达到停顿或者转折的作用,除此之外,她喜欢使用破折号——正如此时我频繁地、不知不觉地使用大量破折号一样,这使她的小说有股郑重其事的英文小说的传统味道,但她又是行文无形,不滞缓,不啰嗦,有些地方甚至显示着悬疑小说般的扣人心弦——她笔下的故事,大部分其实是相当吊诡和扭曲的,然而就像一个人说出什么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出这句话时这个人所处的环境、心境、情绪及情感一样,将隐藏在线性事件后面所有不可言说的东西表达出来,让人进入到一层又一层的连绵不绝才真正显示出事件的厚重一样,我总是被她带动着走进她的语境中,在那里展开我自己的联想,涌上我自己的感受。这种感觉非常绵长,像黄昏时落个不停的雨,一直要落到深夜里去。
门罗获奖的意义或者就在于此吧——她让诺贝尔文学奖具有了平凡又不平凡的意义,她应该可以大面积地走进阅读者的视野,她的小说的受众性应该是非常宽广的。这也是作为一个作家最高的期待吧——他(她)所要做的,只是引导你,引导你进入一个世界,那是你的世界,也是他者的世界,而不仅仅只是带给你一个世界。
而在某一种意义上,我还觉得门罗的获奖是对传统英文小说的温柔回归。
记得读完《逃离》后,与文友弱水有一次QQ聊天,我向她推荐爱丽丝·门罗,我说,请读读这个七十多岁的女人写的小说吧,我们全体写小说的,国内的,有名的,无名的,是不是都会感到汗颜?我们是不是都该想一想,认真地、精心地写一部小说,到底有多重要?
也记得读完《逃离》后,去网上搜索相关资料,当时阅读她的人不多,但还是有许多喜欢她的人。我对她一见钟情,再难忘记。《逃离》出版于2009年7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译者李文俊遇见爱丽丝·门罗小说时,也已七十多岁,他长门罗一岁,据说他遇到她,也是纯属偶然。书出版时,没有序,没有后记。她在扉页上写道:“为纪念我的朋友,玛丽·卡莱,吉恩·理弗摩,梅尔达·布坎南。”如今想来,这空白竟是颇有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