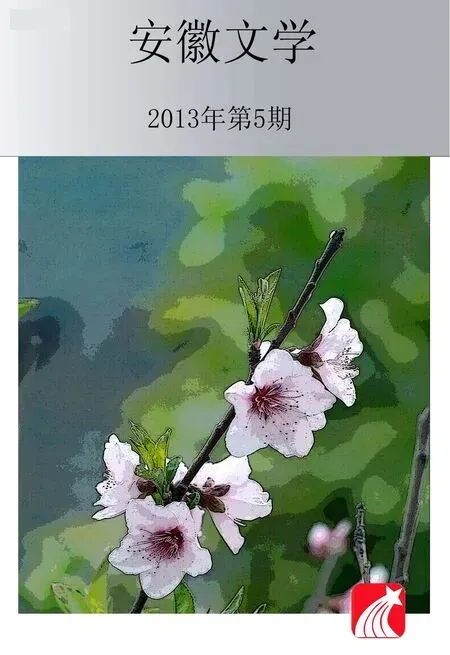开创中国文学的新时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当代意义
2013-12-12
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来说,通常文学与社会制度是相矛盾的,文学基本上以批判社会制度为自己的使命,但是新中国文学走过了六十余年的风雨历程,尽管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却一直与社会主义制度相一致、相符合。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它的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从弱小到强大、从萌芽到壮大、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学一直伴随在其左右,支持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每一次自我完善。新文学发展的这一特征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 《讲话》)有着密切关系,在《讲话》的指引下,中国文学迎来了它的新时代。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延安面临巨大经济困难,同时革命队伍内部也出现许多严重的思想向题,为克服困难,统一思想,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延安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在全党进行的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面对这样的局面,毛泽东同志站在民族命运和先进文化发展的高度,审时度势发表了《讲话》,为新民主主义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讲话》指出:“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讲话》明确指出革命文艺要为人民的观点,以及文艺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这一问题可以说是延安时期革命文艺的出发点和归结点,也是整篇《讲话》的核心理念,它体现出延安时期革命文艺的本质特征,显示出鲜明的人民性。
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延安和各地区抗日根据地掀起了一股热潮,文艺工作者纷纷走到田间地头,走进工厂、连队,深入工农兵群众生活和工作的最前线,与他们亲密接触、打成一片,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文艺队伍的思想面貌,有力地推动了文艺的繁荣和发展。文艺工作者的这种转变是从被动转为主动,他们积极投身创作,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如小说中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诗歌中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歌剧中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的 《白毛女》,等等。这些作品在创作题材上较之以前的作品有了很大的突破,工农兵群众成为作品真正的主人公,作家着力表现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旧势力作斗争以及对新生活的无限向往,工农兵群众才是新时代的英雄人物典范。随着作品内容的变化,艺术形式也产生相应的变化。在语言的运用上,文艺工作者更注重具有民族特色和大众化的语言,清新质朴、轻松幽默的语言使得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在结构、手法上,文艺工作者往往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一改原来文艺的陈旧表现方法,使得作品生动新颖、别具一格。这些作品对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文艺创作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可以说它们是新文学的前奏。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初步确立。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顺利确立,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党确立了毛泽东《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还进一步指出:“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正确性。”这个方向就是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一时间,毛泽东《讲话》成为新时期的文学规范,作家们纷纷高歌革命战争,表现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变,颂扬社会主义新人物,弘扬共产主义理想。例如,小说中赵树理的《三里湾》、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诗歌中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散文中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戏剧中老舍的《龙须沟》和《茶馆》,等等,这些文学作品都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入现实生活的历史土壤中,并用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去照亮壮美的生活和鲜活的人物,从而给广大读者以精神境界的鼓舞和升华,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起到重要作用,也正是它们引领着新时期文学的“主旋律”。
然而新时期文学刚刚走过十七年的历史,就因“文革”而中断,“文革”结束后,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着应该何去何从的困惑,在这个时代的转折点上,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实施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到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形成党的基本路线到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不断改革中得到了完善和发展。在这场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改革实践中,我们党极其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1979年10月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祝辞》指出:“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2]在《祝辞》精神的指导下《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社论明确肯定“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口号,认为“它概括了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它不仅能更完整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对文艺的历史要求,而且更符合文艺规律”。[3]遵循“二为方针”以《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的“改革文学”,以《剪辑错了的故事》、《天云山传奇》为代表的“反思文学”,以《棋王》、《爸爸爸》为代表的“寻根文学”相继出现在当时的文坛上;此后,随着思想解放的逐步深入,在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朦胧诗”、“探索性戏剧”、“先锋派小说”、“新写实小说”也在中国文坛上相继亮相。文学用它独有的方式,向人们展示着改革与发展的必要性,文艺工作者用他们的信念又一次实现了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使命。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期,在“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下,社会主义制度又一次面临着挑战。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其实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不断创新的过程,在这种创新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在那个时期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就是江泽民同志2000年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提出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4]“三个代表”思想从经济基础的要求、上层建筑的支撑和人民大众的力量三个方面展示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过程,进而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丰厚的经济基础、强大的上层建筑的支撑、人民大众的力量。文化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中西文化的碰撞将中国的思想界带入了多元化时代,文艺界相继出现了鼓吹文艺创作的本质是“非理性”,是“跟着感觉走”,是弗洛伊德的所谓“白日做梦”,是“性”驱动,是“生命的表现”等主张,正是在这种背离辩证唯物史观、否定文艺的社会意识形态性的主张下,文坛出现了文学疏离政治和现实的倾向的“私人化写作”、“性描写”和“下半身写作”。针对这一现象,江泽民同志在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文艺要讴歌英雄的时代,反映波澜壮阔的现实;深刻地生动地表现人民群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的精神世界。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在自己的作品表演中,贯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崇高精神,鞭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5]江泽民同志的讲话让更多的文艺工作者认识到社会主义文艺要真实地反映时代精神,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社会主义文艺繁荣贡献力量。值得庆幸的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的全面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的确立,“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号召的发布,使文学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位置:《国家干部》、《根本利益》等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和愿望,“打工文学”突现关注底层建设者的生存状态,《绝对权力》、《我本英雄》等“官场文学”更尖锐地揭露社会的腐败,《猎原》、《狼图腾》、《藏獒》则是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学”。
新中国成立的六十余年,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的六十余年,社会主义制度的每一次完善与发展,文学都为其提供坚实的思想支持,这种文学与社会制度的高度一致性,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支持新文学如此发展的一个动力就是毛泽东的 《讲话》,正是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新文学开创了新的纪元,我们也坚信中国新文学必将健康地发展下去。
[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毛泽东选集·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3.
[2]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A]//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78.11—1980.12[C].香港:中国文献出版社,1982:232.
[3]人民日报[N].1980-1-26.
[4]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做到“三个代表”[A]//论“三个代表”[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5.
[5]江泽民.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A]//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99.4—2001.3[C].香港:中国文献出版社,2001: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