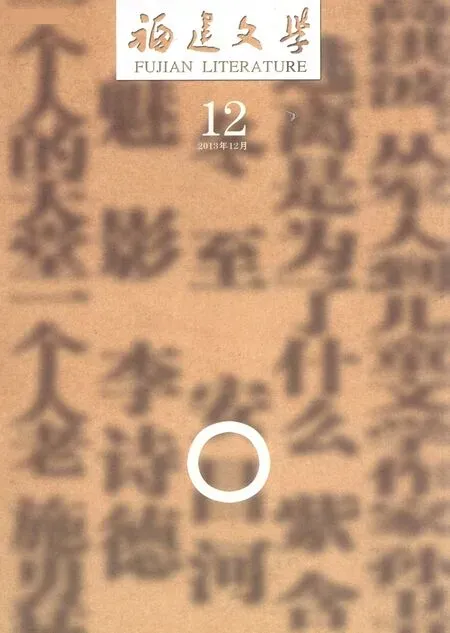诗的外衣(创作谈)
2013-11-16施勇猛
□施勇猛
诗的外衣(创作谈)
□施勇猛
有一只飞虫它飞来飞去,不知道它在找什么。我盯着这只飞虫,我不知道它叫什么,知道了也没有意义。在一只飞虫的世界里,飞着生,飞着死,这就是它的全部。
诗也一样,我根本不想知道什么叫做诗,假如诗也能飞,也必定飞着生飞着死。飞是自由,一种活着的状态,也是死的状态,或者根本没有状态。很久以前,听朋友谈诗歌,总觉得与诗歌无关,无非是喜欢和朋友在一起。和朋友在一起,人总是开心的,会忘记很多东西,至少会忘记一些愁绪,会忘记孤独。
所谓诗歌对于我,就是这样,我所经历过的,所能想到的,把它写出来,这样,人生的忧郁和孤独,就会忘记,我就会开心,就让所谓的诗歌帮我记着,或者忘了,就由它吧。
在这个朋友、爱情都需要验证的年代,我们还有多少东西可以信任永久,可以忠贞不渝,可以无畏付出?活在这世上,生命是一种过渡,一次灿烂绚丽的绽放,又何必用什么来证明我们的存在。诗也如此,它无法证明什么。诗火热冰冷,孤独无情,诗是一种轨迹,心灵轨迹,一种证明心灵曾经存在的方法,仅此而已。
正如我看见的一只飞虫,飞得缓慢的时候,我们都有杀了它的想法。一个微不足道的生命,在人间往往被漠视。正如我们,在时间,在距离,在人心里,也许也飞得缓慢,飞得那样细微,,细到无声,细到看不见自己在飞。我们就是这样,以为走在人间,其实已飞出人心。所谓的诗歌,是我们心灵世界的错误,是变异,是一切美好一切丑恶,一切我们想忘却忘不了的事。诗本身没有对错,错的是我们。我们相信永远,相信美好,相信堆砌在我们身边的真实,但就是忘了谁会相信我们,我们还能相信谁。
在我所能理解的世界里,是一个被简化了的世界,只剩人、事、物。一个精确计算的世界,有着异乎寻常的优雅和从容,爱、恨、忠诚、背叛,都有着精确的刻度。我所理解的世界,每一天都试图感动我,或者试图说服我。我的世界充斥着高尚和卑微,怜悯和绝情,充斥着倒流的影像和幻觉。其实,这一切都是妄想,就是这样,在我的世界里,一切都是旧了的踪迹,有爱的痕迹,有无望的抚慰。
现在,我看见的那只小小的飞虫,仿佛也不存在。我和这只飞虫彼此互不干扰,彼此忘了存在。多好。正如所谓的诗歌,对于我,也不过如此,或者这个世界对于我,也如此。生命中的安慰,可能有,但不会时时有。拿什么来忘记生命中面对的所有奢华和盛宴,像一只飞虫那样随心所欲。
谁把水揉碎了,让一夜的城破了。这漫天的春雨,在灯的微光中,露出了短暂的面容。冰冷不是它的本意,短暂不是它的祝福。时间的永恒,让我们飘荡如雨。聚了,散了,像松开的命运,如此简单,却永远猜不透。像一场戏的最后,有时候会下起小雨,那些无处可飞的飞虫终于不见了,如同我所见到幻觉,一切转眼成空。不管是一天一年或者一世,我们所谓的时间,和我们的名字一样冰冷。在我眼里,所谓的诗歌,记不住所要想念的一切。
今天,我用我的方式爱这个世界。有人说在黑暗里,影子会离开我们,有人说在亮光里,光线会将影子赶出我们的身体,影子仍然想要离开我们。我们亲爱的生活给我们的教训是,你无论如何都无法将自己冰冷的影子变得温暖,你无论如何都无法守住自己的影子。所谓诗歌,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借到的一个玩具,或者是一个自言自语的片段,可以让我去看看心灵里还会有什么。
责任编辑 郭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