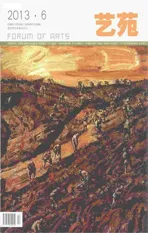《毒战》:杜琪峰“黑色映像”的内地化改造
2013-11-16文‖尹兴
文‖尹 兴
2013年4月26日,杜琪峰、韦家辉携《毒战》进军内地市场。作为一部全新包装的合拍片,对于杜琪峰的这次破冰之旅,知名影评人,港片研究专家魏君子的评价是:“毒战不是港影北漂,而是杜琪峰北伐!”从表面上看,对于以大中原为核心的北方文明,《毒战》的姗姗来迟不过是又一次迟到的认同与皈依。而事实上,当港片“北伐”成为应时而动的潜流时,秉承自身独立黑色风格的电影作者杜琪峰处境颇为窘迫。“北伐”意味着身份殆尽,合拍表明主权丧失,于个性色彩浓烈的杜氏“黑色映像”而言,实在是永远无法调和的裂隙。
坚守作者风格抑或迎合内地市场、咬合集体秩序抑或一骑绝尘,面对充满诱惑和未知的北上之旅,杜琪峰的黑色映像该如何做出内地化改造?几番突围,又几番以静制动,兼容现代意识和历史质感的新作《毒战》,演绎的是杜琪峰最不熟悉的大陆题材,即内地公安与香港毒枭的斗智斗勇。在浓烈雪茄烟雾的掩映下,杜琪峰将如何突破大陆警匪片的外衣,抒发自己一以贯之的悲情宿命?
一、逆袭:清冷凛冽的“英雄梦”
杜琪峰曾经说过:潮流往哪里走,我们就往反方向走。无论在香港还是内地影迷的心中,银河映像都是华语影坛一块拥有特殊记忆情节的金字招牌。节奏感较弱的长镜头、舞台造型的静态效果、“精中蕴动”的人物内心冲突、主人公寂寞尴尬的生存状态、底层小人物宿命般的悲剧命运以及缜密巧妙的叙事结构,无一不是在颠覆传统类型,诉说一曲曲清冷凛冽的“反英雄”挽歌。这位类型电影的“另类作者”在电影形态上左冲右突,自1995年《无味神探》始,杜氏黑帮警匪片俨然成为香港电影重要的地理标识。作为银河映像的幕后推手,从银河初期的幕后策划到中期的锋芒初显,话事人杜琪峰始终明白自己所需。如今高调宣布以《毒战》进军内地市场,杜琪峰舍弃了《枪火》中低调却不失华丽的舞台化造型,置港片“双雄对决”的兄弟情仇于不顾,一意寻求与内地市场的契合点。他说:“作警匪片的好处是它有动作和突出人性,这些点在内地比较少见。时装的警匪片在内地本来寥寥可数,银河映像又在这方面有一些经验,所欠缺的是如何在题材上与内地融合。合拍片《毒战》是我自己的一次尝试,也希望它是对内地电影制作的一次推动。”
事实上,杜琪峰之所以迟迟没有进军内地市场,除了对艺术品格的坚守之外,反倒看出他对于商业电影的洞察与操守:不了解内地市场,无法看清审查的边界。诸多顾忌让他迟迟不愿意拿自己的“黑色映像”试水内地,这样的顾忌只需从杜氏电影当年“被动或主动式内地化改造”的险阻之途便不难理解。究其原因,除了严苛的审查制度之外,英国殖民文化与岭南文化杂糅相间的香港文化,与内地中国传统文化不乏离析和裂隙,亦为重要原因之一。其实,对内地当代文化现状的误读、“97回归”前后的失落彷徨、世纪末的宿命情绪,恰又是杜氏电影极力渲染的重要元素。不同的文化基础、迥异的审查制度,让“一路向北”的众多香港导演纷纷落马,既无缘契合内地观众,更无法通过审查。杜琪峰之前的电影之所以难逃被阉割的命运,亦当如此。最为典型一例,即是《黑社会之龙城岁月》中,被删减的乐哥挥动石头砸死大D哥的镜头,在港版原作《黑社会》中足足砸了近三分钟。杜氏电影中的“善恶平等论”、贪腐奸佞的警察形象、“盗亦有道”的匪帮图谱,无疑与“是是非非、善善恶恶皆有报”的内地精神背道而驰。
在几次不成功的界外球尝试之后,《毒战》再次选择了杜琪峰最青睐的警匪题材。作为首部由香港导演拍摄的内地警匪片,故事一开始便彻底推翻以往电影“善恶不明”的基调,古天乐饰演的毒枭蔡添明在影片刚开始五分钟即被捕伏法。之后,随着津海禁毒大队长张雷(孙红雷饰)缉毒工作的展开,影片用了接近四分之三的笔墨来渲染蔡添明的狡诈凶狠,以及张雷同蔡添明及七大毒商的斗智斗勇。这样正邪两分、符号鲜明的角色形象,倒是有几分吴宇森作品爱憎了然、忠奸分明的影子。《毒战》缺失了《暗战》中迷失的警匪双雄,抹去了《机动部队》里正邪双亡的惨云,唯独不缺的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宿命基调。杜琪峰选择与以警匪片、涉案剧见长的海润影视合作,后者对内地市场、技术运用、审查界限的了然于胸,无疑成为银河映像进军内地的有力臂膀。正因为如此,尽管《毒战》结尾小学校门口惨烈的大屠杀式决战、在国内银幕上首次展示死刑全过程,无一不是开警匪合拍片先河,但由于有了泾渭彰显的道德分界线和鲜明的警匪两派人物设计,顺利通过审查也自在情理之中。
二、改造:写实为骨的“中国面孔”
从立场上看,善恶分明的道德界限似乎与杜氏风格截然不同。以剧情观之,杜琪峰也全然从黑吃黑的窠臼以及“大圈仔”与警方连环枪战的模式中解脱出来。而《毒战》对于社会问题及各色人物的写实处理,同往昔杜琪峰电影架空的故事情境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相较《黑社会》之内地公安在关键时刻的杀将过来,《毒战》对于大陆警力无疑着墨更甚,从叙事主体上看,此前已过世的香港动作明星罗烈也曾自导自演过一部名为《边陲威龙》的警匪片,也涉及到了扫毒,但由一干香江面孔演我金色盾牌下的铮铮男儿,总有些不伦不类。而《毒战》中孙红雷、黄奕、李光洁的加盟,至少在外观上更为落地更具烟火气”。李光洁千里国道越野追凶、孙红雷以身试毒、黄奕意外被撞,无一不尽显内地公安的浩然正气。以上种种正面人物图谱,“白”质感明晰了然:缉毒民警从广东一路开车追到天津,交不起过路费;当毒贩用百元大钞作冥钱祭奠大嫂之时,监视他们的内地警察从口袋里掏半天却只有几十块钱。观众置身于尘土飞扬的县城公路、流连于嘈杂暧昧的夜总会,恍恍惚如欣赏一部杜琪峰版的《任逍遥》与《三峡好人》。看惯了香港高楼大厦的杜氏影迷们难以相信,这样的写实手笔果然出自银河映像?另外的疑问则不言自明:如此‘高大全’的警察形象,和以往杜氏作品中亦正亦邪的香港警察相比,仅仅是为了通过审查的考虑?
惟其如此,《毒战》对于杜琪峰而言无疑是一次有趣的尝试。为了重现内地特有的文化、服装与场景,突出中国公安电影的风格面貌,编剧韦家辉前期与政府机构安排的警察做了大量交流。在充分熟谙内地警察办案流程的基础上,韦家辉将大陆公安办案方法的众多类似细节融入剧本当中。而这样做的结果不难理解,和标志性的黑色银河映像相比,《毒战》中的人物图谱出现大量非常规的因素。首先暴露在《毒战》里的不同,是杜琪峰对人物的改造与打磨。在经典杜氏黑色影像中,杜琪峰喜欢塑造一个个颠覆类型的“悲情另类”,于风云突变的黑色江湖坚守全然不可能的信念。“这个人可以是林雪,地下社团风起云涌,他生死关头却仍然虔诚地念着‘私劫兄弟财物,暗帮外人抢夺兄弟财物者,五雷诛灭……’(《黑社会》);他又可以是那个跟同一个人玩同一个游戏,猜了327次硬币,答案从来不变也从来没有赢过的警察;他甚至可以说是每次去餐厅吃饭,永远对点餐员说同一句:‘红烧翅,蒸一条鱼,半只炸子鸡,再来一碗白饭’的性格分身(《神探》)……他更可以是刘青云,当城市上空漂浮着经济泡沫,各家自扫门前雪,他却坚持为兄弟一次次付出财力(《夺命金》)。”然而,《毒战》要对人物图谱进行内地化改造,首条规则便是:黑即黑,白是白。《毒战》中的内地公安没有一个人贪污渎职;与之相对的黑帮则都是“盗亦无盗”,为了生存和利益彼此出卖的悍匪。
杜琪峰说过:“香港警察的形象是很好的,无论我怎么拍,市民都相信警察,都不会影响到真正的警察地位。香港警察不在意电影把他们拍成什么样子,你说他忠也行,奸也行,杀人也行,强奸也行,贪污也行,他们明白这是看电影。”但是内地的公安部门却重重顾虑,他们担心电影编剧虚构出来的极个别“坏警察”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正因为如此,内地犯罪片警察形象不够立体生动,每一个警察都循规蹈矩,人性弱点无法植入其中,让戏路显得平直单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编剧韦家辉找到的对策是:“整个电影的节奏一定要很强,情节衔接到最紧,观众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其他的了。《毒战》因此就像一个‘缉毒版’的《24小时》,从张雷发现毒贩蔡添明(古天乐饰)的制毒工场,直到最后缉毒队与‘毒帮’同归于尽,片中所有人就是一口气跑到生命的尽头。”“写实为骨”的叙事基调也让两大主演孙红雷与古天乐都找到了施展的空间。在固定空间内大打时间差的孙红雷,忽而是“老乡老乡,背后一枪”的笑面虎风范(哈哈哥),忽而是神经质的瘾君子。一场“你干杯、我随意”的吸毒场面,被孙红雷演得丝丝入扣、大开大合。反观《毒战》的灵魂人物古天乐,跟随在车祸之后的种种随机事件就像乱抛的蛛网,将其愈发紧密的困在当中。这位惶惶不可终日、游走于野兽丛林的亡命徒,视人情人命如草芥,当被曾经的“自己人”追杀时,也出卖着警方或另一批自己人。一暗一明、一主一从,古天乐和孙红雷的精彩互博,在沿袭杜氏电影冷峻风格之余,依稀开启了“黑色映像”内地化改造的有力尝试。
三、宿命:一以贯之的黑色视点
《门徒》(2007年)和《枪王之王》(2010年)的票房过亿让尔冬升有底气说:“为了保持影片纯粹地道的香港味道和创作的自由度,《新宿事件》自愿放弃内地市场。”而杜琪峰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单纯依赖香港市场,他的票房可谓惨淡之至。2008年追忆旧日香港情怀的《文雀》收入仅559万港币,同期朱延平的《大灌篮》则未上映就已经收回7000万成本。银河映像的票房清单冷清如故:《PTU2 机动部队》390万港币,表现稍好的《意外》也不过区区523万港币。几乎所有香港导演都北上赚钱的时候,杜琪峰却始终置身局外。忍受资金和内地检查制度的双重挤压,却又能秉承一以贯之的黑色宿命视点,这不能不说是《毒战》“北伐”于杜琪峰的特殊意义。
《寒战》的警界办公室政治、《逆战》的去香港化,在改造香港警匪电影之余,因为迁就迎合内地市场而终成类型破局。与之相对,杜氏黑色电影系列之所以带有显著的作者电影印记,在于其常常能异峰突起而不失先声夺人,用个性化的电影手法承扬经典黑色电影美学。在杜琪峰的眼中,人物身份乃至故事情节本身都不是重点所在,他仅仅需要探讨某种人群的悲欢离合与生存危机。悲情宿命、静中寓动的独特风格在其人物塑造和影像编排中一以贯之。
作为合拍片的《毒战》亦不例外,尽管正邪分明的道德界限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宿命的意味,但是人与环境、人与命运的随机连锁关系依然冷静残酷。当观众进入这个叠加于虚构和现实之间、亦真亦幻的世界时,真正让其痴迷的,应当是宿命附着在俗事之后产生的近乎荒诞的黑色情绪。荒诞的黑色幽默搅乱了事件的种种“迷局”,彰显出人物命运的无常和个体的渺小。以《毒战》一片观之,众毒贩真钱无处消费,只能作冥币祭奠大嫂;大聋小聋突然发飙,从密室潜逃;蔡添明亡命天涯,最后却难逃被曾经的“自己人”追杀的命运……凡此种种荒诞事件,直至蔡添明被执行安乐死,终达高潮。人物打破常规的选择中,无时无刻透露出的却是滑稽和无奈。当古天乐的脉搏声渐渐归于平静,去除一切可能修饰的灯光和音乐,真实环境中的喘息声成为最具震撼力的元素。《毒战》从随机发现制毒工厂的荒诞开始,也最终以荒诞收场,不能不说是善恶有报的宿命使然。
一如《黑社会》片尾曲所唱:“现在春花开遍,日后秋风不免……有灭有生,世事有续有延,没有当天没有今天。笑问何时何地,再遇从前人面,你是否会知当年?”杜氏电影向来以冷峻著称,却从未像《毒战》这般面无血色,于悲悯感伤中体现人性深层思索。过着刀口上舔血日子的蔡添明实为影片灵魂人物,其自私冷酷近乎极致,但却又难以让观众涌出恨意。大家仿佛不过在看《地理》频道中猎豹捕杀羚羊的精彩片段,严酷的丛林法则和强烈的生存意志让一切奔跑与撕咬显出几分诡异的理所当然。以此观之,显然不能用简单的“善善恶恶皆有报”的道德分界线来标示《毒战》,影片在小心翼翼触碰内地电影检查制度之时,也揭开了中国内地社会冰山一角。这与《暗战》、《黑社会》、《一个字头的诞生》等片形成了隐约可见的互文关系。在谈到影片结尾安乐死一幕,杜琪峰说:“其实我们当初也有点害怕它会被剪了,但还好让我们过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无论对内地还是香港观众都比较新鲜,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它就像是现在的普通电影了。恰巧就是这一点这一滴,让它变得不一样。让我自己说,它并不仅仅是一场死刑这么简单,是一个电影的开放……这是社会的另一面,对电影来说也是一个进步,这一笔如果剪去了,我们可能还要再花时间去发展,这部电影让人看到香港电影或者内地电影是有另一个机会的,这个是我觉得好的事情。”这段话道出了《毒战》作为杜琪峰“黑色映像”内地化改造的全部秘密,也依稀指出了华语警匪片题材的又一发展契机。
[1]许嘉.毒战:一战到底![J].大众电影,2013(8).
[2]杜琪峰独家解说《毒战》[J].看电影,2013(3).
[3]毒战:杜琪峰的破冰之旅[J].环球银幕,2013(4).
[4]嗨了,毒战[J].看电影,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