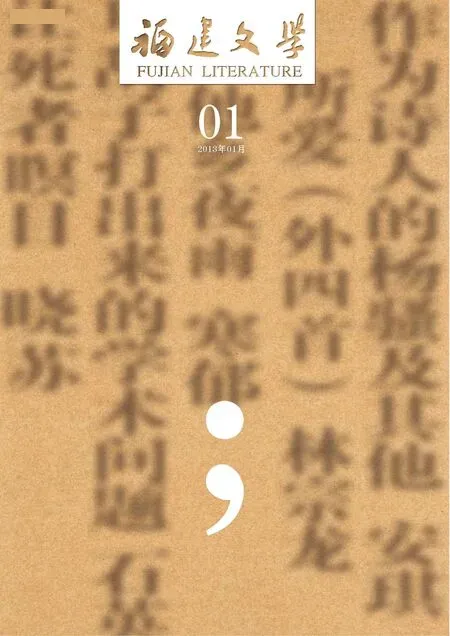垂危的美(创作谈)
2013-11-15林宗龙
□林宗龙
垂危的美(创作谈)
□林宗龙
“身体跑得太快,灵魂都跟不上。”在一种过于媚俗的失衡之中,形成了当下的普遍焦虑,在秩序的天平两端,对物质的过度膜拜,必然导致精神的严重缺失,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最初的善和真,忘记了一种朴素的笨拙的原始面貌。
在一条看似宽阔但充满陷阱的路上,类似于无脚鸟的命运悲剧,似乎随时都可能降临在这个焦灼的土地上,看不见的无法触及,让土地上每一个焦灼的事物,都可能成为一种仪式之外的虚空,像永远见不着光的黑洞,需要更大的虚空来填满。
从这个意义来说,诗的力量其实就在于,它用虚空填满虚空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它是哥特式拒绝的冷酷,是达达式否定的消解,是摇滚,是抒情……是一切形而上的返乡图腾,在日常之中显露出超现实的荒谬,在超现实之中又隐藏着日常的琐碎。在正负两级的对流之中,诗所传递的是诗人内在精神与现实世界的对抗。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对抗越强烈,它就越能接近存在的本质。
在后现代“人被异化为物”的文明大跃进中,诗的这种对抗自然是无效的。但它的价值也正在于这种无用之用的个人化命名,类似于殉道者一般的宗教信仰,在茫茫的迷雾丛林之间,向着自然之境,怒放人性最纯真的花蕊,正如海德格尔对“诗意的栖居”所阐述那样,“只有当诗歌发生和出场,栖居才有可能发生”。
在看我来,诗歌的出场就是经验在时间的向度上对存在的深刻记忆。它不是浮于浅表的修辞,而是隐藏在身后诗人抗拒一切又接纳一切所呈现出的特质,就像一个神秘的庄园,只有无限接近自我,才可能看见时间毫无保留地在周遭发出神性之光。
因而,我无比迷恋时间,这个有着伟大批判力的雕塑家,让我时常地游离在片刻的模糊和清晰之间,那是每一次深入骨髓的经验和感受。而大多时候它们是可靠的,像影子一般,抓不着却切肤地存在着。但我更愿意去寻找那些不可靠的少数时候,这是未知的,隐秘的,对真实与自由的崇敬,抑或像巫术一般与逝去的另一个世界做对话。
我始终相信:那是通往自然之境前的仪式。这仪式是对童真的唤醒,对存在的观照,对虚无的敬畏。《致流年》可以看作我对唤醒童真的实践。那些古老的生动都发生在遥远的孩童时期。可以说,孩童时期是生命体最接近自然最接近真我的时期。那些成人世界很少有的无拘无束,那些像树叶一样很单纯的功利性,那些没有太多教条和束缚的存在感,都会让你无限地去怀念。但让人感到恐惧的是,孩童时期是向成人世界演化之中并不可或缺的阶段。这就意味着游戏规则的合理化,复杂化,物质化。这时候,人性的欲望性就会越加凸显出来,也就意味着更多的美好和纯真的丧失。这种反差,无疑是会让人感到难以适从,甚至出现心灵的异化或扭曲。而诗歌是最为柔软的能够唤醒真我的美妙雨声,那个深藏在存在之中暂且被掩埋的自我。
而存在往往带着其戏谑的,荒诞的,滑稽的面具出现。它有着用不完的力比多,联系着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时代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这种连接,或直接,或间接,或紧凑,或疏离,因而产生无止境的因果回转。《一年》《刚刚开始》正是在这种情境下,催生出的对自我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和危机感。《一年》是迷惘一代无根性的真实写照,有着英雄主义的落寞和孤独,有着精神家园缺失产生的茫然和无力,它像一列无始无终的火车,带着我流离失所,寻找故乡和根,如果还有的话,那就是尽头。而《刚刚开始》同样是对存在的荒诞感以及时间伟大批判力的暴力美学中催生的,探讨的是人的本性和神性之间的博弈,是人类现代性的寓言,以及身份认同过程的恍惚感。前者是戏谑之轻,侧重的是时间意识的体认,后者是沉思之重,糅杂着童话意味的混沌感。但两者,无疑都是自我的一次次艰涩荆棘的精神历险。
在诗歌的丛林之中,我无时无刻不在享受着冒险带来的认同感。可以说,每一次冒险都是一次自我的救赎,这便是诗歌于我的意义所在。它绝不是一次性的消费,或者快餐式的一夜狂欢,而是生命运动过程中自我的认同,一部浸染着爱与虚无的心灵史,像“黑玫瑰垂危的美,慢慢钻进自己的刺中”。
责任编辑 郭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