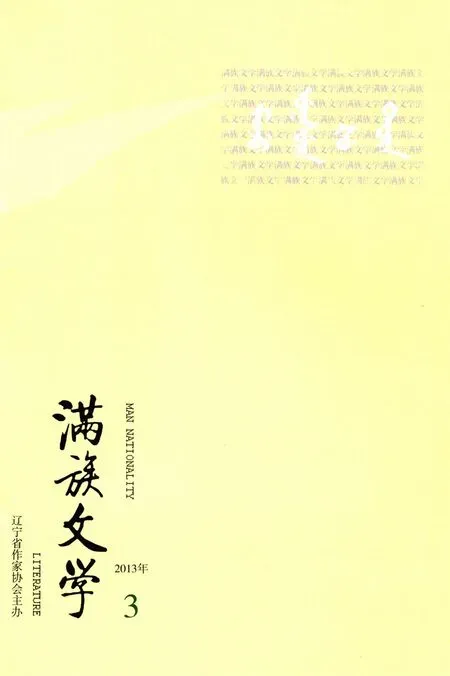梦一场
2013-11-15冯忠臣
冯忠臣
雨,丝丝屡屡如一袭薄纱,细细软软、绵绵密密地下着。阴冷、潮湿,天空灰暗,似乎惆怅布满了每一寸空间,抓一把空气好像都能攥出水来。几只不知名的鸟从天际飞过,叫声幽远、凄凉。
吉胜站在窗前,内心一阵一阵的蛰疼。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疼越来越强烈,像一只不断长大的怪物,用坚硬的鳞角触碰脆弱的内脏和敏感的神经,有时让他觉得好像要窒息了。对谁说呢?无厘头、莫名其妙的身世,如何能说得清。纵然有人倾听,又从何说起,怎么张开这张嘴。每当陷入痛苦的深渊,吉胜只能躲到没人的地方,自我折磨。多少个暗夜他从精神深处分裂出另一个自己,不断咒骂、责怪自己,以此宣泄心中积郁已久的悲凉,为自己舐伤。
伤在二十年前。
那年吉胜五岁。
吉胜的父亲赵木匠常常走村串户给人家打家具、建房屋,因为手艺妙为人厚道,受到了人们的尊敬。母亲菜花心灵手巧,人长得甜,会打理家务处邻居,人们都愿意和她来往。夫妻俩恩恩爱爱,无忧无虑,生活过得殷实、惬意。村人们经常说,这真是天造的一对地设的一双,羡慕不已。小吉胜也生活在蜜糖罐中,享受着别个孩子没有的充满阳光雨露的快乐童年。父亲经常出去干活,有时会给吉胜买回些稀奇古怪的玩具,让吉胜在小朋友面前很是扬眉吐气,小朋友都围着他转,小吉胜感觉很是受用。赵木匠外出短则三五日,长则个把月,偶尔三俩月也有过,回来就会格外地疼爱吉胜。时间长了小吉胜想爸爸,看到赵木匠又有些陌生,低头不敢直接看,用眼睛一下一下地瞟。
那个平淡无奇的午后一直根植在吉胜的脑海中,像一根刺,伴随着他的成长,让他鲜血淋漓地疼。
出去两个多月的赵木匠回家,对吉胜亲昵有加。小吉胜缩着肩,勾着头,有些惧怕赵木匠。看到孩子缩手缩脚,作为父亲,赵木匠舐犊之情涌上心头,心里愈发荡漾着幸福的涟漪,蹲下身,轻抚着小吉胜的头,慈祥地说,想爸爸没有?小吉胜脸别在一边,嗫嚅着细声细气地说,想了。赵木匠说,哪儿想了?小吉胜用小手指指脑袋又指指胸口说,这儿想了。赵木匠一时激动得不知干点什么好,看到紧张的小吉胜,一把搂过来夹到腋下,说,爸爸领你去小卖部买买好不好?小吉胜的情绪放松了不少,兴奋地拍着小手说,好好。
赵木匠放下小吉胜,弯下腰说,亲爸爸一口。小吉胜忸怩地张开了甜甜的小嘴在赵木匠的脸上“吧嗒”一下。赵木匠幸福地眩晕了,一下把小吉胜抛了起来,稳稳的放到脖子上,驮着向小商店走去。
坐在爸爸的脖颈上,小吉胜嘻嘻呵呵咧着嘴笑,心中有暖洋洋的溪流淌过。小吉胜小小的脑瓜陡然呈现一个画面,似乎有几次的睡梦中他迷朦地看到父亲似乎骑在母亲的身上。吉胜想,为何每一次爸爸一回家,天一落黑,准保让自己赶快睡觉?小吉胜赖赖叽叽不睡,赵木匠有时一改白天的好耐性,好像变了个人,吼着吉胜快点睡,小吉胜真是不明白,白天的爸爸和晚上的爸爸怎么不一样呢?现在似乎明白了,爸爸逼自己快些睡,是为了和妈妈重叠在一起。两个大人辛苦地叠加在一起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做游戏?爸爸、妈妈为何要回避自己?俩人之间的游戏很有趣吗?好奇心是小孩子特有的天性,当然小吉胜也不例外。小吉胜开始专注起他脑海中的问题,问,爸爸,男人为什么要趴在女人身上。赵木匠说,小孩子,净瞎说。
小吉胜小脑瓜里闪烁着赵木匠趴在妈妈菜花身上的画面,这画面像一条馋虫定居在懵懂未开的吉胜心田,勾起他探索的欲望,比上小卖部买好吃的想法还强烈。小吉胜执拗地想知道答案,寻根刨底地问赵木匠。赵木匠被幸福笼罩着,哪还把小吉胜的话放在心上,胡乱应付着说,小孩家家的,哪来那么多奇怪的想法,长大你就明白了。
赵木匠的答非所问,更激起了小吉胜无限的遐想,他太想知道其中的奥妙,以便和小朋友玩耍时也有炫耀的资本。小吉胜脑中闪现出隔壁双眼皮妹妹麦粒,不知为啥这几天她一直不搭理自己,不和自己玩耍,如果能探得大人的秘密,和她一起做这个有趣的游戏,大眼睛妹妹麦粒一定会喜欢他这个大哥哥。爸爸不告诉他,小吉胜想啊想啊,小脑瓜都想疼了,也搞不明白。大人们太奇怪了,为什么要做些令人费解的事情?看到爸爸心情好,可是逮到机会了,小吉胜哪能善甘罢休,紧追不放的问赵木匠。
赵木匠清楚儿子的秉性,凡事不弄个水落石出,肯定要没完没了叨磨下去。为了转移儿子的注意力,说,爸爸没在家,淘气没有,妈妈打没打你小屁屁。
说到妈妈打没打自己的小屁屁,小吉胜陡然想起爸爸不在家时,二栓叔经常到家里来,帮妈妈干这干那,围着妈妈转。一次小吉胜从外面疯跑回来,看到妈妈和二栓叔面对面站在一起,往二栓叔的眼睛里吹气,过一会儿妈妈还问,好点没。二栓叔说,沙子没出来,眼睛还疼。妈妈接着吹,小吉胜突然在后面叫了一声,妈妈和二栓叔倏然分开了,妈妈说,小鬼,吓死人了。
想到这一节,小吉胜随意地说,我看到二栓叔叔趴在妈妈身上。
赵木匠把吉胜放到地上,问,真的?
此时小吉胜根本没发现爸爸的脸色变得铁青。吉胜后来一直陷在自己幼年编织的黑洞里,暗恨自己为何不改口呢?如果改口世界会变成另外的样子。
小吉胜有些紧张,他本想说趴在妈妈身上的是父亲,转念又不想说了。当时不知怎的,吉胜认为男女之间所干的事肯定很机密,他不说是爸爸趴在妈妈身上,也许爸爸才会告诉他男女之间的原委,让他好奇的心得到满足。吉胜看着脚尖细声说,真的,我亲眼看到二栓叔趴在妈妈的身上。尔后补充了一句,骗人是小狗。
生活中,小孩子因为单纯幼稚,说出的话有时比大人真实可信,甚至铁证如山。赵木匠的脸色由铁青而死灰继而菜绿,他有五雷轰顶的感觉,心肺都被掏空了。他狠狠扯起小吉胜的手说,你上爷爷奶奶家。
看着父亲如此阴森恐怖,吉胜小心翼翼地说,不是去买买吗?
赵木匠狮吼般地说,买你娘的狗腿。
看到父亲变得比魔鬼还凶狂,想哭又不敢哭,趔趔趄趄、一步一跟头地被父亲送到了爷爷奶奶家。
之后,赵木匠急切地返回自己的家,插好了门窗。菜花以为赵木匠要和她云雨一番,娇嫩地说,他爹,大白天的,让人看到多不好?
赵木匠直勾勾盯视菜花说,大白天和我干不好,和别人干好是吧?
菜花这才发现丈夫的不对头,和声细雨说,听谁嚼舌头了?
赵木匠说,没事怕人嚼什么舌头,你说和二栓是怎么回事?
菜花急赤白脸地说,你好日子过够了,把屎盆往自己头上扣。
赵木匠说,急了不是,没这事你急个逑。这种事我不给你点教训是不能承认的。说罢赵木匠拖过菜花没头没脸地狂打。
打一气赵木匠问,有这事没。菜花不承认,赵木匠继续打。
菜花几次昏厥,赵木匠学电影里用凉水给菜花泼醒,接着打。赵木匠铁定的认为菜花一定有事,不然儿子怎么能说出那种话,小孩子不懂男女之事,让孩子编造都不可能。赵木匠觉得,不把二栓和菜花的猫腻弄个水落石出,枉为男人。想到此,赵木匠更加疯狂。
菜花的骨头太硬了,赵木匠打得累了打不动了,菜花仍然死不认账。赵木匠想,俩人这样硬撑下去不是个事,打死了菜花便宜了二栓那个王八羔子。他恶狠狠威胁菜花说,你死不认账,我会把你和儿子都杀掉的。提到儿子,菜花心里一紧一紧的害怕,一阵一阵头发根发奓,想不出办法解决今天的事。看菜花木讷的没有反应,于是赵木匠说,你去把二栓找来,当场对质。
没有更好的出路了,菜花想。
二栓和赵木匠是远房的亲戚,平常多有来往,赵木匠不在家,二栓常来帮着干些粗笨的活。菜花找到二栓谎称到家里帮着干点活时,他一点没打艮,爽快地跟着来了。路上看菜花脸上有伤还关切地问,怎么弄的。菜花掩饰说,搬酸菜缸石头不小心摔的。二栓说,我哥不在家有重活怎没找我,自己硬撑着?亲戚三分向嘛。还开玩笑说,我哥没在家,有些事我也可以解决嘛?俩人太熟悉了,开玩笑是经常的事,二栓根本没看出来菜花今天的异样。
无知无觉的二栓傻呵呵跟菜花刚进屋,房门在背后被拴上了。二栓一回头,看到赵木匠古怪狰狞的脸,结结巴巴地说,你在家啊,我嫂子让我帮他干点活。
赵木匠怪笑着,说,我没在家没少帮你嫂子干活吧。说着一个通天炮打在二栓的面门上,血像一挂瀑布,刷地染红了二栓的脸。没容二栓辩解,赵木匠操起斧头向二栓劈来。二栓东躲西窜,高喊,哥,为什么事你说。赵木匠气喘吁吁地说,还装混,你和菜花的事,她都承认了,你还装混。二栓跳上了炕说,冤枉,你问我嫂子。赵木匠说,问你娘个B,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有种做没种承认,孬货。接着一斧紧似一斧劈向二栓。
锅碎了。水缸破了。橱柜倒了。二栓一下躲避不及,手臂被划出了一道很深的伤口。菜花看着要出人命,跪下抱住丈夫的双腿说,他爹你到底想干啥?赵木匠一脚把菜花踹出老远,说,你个贱人,现在你还向着这奸夫。菜花又跪行到丈夫的脚下,赵木匠又是一个窝心脚,菜花昏厥了过去。
赵木匠吼声如雷,一蹦三丈高,哪有二栓的回旋余地。本来胆小的二栓吓得面无血色体若筛糠,央求说,哥只要别弄出人命,你说怎样就怎样。
赵木匠说,认了这件事,不然你俩都得死。
二栓为了保命,说,我认。赵木匠说,好,你写一张借我一万元的借据。
二栓稍微艮迟了一下,赵木匠举起了斧头,“刺啦”一声在自己胸口拉出了半尺多长的口子。二栓大气不敢出,乖乖写好了借条,逃命去了。
逃出了生死场,好长时间二栓的魂魄才回到身上。待胆小怕事的二栓稍稍舒展了一口气,回顾刚才惊心动魄的一幕,越想越荒唐透顶,赵木匠这是发得哪股疯,简直不可理喻。
平时赵木匠不在家,二栓隔三差五到赵木匠家,帮菜花干些脏累的活,俩人独处的时候,二栓时常也心猿意马,内心有欲望的小火苗跳动,可是毕竟没有形成事实,想想还犯法吗?如今自己没吃到鱼沾了一身腥,挨了一顿胖揍不说,还欠了巨额饥荒(当时万元户是寥若晨星)。二栓窝囊憋屈得不行,想着想着他心里似乎开了一条缝,这是他妈的赵木匠两口子演的双簧,抓自己大头骗钱不是。想明白了二栓毫不犹豫报了案。
可想而知,赵木匠涉嫌敲诈勒索被收了监,判了刑,出狱后无脸面对乡里乡亲,流落他乡,至今杳无音信。赵木匠被逮捕,这事必然轰动了十里八村,各种传闻层出不穷,波及甚广。菜花经受不了舆论波涛的冲击(大部分传闻都把菜花说成比狐狸还骚的娘们,她有十张嘴也找不到人辩论。就是她去澄清,讲的是真话,谁会相信),投河自尽了。菜花真的很惨,尸首捞上来娘家人、婆家人都远远地躲着,最后被好心人埋在了乱坟岗。吉胜长大后想给妈妈烧刀纸、认个错,都找不到地方。
窗外,夜雨缠缠绵绵,恼人地下着。屋檐落下的水,滴滴答答地敲击着窗棂,好像在浸淫、清洗年久发霉的秘密,这样的天气格外让人沉闷压抑。
吉胜站在窗前,望着漆黑一团的外面,胸口好像长出了一团一团的绿毛菌,在向身体的四周迅速扩展。想想人生真是滑稽,自己年幼时口无遮拦的一句话,像一只母球击中了无数只子球,母球改变了方向,子球也四散而去改变了原有的轨迹。生命有多少种假设,也会有多少种结果。可惜个体的生命只能在自身和外力的作用下,走完属于自己的生命过程,没有重来和后悔的机会。茫茫人海中有多少像妈妈的人,被不明不白的灾祸击中,含冤九泉?又有多少像爸爸一样的人,背负子虚乌有的包袱,踽踽苦行挣扎在人世?
雨时大时小,绿毛菌溢出体内,在屋里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