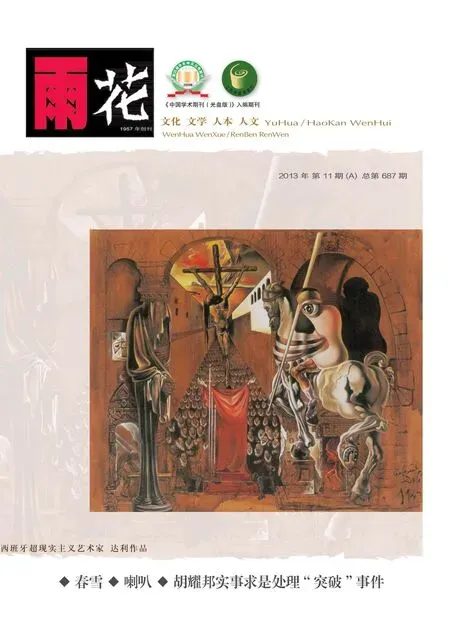老余
2013-11-15沈乔生
●沈乔生
老余
●沈乔生
从此,老余就把装有骨殖的盒子揣进了怀里,走到哪里都带着。他去上班了,不坐车,步行去。走了一段路,他就停下来,拿出锦盒,说:“囡囡呀,你走累了吧,我们歇歇。”
老余一生平淡无奇,在一个公家单位里谋事,最高也就做到副科长,也是看他年龄大了,照顾他的情绪。翻他履历也是没有亮点,中专毕业了分到单位,文化大革命中是逍遥派,以后不咸不淡地上班过日子。
如果因此认为有关老余的一切都平淡无奇,那就大错特错了。老余有一对女儿,小名叫大妹、二妹,见到的人都大惊失色,说,“老余,你真有本事,怎么生得出的!”的确,生一个好女儿都是极难的事,去大马路上看看,一大堆女人,堵了半条路,要长得好,又品行好、性格温婉的女孩能有几个?老余怎么就生出一对来,那要天大的本事啊。二妹11岁,大妹13岁时,就看出是一对美人胚子了。夏天,两个女孩一起出门,都是一样的装饰,脚下穿天蓝色滚边的布鞋,上身是月白色的缀红花的褂子,乌黑长发似波浪一样垂下来,半腰里扎一根鹅黄色的头绳,身材苗条灵秀,像是两株出水芙蓉,短袖里伸出两条白净、细巧的手臂,像是刚起出塘的鲜藕。路人没有一个不驻足看的,走过去了,还要回过头。又过了六年,二妹的五官都长开了,越发的楚楚动人。那时候学国外,时兴起选美了,二妹也大胆,瞒着老余,报了名。
老余知道了,说:要有好几轮比赛,这么抛头露面,合适吗?二妹也不和他辩,握了老余的手臂,不停地摇,像是摇船的摇着手中的橹,说:“爸,我要去嘛。”经她一摇,老余也就不说话了。二妹参加比赛了,他带着大妹、妻子坐在底下看,他的心怦怦跳,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舞台上的二妹,像是看一个陌生人,他发现二妹比他认识的还要聪颖,还要有智慧,还要光彩照人。
结果二妹获得了亚军。电视台来采访了,各路媒体都来了。有本全国著名的生活杂志的记者也闻讯赶来了,他正和老余说着话,大妹下班回来,记者说,你爸爸正在说你呢。老余说,不是她,这是二妹的姐姐,是大妹。记者很吃惊,说:“你有两个女儿?太不可思议了。”记者很激动,要老余谈两个女儿,只要想得起来的,都可以说,从小时候说起。他勉强说了些。二妹也从大学回来了,记者一定要拍张照,老余站在中间,二妹站左边,大妹站右边,她们一人挽老余一个手臂,老余笑得脸上的皱纹全绽开来了,像一朵盛开的菊花。
不久,这张照片就登在杂志的封面上,还引用了汉武帝的一句诗,怀佳人兮不忘。虽然用错了地方,他们是父女嘛,但没有多少人发现。单位里很多人都看到这期杂志了,没看到的也找来看。有人说,老余呀,全国人民都知道你有两个貌美如玉的女儿了。老余咧了嘴,呵呵笑。有人说要请吃饭,有人说要喝酒,闹成一团,最后科长出面,让老余买了一盒巧克力,大家都甜了嘴。
从老余心里来说,他爱二妹,超过大妹。二妹比大妹更仔细,更贴心。她下班回来,看老余歪倒在圈椅上,就走上来,让老余在床上躺好,她伸出一双手,从颈脊捏到腰脊,又从腰脊捏到颈椎,她额上出细汗了,老余浑身上下也通畅了。他说:“阿囡,你太吃力了,不要推了。”二妹才停下手来。
天冷了,二妹买了三斤黑芝麻回家,洗干净了,漉水晒干,拿到朋友家磨细了,回来封在大瓶子里,她在家里宣布:“这是给爸爸吃的,每天吃两调羹,冬天补身体。”妻子说,看看,你这个女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老余也不说话,嘿嘿地笑。
又过几年,二妹上班了,在一个文化单位。大妹谈男朋友了,可是谈得不顺当,隔几天就回家抹眼泪,二妹问:姐姐,你们之间发生什么啦?大妹就把些枝枝叶叶讲给妹妹听。二妹叫起来:“这怎么行!心胸这么狭窄,这样的男人少有。姐姐,你说给爸爸妈妈听。”老余和妻子听见了,都走过来。大妹把刚才的话又讲一遍。老余的妻子说:“怎么会这样呢?真要跟了他,将来怎么过日子。”老余说:“我要看一下人,看他面相怎么样。”妻子说:“怎么看呢?又不能带回家来。”二妹说:“这个简单,姐姐和他见面,我和爸爸走过去,当作不认识,不就见着了。”妻子说:“这个办法好,二妹脑子灵活。”
两天后,大妹和男朋友见面了,二妹挽着老余的胳膊也去了,二妹围一条雪青色的纱巾,老余围一条骆驼毛围巾,半条围了脖子,半条遮了脸。去了一个小时,老余和二妹先回到家,过不一会,大妹也回来了。老余眼里闪出奇异的光亮,说:“我看清楚了,这人眉头结得非常紧,脸上隐隐有一股黑气。再加上大妹讲的那些事,不能谈,不能谈!早了结早好。”
大妹说,男的不同意分手,情愿死,他也不放弃她。老余的妻子说:“怎么碰上这么不讲理的人,倒霉!”二妹说:“不怕他,现在文革结束了,他敢怎么样?”
大妹还是向男的解释,但越是解释他越是猖狂。大妹决意不理他,他打电话不接,他写的信每封都退回去。男的就在路上拦她,下班拦,上班也拦。大妹上下班就像通过封锁线一样紧张,终于有一天给他拦到了,他揪住了大妹的衣领,时而破口大骂,时而苦苦哀求。人们围过来看,一条马路都给堵住了,后来警车来了。老余和妻子到派出所领回了大妹。大妹衣衫撕破了,脸上没有表情。那男的被拘留了15天。可是,他并没有悔改,而用了更阴险的法子。他跟踪她,不远不近的,像个幽灵,还到处写信,捏造事实,散布流言,败坏大妹的名誉。大妹整夜睡不着觉,眼窝下陷,没有了人形。二妹忍不住了,说:“这人太无耻了,他还讲不讲理?”大妹说:“你和他说,他可能听你。”二妹说:“你把他地址告诉我,我这就去。”说着就要出门。背后传来一个沉重的声音:“你回来。”说话的是她的父亲。老余说:“你不能去。老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二妹说:“那就眼睁睁看着姐姐给他折磨死?”老余说得斩钉截铁:“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不能去。”二妹只得退回来。
第二天是休息天。二妹把象棋盘摆开了,说,大妹,我们下盘棋吧。大妹说:不下。二妹又拿过杂志,说,你看书吧,这是新来的杂志。大妹摇头。二妹不做声了,她翻起杂志,眼睛却看着大妹,她失神的脸在慢慢地变暗,二妹回头往窗外看去,外边的天也在变暗,忽然想起来了,今天是日全食。她忙跑到窗前,太阳高悬在天中央,一个巨大的黑影正在向太阳盖去,太阳慢慢变化起来,由一个圆变成大半个圆,再变成半个圆、小半个圆、月牙儿一样的。有人叫起来,天狗吃太阳了!就有当当当的敲打声,似是敲打破脸盆。二妹回头看,大妹还痴坐在那里,脸更暗了,五官都模糊了。刹那间,太阳消失了,天地间一片黑暗,就跟在夜里一样。
二妹回头喊:“大妹!”没有回答。二妹摸着黑过去,摸到了大妹的肩膀,摸到大妹一双手,像鱼一样冰凉,发着抖。二妹把它们握住了。大妹喃喃地说:“你去和他说,他可能听你的。”当当当,当当当,屋外敲打得更响了,不止一个脸盆,许多个脸盆都在敲。这时,天有了一丝亮。二妹拉着大妹,朝窗口跑去。两人朝天看,太阳正在奋力地从黑影中挣脱,先是露出一道弧形的刺目的金光,然后慢慢变宽,变成月牙儿似的,变成小半个圆,二妹心里的想法一点点坚定了。她欢快地叫起来:“天狗把太阳吐出来了!”太阳变成小半个圆、大半个圆了。天地间重新亮了起来。
二妹流泪了,她被神奇的天象感动了。大妹无力地倚在她肩上。
当天,二妹就找到那个男的。男的说,这里不方便,找一个地方说话。二妹心想,去就去,怕他什么。男的把二妹领到一个偏僻地方,把她活活掐死了。他还在她身体上做了龌龊的事,随后上了一幢高楼,从顶楼跳下来,摔得脑浆迸裂。
老余的妻子不知道该怎么对老余说。两天过去了,老余没有见到二妹,着急地问:“二妹到哪里去了?”妻子忍着悲痛说:“她出差去了,她们歌舞团到广州演出去了。”老余说:“到广州去演出了?走前怎么没和我说?”妻子说:“可能走得急,她和谁都没有说,只让同事来家里说了一声。”她快站不住了,倚在墙上,随时可能倒下。老余打开门,怔怔地望着远处。又过了两天,老余的嘴唇干枯了,起了一个大水泡,他说:“为什么二妹没有一点消息,她怎么啦,她在哪里啊?”声音里透出焦虑和绝望。
妻子打电话叫来了老余的妹妹、妹夫,叫来了她的弟弟、弟媳妇,叫来了老余的两个朋友和一个同事。家里挤满了人,这才把真情告诉他。
老余的嘴张开了,咝咝地发不出声音,眼睛成两个窟窿,似有冷风从里面窜出来。他愣了半天,一耸身奔上阳台去。一屋人都呆了,他的妹夫看出来了,猛跑几步,抱住了他。好险啊,老余一条腿已经跨到栏杆外,半个身子都在外边了。妹夫叫一声:“还愣着干什么?”屋里的男人都冲上来了,伸出一条条手臂,摁住了他。像是餐桌上上了一道菜,许多双筷子一齐插上去。
老余在众人的手下挣扎、冲突,额头撞上了桌子角,撞出个窟窿,鲜血直冒。大家脸吓黄了,叫嚷着,找来了药和纱布,给他包扎好。老余还在挣扎,直到力气使尽了,他倒在地下,从齿缝里漏出话:“让我去死。”
此后一个月,老余躺在床上,亲友、同事,轮流看着他,不敢有一刻离开。一个月后,他起来了,背佝偻了,开了门出去,没走几步,抖抖地回来了。大妹说:“爸爸,我搀你出去走走。太阳挺好的。”她低着头,不敢看老余的眼睛。老余说:“看我,你看着我。”大妹抬起眼睛,看一眼老余,赶紧落下了。她怕老余眼里的嗖嗖冷风。老余说:“你谈男朋友,怎么害了二妹?你害人呀!”
大妹怔住了,脸色发白,继而发青、发黑,忽然嚎啕大哭,哭倒在地下。老余的妻子从里屋跑出来,扶起了她,不停地用手抚她胸口。大妹还是哭,后来,哭不出声音了,只有嘶嘶声。再后来,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
老余打开他的柜子、箱子,拿起这个,放下,又拿起那个,摸索了半天,终于找好一样东西。那是一个锦缎蒙面的盒子,做得精致,不大,也就三寸来长,两寸来宽,装的是一块寿山石,是老余6年前出差到福建买的。他把寿山石取了出来,在二妹的骨殖里挑了一块,大小差不多的,放了进去。
大妹在旁边,看清楚了,脸都骇白了。
从此,老余就把装有骨殖的盒子揣进了怀里,走到哪里都带着。他去上班了,不坐车,步行去。走了一段路,他就停下来,拿出锦盒,说:“囡囡呀,你走累了吧,我们歇歇。”他双手捧定了锦盒,在长凳上坐下。一会,太阳从云层后露出来了,到处都闪耀着金色的光芒,草地、大树披了金光,楼房和车辆也是金闪闪的。老余就对着锦盒说:“囡囡呀,太阳出来了,你暖和吧。哦,我看见了,太阳照在你的脸上了,太阳照着你的长发了,啊啊,太阳照着你整个人了。”
到了单位,忙过上午,吃午饭了。老余把饭打回来,放在办公桌上,先不吃,打来一盆水,就从怀里掏出锦盒。他坐在饭菜的一边,盒子放在另一边,旁边放了碗筷。他说:“囡囡,要吃饭了,你洗洗手吧。”他说了,恍然听见了哗哗的水声。等水声停了,他说:“囡囡,你洗过了,爸爸来洗了。”两个都洗了,他就把饭盒打开,说:“囡囡呀,爸爸晓得你喜欢吃鱼,买来一条糖醋大黄鱼,明天再买红烧对虾。”
办公室里人起先弄不明白,等到大家明白了,吓得不轻。人死了,谁知道还有没有阴魂,老余天天带着阴魂来,不吓人嘛?于是在背后纷纷议论,科长就动了老余的桌子,让他坐到边上去。但大家觉得还是不行,还是在一个屋子里啊。科长认为确实是个问题,就放弃一个休息天,带了两个小青年,把仓库整理了一番。到星期一,老余来上班时,发现他的办公桌已经在仓库的角落里。
老余发现,大妹不见了,过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看见,他问老伴了,她说,大妹受不住了,搬出去住了。老余没有再问。
老余神魂颠倒的,大家看了都着急,妹夫劝他说:“中国人讲究叶落归根,我问过风水先生,人离开了,还是入土为好。”老余说:“我是她的爸爸,就是她的土。她在我怀里,已经在土里了。”
单位里觉得他病得不轻,也不见有治好的希望,刚好机关里精简人员,就让他提前退休了。老余没有觉得不好,退休了,时间就多了,更可以和二妹厮守在一起了。天冷了,他就在锦盒外包了羊毛围巾。天热了,老余让人在卧室里装了空调,那时候市场上刚有空调,老余觉得自己年岁大了,吹空调不一定好,但他想女儿年轻,一定喜欢新鲜玩意。他对锦盒说:“囡囡,凉快了吧,以后每年夏天我们都开空调,这点电费不算什么,爸爸付得起。”
他带着女儿的骨殖到处走,一天忽然想起,二妹年龄不小了,差点耽误了。他来到花园里,坐在一条欧式的长椅上,和二妹商量开了。阳光从树叶缝隙中透下来,老余眯起了眼睛,他说:“囡囡,你看中哪一个了,爸爸替你参谋。小张皮色好,人也英俊,配得上你,你说他业务挺钻研的,那好。可是,我见了他两次,总觉得有点油,爸爸担心你将来吃亏。小赵高高大大的,模样不错,也很上进,我看他比小张要忠厚。听说他的妈妈挺厉害的,就怕你将来婆媳之间不好处。罢罢,二妹,你说你想和哪个谈,爸爸尊重你的选择。现在的世道,女孩找一个厚道、靠得住的男孩不容易。你选小赵?对啊,爸爸心里也是倾向他。”
老余站了起来,说:“你和他见面,就坐这条长椅子。”他把锦盒端放在椅子上,后退了十来步,“爸爸就藏身在这棵大树后,或者装作不认识走过来。啊啊,你不愿意?”老余笑了,走上前,端起了锦盒,“爸爸说说玩的,不来打扰你们,你放心谈。不过,在定终身之前,请他庄重些,不能让他看轻了我们。”
又好些年过去了,锦盒依然揣在老余怀里。
一年秋天,老余从外回来,一脸惊慌地说:“不好,二妹生病了。她呕吐了,还发高烧。”老伴在拣菜,看看他也不回答。老余说:“老太婆,你耳朵聋了?我跟你说,二妹发高烧了。”老伴说:“我耳朵不聋。”
老余说:“你说怎么办,现在上海传染甲肝,很可能她传染上了。”老伴顺着他说:“有什么办法,传染上了就去看医生呗。”老余在地下转了两圈,出门了。老伴想想不对,追出门去,已经不见他踪影。
老余一路跑到医院,好在也不远。他坐在医生面前,急慌慌地说:“二妹生病了,发高烧。”医生不明白他说的是谁,对他说:“张开嘴。”老余疑惑地张开嘴。医生摸他额头,皱起眉头说:“你没有发烧。”老余说:“不是我,是二妹。”医生说:“她人呢?”老余从怀里掏出锦盒子,放在桌上。医生问:“这是什么?”他说:“二妹呀。”医生生气地说:“你搞什么名堂?我问你,她人呢?”老余说:“这就是二妹啊,我感觉出来了,她在发高烧。”医生板着脸说:“你把它打开。”
老余把锦盒打开,嘴里说:“阿囡,医生来替你看病了,你忍着点啊。”医生探头看了,骇得脸色发白,说:“你搞什么鬼!拿走,快拿走。”老余说:“你还没有替二妹看病,我求你了。她已经说胡话了。”他抖抖地伸出手,抓住了医生的衣袖。医生跳了起来,身子往后缩:“如果你再不走,我叫保安了。”
老余踉踉跄跄回到家里,脸上有股黑气,两手捏住了锦盒,说:“医生不给看,还要叫保安赶我走。”老伴这才发现问题严重了,说:“你不要急,你要是急出病来,谁照顾二妹啊?”老余想这话不假,就说:“你倒点水给我喝。”
第二天中午,医生送走最后一个病人,走出门诊室,听见有人喊他,转头看,见门外恭恭敬敬站着一个老妇女。医生问:“你有什么事?”老妇女说:“求你了,救救我家老头。”医生说:“谁是你家老头?”她说:“就是昨天拿着个盒子来找你的。”医生说:“想起来了。我问你,你家老头是不是精神有毛病?”老妇女说:“在别的地方,他都没有毛病,在这个地方,不光有病,还病得很重。”她把许多年前大妹被人缠住,二妹去说,却被掐死,而老余寻死寻活,把骨殖藏在身上,前前后后全都说了。医生怔住了,说:“原来这样啊。”
老余的老伴说:“昨天夜里,我家老头子一直在床上翻身,弄得我也睡不着。天麻麻亮了,我才迷迷糊糊睡着,他突然一脚蹬醒我,喊起来,二妹昏过去了,再不看医生,就救不活了!”医生陷入了沉思,说:“你别急,让我想一想。”
当天,医生跟分管院长讲了。院长说:“有这样的事?你等一等,我这阵真忙。”一小时后,分管院长找来了,说:“这事院里不好决定,你自己看着办吧。不过,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医生心里还是没有底,回家对妻子说了。妻子愣住了,过一会说:“都说世风不好,还有这样的事!你去看吧。”医生说:“我给人看了20多年病,还从来没有给亡灵看过病。”妻子说:“你不是给亡灵看病,你是治活人的病。”
老余歪斜在床上,怀里抱着锦盒,一声声地呻吟着。老伴激动地跑了进来,说:“老头子,二妹有救了,医生来了。”老余倏地坐了起来,说:“真的来了?”
医生带着一个护士,走进来了。医生说:“你在床上躺着,不用起来。”医生就在床边坐下,老余拿出锦盒,放在床头柜上。医生抽出笔,在纸上划拉,说:“给她配了营养液,和药放一起,每天给她挂两次水。五盒板蓝根,每天喝三包,开水冲服。”护士一一答应了,从药箱里拿出玻璃器皿,弄得乒乒乓乓响。医生又说:“这病不可怕,只要治好了,就不会复发。让她好好休息。不过,发病期间有传染性,你们家里吃饭,碗筷要分开,不要传给你们老头老太。”
老伴说:“我们一定注意,不让传染开。”
医生和护士走了。第二天,他们又来了,还是吊水、吃药。一连来了五天。
老余的脸色慢慢地红润了,早晨,他从床上爬起来,捏着锦盒,走到窗前。老伴忙上来,拉开了窗帘。老余往窗外看,他看见了远远的青山,山上有茂密的树林,林间飘着蓝色的山岚,太阳从山后露出脸来,山上就腾起了快活的火焰。他回头对老伴说:“二妹的病好了。”
眼看春节到了,老余散步回来,老伴颇为激动地说:“老头子呀,你女儿要来看你了。”老余不解地说:“女儿来看我?她不是天天和我在一起?”
老伴在他背上捶一下,说:“你啊老糊涂了,你不是还有一个女儿嘛?大妹呀,她早成家了,我早知道了,一直没敢和你说。你女婿挺有出息的,不吃大锅饭,自己下来干,开了一家长途客运公司,干得有声有色。大妹一直想着你,快到春节了,她要带着女婿,带着7岁的小儿子,一起回家看你,给你拜年。”
老余嗯一声,就没有话了。老伴说:“你什么态度,说话呀,大妹等你话呢。”老余张了嘴,嘶嘶的却没有声音,突然咳嗽了,越咳越猛,吐出痰来,带着血丝。
老伴和女儿通了电话,说是大年初二上午就来。到了初二,老伴一再关照老余,今天一定不能出门。老余就在客厅里坐定了。老伴张罗起来,又是剁鸡又是烧鱼,等有了喘息时间,回头一看,老余不见了,两个房间里都没有他。老伴急起来,出门找,前弄堂后弄堂都找遍了,没有他踪影。她叹了口气,走到家门口,一辆银灰色的汽车刚好在门前停下,车窗玻璃摇下了,大妹探出头,直喊:“妈妈,妈妈!”开车的是女婿,他一身衣服都是新的。他走到车后,打开后备厢,满满的,全是吃的东西,有冬虫夏草、西洋参、阿胶,有无锡肉骨头、杭州小核桃、南京盐水鸭、宁波汤圆,还有苹果、芒果、柚子。老余的老伴说:“你们来就是了,还带这么多东西。”“不多,不多,都是他置办的。”大妹指着她丈夫说。
一个小男孩蹦到她跟前,他穿一套咖啡条子的小西装,还系一条红色的领带,说:“你是我外婆吗,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你。”她还没有回答,大妹就在男孩身上拍了一下,说:“没有礼貌。快叫外婆。”男孩叫了,老余的老伴掏出早准备了的红包,塞给了男孩。大妹说:“爸爸呢?”声音里有不安和紧张。老余的老伴又叹气,说:“刚才还在厅里,我和他说得好好的,转眼就看不见了。”大妹眼睛红了,说:“爸爸还没有原谅我。”女婿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摸着她的肩膀说:“不要这么想,说不定爸爸有事。”
大妹问:“爸爸用拷机吗?”她说:“不用,给他也不要,说是会打扰他。”
女婿和大妹相互看一眼。大妹就问老余常去哪些地方,问清了,女婿出门开动车,两人一起去找。老余平时去的地方,他们都找遍了,没有见到。回到家里,已经一点了。老余的老伴说,不等了,饭菜早冷了,我们快吃吧。
他们吃了饭,下午回去了。
这时,老余正在郊外的果园里悠哉游哉。上午,他是想在家里等大妹一家的,可是心里总抹不平,趁老伴不注意,走了出来。也不知往哪去,一辆公交车开来,他就上车了,没想到是开往郊区的,干脆坐到底,下来是个果园。他进了果园,没见几个人。冬天的太阳懒洋洋的,照着浅黄色的泥土,园子里有青蓝色的烟气,氤氲在果树的枝头。老余掏出了锦盒,说:“二妹,大妹回家来了,你说我是应该在家呢,还是跑到这里来比较好?”他似乎听见了二妹的声音,说:“哦,你也让我在家里等她,可是我已经跑出来了呀。大妹带了她的儿子来了。啊,想起来了,你也应该有儿子了。”
老余就往一棵棵果树下看,仿佛真有一个男孩躲在树后,跟他捉迷藏。他高声地说:“你在这呢,小东西!我看见你了。”他张开两手,向树后搜去,这时,阳光忽然强烈了,在这灼灼的晃眼的光亮中,老余看见二妹的儿子了,他从一棵树后跑出来,又躲到另一棵树后去,像兔子一样灵活。阳光照在男孩的额头上,那里就和玉一样白净,他的眼睛像二妹,嘴也像二妹,鼻子大概像小赵吧。老余淌汗了,他一棵一棵树搜过来,“你溜得好快呀,小东西,看我逮住你!”老余跑起来了。眼前出现了奇幻的景象,树干变成了男孩,男孩变成了树木,两者连成一片。他直喘粗气,倚在一棵树上:“我累了,跑不过你了,你比二妹小时候还调皮。”老余似乎听到什么动静,抬起眼睛,这时,他看见二妹了,她仿佛是从云端里下来的,她还和以前一样,20多年了没有变。二妹袅袅婷婷地向他走来。他张开了嘴,身子像筛子一样抖动。他张开两手,向二妹跑去,可就是走不到她身边。她袅袅婷婷地走,也好像一直在原地。她双肩披着太阳的七色光彩,灼灼闪亮。她本身就是一道光,只能看见,却不能抱住。
“二妹!”他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喊声。他听见二妹说:“我苦啊……”
老余拿出身上所有的力气,向她跑去。忽然心口一阵绞痛,眼前冒出金星,一条腿慢慢跪下,另一条腿也跪下,倒在地下。
老余躺在病床上,大妹来了,她哭喊着进了门,跑到床前,抓住老余的手,把脸伏在他的手上,跪了下去。她没说几句话,一直在哭。老余的手上都是大妹的泪水。老余老泪纵横,说:“怎么来说,你们都是老爸的女儿。”
大妹说:“这么些年了,我天天想你,想妈妈,是我害了这个家……为什么不是我死,让二妹侍候你老人家呢?”
他说:“你起来,起来呀。以后你经常来家吧,和我、和你妈说说话,也和二妹说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