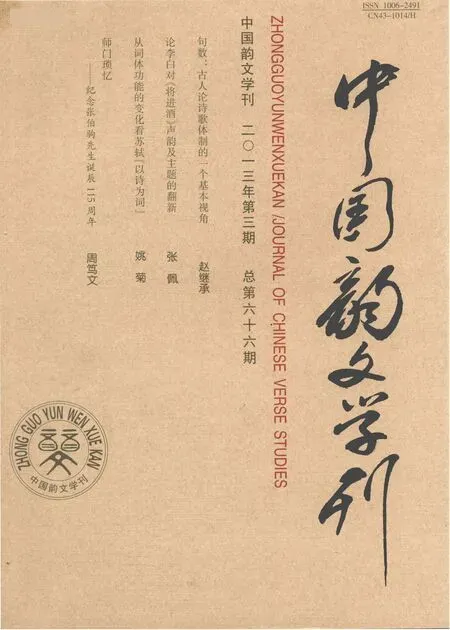从本体到历史:玄言诗的重新定位——读杨合林《玄言诗研究》
2013-11-14刘泰然
刘泰然
(吉首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文学史眼界的拓展,曾经属于边缘现象的玄言诗研究亦逐渐成为热点,产生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围绕玄言诗,研究其义界、源流、发展阶段、类型、创作机制、文本特征、审美个性,玄言诗与佛教、玄学的关系,玄言诗与山水诗的联系,以及某些具体的玄言诗人如郭璞、陶渊明、谢灵运等。这些成果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上有所发明,为进一步研究玄言诗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但是与此同时,有关玄言诗的某些基本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澄清,研究者往往从各自的倾向与视角出发去剪裁文学史材料,从而都能得出某些看似自圆其说的结论,但各个不同结论之间却往往存在着不可弥合的冲突与矛盾,难以达成共识。这一方面体现出学术研究的多元化以及玄言诗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一种更为客观的历史评价尺度的缺失。就这一点而言,在近年的研究成果中,杨合林《玄言诗研究》一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的缺欠,可以为重新探讨玄言诗提供一个新的起点。
一 玄言诗研究的状况及问题
在具体评价《玄言诗研究》这本著作之前,不妨对玄言诗研究的一些基本状况及问题略加梳理和探讨。
(一)玄言诗的义界问题
有关玄言诗的义界,不仅关涉到玄言诗研究的起点,而且关涉到如何理解和看待玄言诗的问题。学界对于玄言诗的界定大致有这样几种:
一种是从内容上加以界定,强调玄言诗与老庄哲学以及玄学的关系。王钟陵认为:“凡是以体悟玄理为宗旨的诗,概属于玄言诗。”钱钢指出:“玄言诗,顾名思义是以诗的形式说玄言。”詹福瑞指出:“所谓玄言诗,主要是指受清谈风气影响而产生的以表述老庄思想为创作意图,理过其辞、平淡而缺乏诗味的作品。”
这种界定方式强调玄言诗与玄学义理或玄言的关系,抓住了玄言诗有别于其他诗歌的基本方面。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值得追问:一方面玄言以及玄学本身的内涵和外延如何界定?如玄学与老庄、儒学、佛教之关系究是如何?另一方面,玄言诗与玄学(玄言)的关系亦界定不明:以诗的形式铺陈玄理和以诗的形式体悟玄理是不一样的,是否它们都是玄言诗?玄言诗说玄言的方式是否是一成不变的?玄言诗是否也有自身的诗性特质?
第二种界定方式强调玄言诗所具有的审美特质。黄新亮指出不能用“逻辑思维写的”笼括东晋玄言诗的特征。许总进而指出玄言诗是以“清谈‘言约旨远’的语言特征及清谈者‘麈尾扣案’的举止神态”所体现出的“一种极具艺术性质的精神风度”为“契机”,又与“自觉时代的文学艺术汇流”而形成的。此外,邓福舜、张廷银等亦持相似观点。这种界定方式注意到玄言诗自身的审美特质,无疑对问题有所推进和深化。但问题是,玄言诗是否从头到尾都具有这样一种不变的审美和精神特质?
第三种界定方式是从思想方式入手。对于玄言诗界定的莫衷一是,胡大雷提出了一种新的关于玄言诗的界定方式。他指出“以玄学思想方法来体悟玄理的诗,才是典型的、完全的玄言诗”。这一界定自然比前面两种界定要更为深刻,也很有启发意义,因而被不少玄言诗研究者所认同和接受。
对玄言诗义界的层层推进,意味着玄言诗研究在不断走向深入。但以上诸种界定不仅侧重点不一样,而且有时还相互冲突,对此,有学者甚至主张我们应该放弃那种个人化的界定方式,而回到南朝时代,根据刘勰、钟嵘的批评来理解什么是玄言诗。这种将某一特殊历史时期对玄言诗的评价当作玄言诗界定的不易标准,不免有非历史的倾向,不仅未能顾及南朝以后历史上有关玄言诗的新的评价,而且也会使现代玄言诗研究的成果失去意义。
(二)玄言诗的历史阶段划分问题
对玄言诗历史阶段的划分同样存在较多分歧。如何给玄言诗划分阶段,不仅要考虑到玄言诗在内容、风格上的嬗变,而且还需要考虑到玄言诗在思维方式、表现方式以及类型上的赓续和转换。
关于玄言诗的起始阶段,有学者认为玄言诗的起始阶段要从过江之初开始算起。葛晓音、王钟陵皆持此种观点。又有学者依据檀道鸾“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的评论,以郭璞为玄言诗的创始人,陈顺智、张俊以两晋之际为玄言诗发展的初期阶段,郭璞、庾阐为代表;以东晋中期为玄言诗发展的中期阶段,孙绰、许询为代表;以东晋末年为晚期阶段,殷仲文、谢混为代表。卢盛江同样把玄言诗的起始阶段定在东晋时的庾阐。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依据钟嵘《诗品》中的观点认为郭璞是“反玄言诗风的健将”,并带来诗文的中兴。
有更多的学者认为玄言诗的初始阶段应该从正始时期算起。如李绍华、陈洪就认为正始时期的嵇康、阮籍之作已经属于玄言诗的范畴。龚斌也把玄言诗的初始阶段放到正始时期,并将玄言诗分为三个发展阶段:魏正始至西晋永嘉为形成期,东晋建武至义熙中为兴盛期,晋安帝义熙中为消退期。而张可礼则依据刘勰的观点把玄言诗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产生期(正始),停滞期(西晋),兴盛期(东晋),衰退期(宋初)。
总体来看,学界对玄言诗历史阶段的划分越来越趋于明晰。通过对历史现象的不断清理,对玄言诗的存在状况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对于玄言诗的变异性及其历史连续性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这个认识的过程表明,不能孤立地看待玄言诗的历史,如果对玄言诗与整个历史的上下文关系缺乏足够的理解,就有可能缩小玄言诗的历史内容,不但认为正始与玄言诗无涉,而且也容易将郭璞、陶渊明、谢灵运等诗人从玄言诗的行列中切分出去。我们不仅要呈现作为一种现象的玄言诗的变化历程,还要揭示这种变化的历程后面玄言诗之所以如此变化的逻辑运动机制。
(三)玄言诗的类型区分问题
玄言诗是一种复杂多变的动态的历史现象,只有通过对玄言诗不同类型及表达方式的区分与梳理才能认识清楚玄言诗自身内在的历史性差异,才能具体地、历史地去把握玄言诗。玄言诗类型及表达方式的划分也有一个由现象把握向逻辑归类演变的过程。
胡大雷从玄言诗表述玄理的角度将玄言诗分为五种,即:“具体述说玄理、从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体悟玄理、叙写人物的玄学精神风貌、叙写玄学人物的理性活动、叙写玄学人物的现实生活。”稍后,他又对此作出修正,将玄言诗分为四种类型:赠答式、咏季候式、直咏老庄式、观览景物式。这是比较早的对玄言诗进行的分类,是一种意在全面、清晰把握玄言诗的有益尝试。
与胡大雷不同,辛文、黄志浩提出了另外一种分类方式,他们根据与玄学的不同亲和程度,将玄言诗在内容上分为两类:(1)直接阐释玄学义理(包含老、庄、佛理)的作品;(2)个性化的表达中包涵着老、庄、佛理思想意蕴的作品。并进而在表达上将玄言诗分为四类:(1)抽象说理的诗;(2)用形象包蕴玄理的诗;(3)具有个性表达的玄言诗;(4)与其他类型诗歌如游仙诗、山水诗杂揉于一体的玄言诗。这种分类,实际已注意到玄言诗内在质性的变化。王澍则将玄言诗分为直言玄理、游仙体道、山水悟道三类,在对玄言诗作现象描述的同时,实际也兼顾到了其内在逻辑的展开。
还有学者明确意识到从思维方式上将玄言诗予以归类的重要性,王钟陵指出,“凡是以体悟玄理为宗旨的诗概属玄言诗。体悟玄理有两条途径:一是直接从理性入手,二是从感性形象入手。前一条途径形成枯燥的说理诗,后一条途径则能够产生出一些将一定的感性的形象性和一定的理性内容结合起来的篇什。”此种分类方法显然更为清楚,只是他在具体的文学史发展逻辑的探讨中,更多地着眼于汉末以来的感伤主义思潮与消释感伤思绪的玄学思潮之间的关系,而未能就体悟玄理的两种方式充分展开。
玄言诗历时近二百年,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式、媒介和载体,内容上也是屡有推移和变迁。如何通过玄言诗类型的划分,准确把握玄言诗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逻辑进程,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四)玄言诗的历史评价与定位问题
事实上,对玄言诗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指向如何在大的文学史背景下把握、理解玄言诗,也即如何给它以正确的评价和定位的问题。玄言诗作为一个从汉魏文学到南朝、乃至唐代文学转换的中间阶段到底起到了一种怎样的历史作用?玄言诗自身又是以一种怎样的历史性变化来承续和衔接几个在审美特质上完全不同的时期,从汉魏慷慨咏怀、到南朝清新体物、再到唐代空灵造境,文学史是否可以略过玄言诗的时代而得到清晰的阐明?
很长时间以来,文学史研究往往把玄言诗视为一个尴尬的异质性存在,在文学史书写中往往予以简单化的处理,至今仍不免有将玄言诗看成是一个可以从整个文学史的大传统中予以剥离出来的异质性存在的倾向,这使得对玄言诗的评价与历史定位难以趋于一致。
一种观点是全盘否定玄言诗。钟元凯认为:“玄言诗的出现无疑是文学史上的一股逆流”,“不但阻遏了山水文学的发展势头,而且造成了严重的诗歌危机,它对文学的作用也终于从助力转化为阻力。”徐国荣则更是以为“玄学和诗歌联姻”是“门不当户不对”,“可谓双重失误”,“从玄言诗主体的创作心态可以看出,玄言诗其实是一种‘雅化的世俗’,而山水诗则只是对玄言诗误入歧途时的无意间的一种拯救。”江云岷、韩国良则直接认为玄言诗不过是受了玄学之风不良影响的诗歌。
另一种观点是全盘肯定玄言诗。如祝振玉认为玄言诗“反映着当时人们思想的成熟与自我意识的觉醒”,它的流行“不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危机,而是向成熟转变的契机”。裴斐认为“玄言诗一反汉人歌功颂德的风气,集中抒写个人的思想感情,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黄南珊则认为晋代玄言诗表现了以玄为尚、以淡为美的美学观,它以情体道、情道同化的美学取向,既是对儒学的以理制情、“以情从理“的传统思维范式的有力反叛,又是对六朝尚情重情、畅情求美时代美学新潮的超拔,是对以情感为重心的诗艺建构的第一次冲击。
除了以上两种理解方式之外,有的学者试图将玄言诗放到一个更大的文学史框架中来理解。葛晓音对玄言诗与山水诗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考察,她认为玄言诗“风行文坛一百多年,对山水文学的发展确是一种阻力”,而玄言诗集中探讨了山水与自然的关系,“对山水诗的发展又是一种助力”。而许总认为中国哲理诗经历了从玄言诗到道释诗再到理学诗三个阶段,玄言诗对后世的哲理诗影响巨大。王澍认为,玄言诗风行文坛逾百年,其影响不可低估,主要表现在它对后世其他类型言理诗的影响、对后世文人精神风貌的影响和对后世文学审美观念的影响等方面。
王钟陵的分析更为深透:“诗歌史发展的本身逻辑,需要一个对主体内在感荡意气和万端悲慨加以消逝的过渡性的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便是玄言诗阶段”,“这一中间环节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因为如果不明白中间环节的面貌及其所起的作用的话,那么魏代和西晋诗歌变为南朝诗歌的轨迹就不易看得较为清楚。”他认为在研究汉唐文学的“来龙去脉”时,汉代文学是“来龙”,唐代文学是“去脉”,而玄言诗阶段则是联结“来龙”与“去脉”的“中介”。王钟陵是玄言诗研究领域历史意识浓厚的学者,只是他的研究更多地是从文化思潮与审美心理的嬗变角度研究这一“中介阶段”,而没有着眼于思维方式与文学表达方式的历史性变化。
对于玄言诗的历史定位,应该不是简单的否定或肯定,而是将其放到文学史自身的理路中去加以把握;同时,在探讨它与后世文学之间的关系时,也最好不要简单地认为它阻碍或是推进了某种文学形式、文学体裁的演进,而是要意识到玄言诗是作为一种精神现象进入到文学史、艺术史;而一种艺术精神的演进有它自身的逻辑,如果没有经历玄言诗那样一个阶段,后续的阶段是不可设想的,中国艺术精神的发展就会缺失掉一个环节,文学史的书写就会产生断裂。或者,我们可以问:没有玄言诗,何来山水诗?甚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没有晋风,何来唐韵?
二 从本体到历史:《玄言诗研究》的意义
可以看出,有关玄言诗研究的几个方面——义界、历史阶段、类型、历史评价与定位——是相互联系的,对其中一个方面的认识往往决定着对另一个方面的理解。只有全面地将玄言诗的各个方面加以把握,这种研究才有足够的历史阐释力。历史性的维度或视角指的是:这种历史一方面是玄言诗自身的历史,另一方面是玄言诗与整个文学史的关系。
在这方面,我认为杨合林的《玄言诗研究》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其开拓性在于将本体研究与历史研究有效结合起来,既注重玄言诗自身的发展理路,也注重它与整个文学史上下文之间的关系。这不仅加深了我们对玄言诗本身的认识,还弥合了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史上缺失掉的一个关键性环节。
在义界问题上,作者认为:“玄言诗从发生到终结,历时近两个世纪,有一个起承转合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玄言诗的型态呈现出不稳定性和多样性,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特点,不同作家有不同表现,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也可能呈现出不同的风貌。玄言诗的定义,应将此近二百年中出现的该类诗概括和涵盖起来,在诸多变式中见出其基本性质。”而玄言诗的基本性质则要从它的思维方式、基本主旨和审美风格诸方面来加以说明。
作者采用了从思维方式入手的玄言诗界定方式,他认为玄学的思想方法是“言意之辨”,具体表现为“言尽意论”和“言不尽意论”两种意见。与之相对应,玄言诗在思想方法上有“铺陈玄理”和“立象尽意”两种,玄言诗便也有表达玄学义理和表达玄学意趣两种类型,“表现玄学义理的玄言诗,是哲学概念和思想的韵语化,而表现玄学意趣的玄言诗则是哲学的诗化。”早期的玄言诗多以“铺陈玄理”为主,事实上是“言尽意论”在玄言诗中的体现,而随着玄学思想方法的展开,“立象尽意”开始成为玄言诗的主导。“这一转化的过程,实际就是玄言向田园、山水演化的过程。田园、山水之所以在诗歌中出现,就在于田园、山水既是玄学之士体会、领悟玄学精神的‘自得之场’,同时又是传达玄学意趣的表意之‘象’。”在对玄言诗义界的把握中,玄言诗自身的类型及历史理路清晰地呈现出来。
在有关玄言诗类型的分析中,除了有关“铺演玄理”与“立象尽意”这种基本划分外,还有更细致的逻辑性区分。就“铺演玄理”而论,有两种情况,“一是从玄学名言、概念出发铺陈玄理,一是从切实的人生感受出发体认、体证玄理。”而“立象尽意”又可以分为三类:“《老》、《庄》之象、虚拟之象和实在之象。三者依次展开,构成了玄言诗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
初期玄言诗从老庄思想而来,故其意象亦多直接或间接取自《老》、《庄》,何晏、阮籍、嵇康诗中多有此类表现。而嵇康诗中对玄远之境的开拓和他善为虚拟之象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其诗中多通过想象的“虚冥之境”来表达其精神诉求。而到嵇喜、庾阐之后,想象的逍遥之境逐渐落实于现实的“水滨兰渚”,并开始对现实山水进行直接摹写。王羲之的《兰亭诗》及其组织的集会赋诗活动更是凸显了山水在诗歌中的作用。到湛方生,山水诗又有了新变,山水中的“理”已不再是固有的“玄学义理”,而是“悠远的生命意趣”。谢安诗歌则更是从玄学义理中跳出,以日常生活入诗,“无疑开了陶渊明田园诗的先声”。再通过玄学理论中的“形神之辨”的作用,使得体物的方式与观照事物的眼光进一步深化,“立象尽意”的艺术手法亦真正走向成熟。于是中国诗歌到了陶渊明、谢灵运这里,“方有大量意、象圆融的诗篇出现”,“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实际是一种意象圆融的玄言诗,代表的是玄言诗的最后和最高阶段”。
在这里,有关玄言诗的义界及类型、主旨、历史逻辑等是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来把握的,因而玄言诗的义界与玄言诗的类型及历史之间的关系是内在的相互支撑的,这不仅源自理论本身的周全,更是源自一种深入和灵活的方法论的应用。
作者始终带着一种历史分析的眼光,玄言诗不再是静态的,而是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发展变化的逻辑过程。“玄言诗是流动的,它由前期向后期的演化,实为直陈玄理向立象尽意的思维和表现方式的转进。”在这种分析中,他试图做的不是经验概括,而是深入到玄言诗自身的历史逻辑中来实事求是地展现那种内在的线索。他将玄言诗分为“发端、发展、兴盛、蜕变”四个历史阶段,分别对应正始、西晋、东晋、晋宋之际四个历史时期。这种划分似乎并无多少新意,但是,这种划分并不建立在玄言诗内容与风格的递嬗基础上,而是体现出一种更内在的思维方式的转变,这几个阶段不是一种静态的并置,也不是一种有关玄言诗的种种客观知识的历时性切割,而是一种意识或精神的自我展开,是一种逻辑的必然性。
书中处处体现出一种良好的历史感,通过对不同时期玄言诗的分析,清晰地展示出玄言诗的演变之迹。对东晋初庾阐《观石鼓》分析道:“不再是玄理的直接铺陈,而是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受、玩味来体证、体悟玄理。……在这里,玄思开始与山水结合起来,玄言诗出现了新的趋向。”解读王羲之《兰亭诗》:“从《古诗》的‘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到玄言的‘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生命的情调与审美的视角发生的更替,正可见玄学的推动转移之功。玄学发展到东晋,已深入人心。同样是体会、感受到存在的有限性,但已经变换了眼光与情怀。”对晋末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的细读:“此种‘孤高之兴’虽未脱离玄理,但和玄理的直接铺演已是不同。‘理’中含‘兴’,或说从‘理’转‘兴’,正标示出玄言诗出现的某种蜕变。”至陶渊明,则“玄心独照,无往而非生命的乐境,先前的满腔‘怅恨’早已化为乌有。玄学的以理释情、以理化情,得到了真正的体现。在这里,‘理’之一字非但不曾出现,根本无迹可寻。而掩卷遐思,却分明又有一‘理’在,这就是玄学主张的‘委任运化’。”诸如此类亲切的具有洞察力的体悟所在皆是,所有这些都时时意在表现一种一以贯之的历史逻辑的分析方法。
这种历史感不仅体现在具体的玄言诗历史阶段的分析中,而且贯穿了整本书的各个环节。探讨玄言诗与玄学、道教、佛教的关系时,作者没有简单地在玄言诗与玄学、道教、佛教之间寻找各种因子的对应,而是试图揭示玄言诗发展的内在动因。在“玄言诗与玄学”这一节中,作者细致分析了从“经学人格”到“玄学人格”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名节’而‘诞节’,再到‘通而有节’的演变过程。‘名节’人格即经学人格,‘诞节’人格则是玄学人格的初始阶段,与‘名节’人格针锋相对。‘通而有节’人格则是玄学人格的完成。”而这种玄学人格的逐步展开正对应着玄言诗的历史进程,“嵇康诗风的清峻,永嘉诗风的清虚,东晋诗风的清通,正体现出不同阶段玄言诗的特征,而归根结底又是玄学之士人格特点的表征。”
在“玄言诗与佛教”一节中,从支遁的“以玄释佛”到康僧渊和张翼的佛玄之争,再到慧远剔除玄学因素以净化佛学,清晰地体现了玄学与佛学历史关系的三个逻辑阶段,同时也是玄言诗历史发展过程的文化逻辑的呈现。玄言诗的终结同样内含了文化的根由:“玄言诗在晋末的式微,原因是多方面的,慧远在庐山所推行的净化佛学活动,包括他本人和在他影响下的庐山僧团的创作及所显示的实绩,应是其间一个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慧远可谓是一个玄言诗的终结者。不过他并未完全脱出玄言诗的范畴,他是站在玄言诗的门槛之内来终结玄言诗的。”在这里,玄言诗不止是对各种文化因素的吸纳,实际还是不同文化思潮、观念之间的历史性互动的场所。通过条分缕析,玄言诗与文化思潮之间的这种复杂的历史关系,玄言诗自身的发展逻辑及其历史文化脉络被清晰地呈现出来。
所有这些工作最终带来的是对玄言诗的重新评价及重新定位。这种评价既要注意玄言诗内部在不同表现方式和类型上的差异,注意玄言诗本身的发展变化,同时也要将整个玄言诗及其所带来的思维方式、表现方式的变革放到一个更大的艺术史、文化史的背景中来加以把握。
中国艺术在东晋时代发生了一种历史性的转换,这种转换是如何发生的?“中国文学艺术何以至此而进入了‘新巧的境界’,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大画家顾恺之,大诗人陶渊明、谢灵运,一大批杰出才能之士何以汇聚于此,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在作者看来,这种转换与玄学以及玄言诗关系密切,特别是由于“立象尽意”的艺术表现方法带来了艺术史的决定性转折。“玄言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是特别的,这种特别不仅仅因为它的异质异态,更是由此种异质异态带来的诗歌品质的变化。玄言诗是玄学对诗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诗由言志缘情向体玄悟道的展开和推扩,这才有了思与诗的邂逅、交流和融合。玄言诗是言理的诗,其所言之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而是存在之思、形上之思,是一种宇宙意识和生命情怀。从此以后,诗的言说与思的言说联为一体、不可离析了。这赋予了诗歌新的内核,从而大大提升了诗歌的审美品质。”经过立象尽意、运思于诗,大大深化了中国文学艺术的精神品格,成就了真正中国式的审美方式。玄言诗从“铺陈玄理”转向“立象尽意”标识的正是哲学精神向艺术意境的转向。
从赋比兴、兴观群怨、诗言志、诗缘情再到对艺术意境的标举,中国艺术的对事物的观照方式以及功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化实为虚、寓无限于有限,打通形下与形上,情景交融、主客统一,“由此而言,玄学和玄言诗实开启了中国艺术的一个崭新时代。中国艺术在东晋发生的转折,东晋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独特地位,只有通过玄学和玄言诗才可以做出充分的说明。”没有玄言诗的洗礼,就不会有那样一种观照世界的眼光,也就不会有中国式的意境理论。
对玄言诗的研究不能仅仅对玄言诗做表象的、经验的归纳和概括,而应该深入到现象背后去把握那精神发展的线索和逻辑。文学史本身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玄言诗之前,文学史的状况如何?在玄言诗之后,中国文学史增加了哪些新的内容,这种内容与玄言诗有何关系?如何在一种更开阔的长时段的文学史语境中来理解玄言诗的历史意义?这些都是今天的研究所应该认真思考的。在探讨玄言诗与山水诗的历史性关联时,应该意识到玄言诗不止是作为一种体裁媒介,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引发了山水诗。玄言诗对后世的影响不仅是作为一种既定的题材、文体所发生的影响,而是一种思维方式、观照方式的陶冶与建构。
德国学者顾彬曾对中国古代的自然观演变的逻辑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现象学梳理,认为其经历了三个历史性阶段,只有到了唐代中国古代自然观才出现主观与客观、情与景之间的完美统一。他更注重禅宗在这种自然观中的作用。其实,如果忽略了玄学及玄言诗阶段,这种观照方式的转变是不可能完成的。经过玄言诗之后,中国文人观照自然的方式就改变了。因此,对玄言诗的研究不应该停留在玄言诗本身,而应该将文学研究与思想研究,将本体研究与历史研究有效结合起来,深入到文学史、观念史、文化史后面去把握中国诗歌观照方式演变的逻辑,应该体现一种研究的纵深感和理论的穿透力。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我们说《玄言诗研究》有其开拓性。尽管对这本著作中的某些具体分析和论断我们未必都会认同,但其所提供的方法和思路无疑是有益的、可取的。
[1]王钟陵.玄言诗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988(5).
[2]钱刚.东晋玄言诗审美三题[J].上海大学学报,1997(1).
[3]詹福瑞.走向世俗——南朝诗歌思潮[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1991.
[4]黄新亮.不能用“逻辑思维写的”笼括东晋玄言诗的特征[J].益阳师专学报,1997(2).
[5]许总.中国古代哲理诗三阶段的特征及发展轨迹[J].晋阳学刊,1998(1).
[6]邓福舜.东晋玄言诗的艺术价值[J].北方论丛,2000(4).
[7]张廷银.魏晋玄言诗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8]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J].文学遗产,1997(2).
[9]徐国荣.大陆近二十年玄言诗流变研究之检讨[J].暨南大学学报,2000(5).
[10]江云岷,韩国良.何为玄言诗[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11]葛晓音.东晋玄学自然观向山水审美观的转化[J].中国社会科学,1992(1).
[12]陈顺智,张俊.东晋玄言诗发展述略——东晋玄言诗研究之一[J].武汉大学学报,2001(2).
[13]卢盛江.玄言诗二题[J].北方论丛,1994(4).
[14]汪春泓.钟嵘〈诗品〉关于郭璞条疏证—— 兼论钟嵘诗歌审美理想之形成[J].文学遗产,1998(6).
[15]李绍华.正始玄言诗论[J].学术论坛,1997(5).
[16]陈洪.玄学的诗化与诗的玄学化——关于玄言诗的发展、特征和价值的再认识[J].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1(8).
[17]龚斌.玄言诗的流变[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3).
[18]张可礼.刘勰论魏晋玄言诗[J].文史哲,1995(6).
[19]胡大雷.论玄言诗表述玄理的五种方式[J].宁夏社会科学,2005(1).
[20]胡大雷.论东晋玄言诗的类型与改造玄言诗的契机[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
[21]辛文,黄志浩.魏晋玄言诗研究综述[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
[22]王澍.魏晋玄学与玄言诗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3]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4]钟元凯.魏晋玄学和山水文学[J].学术月刊,1984(3).
[25]徐国荣.从《世说新语》看玄言诗的世俗底蕴[J].暨南学报,2001(3).
[26]祝振玉.对东晋玄言诗的再认识[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3).
[27]裴斐.中国古代文学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28]黄南珊.以情体道 情道同化——略论晋代玄言诗的美学取向[J].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99(4).
[29]葛晓音.山水方滋,庄老未退——从玄言诗的兴衰看玄风与山水诗的关系[J].学术月刊,1985(2).
[30]王澍.论玄言诗对后世文学的影响[J].中南民族人学学报(人义社会科学版),2004(5).
[31]杨合林.玄言诗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2]W.顾彬.马树德译.中国文人的自然观[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