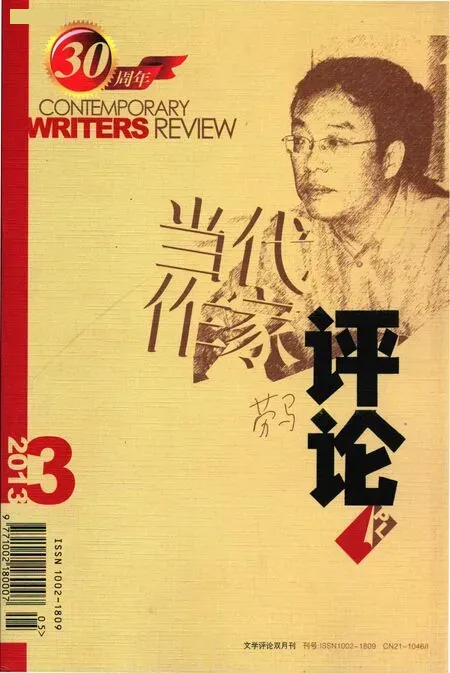论《带灯》的文学创新与贡献
2013-11-14栾梅健
栾梅健
在《废都》、《秦腔》、《古炉》诸佳作已然奠定当代文坛的重镇地位以后,贾平凹在最近发表的长篇小说《带灯》中,丝毫没有显露出半点的懈怠与马虎。据《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透露:“贾平凹把小说寄给《收获》后,先后修改了七八次,这在以前从未有过的。”这种精益求精、精雕细琢的认真精神,贾平凹在该小说的“后记”中也有表述。他自谦:“六十年里并没有做成一两件事件”,而作为献给自己六十大寿的生日礼物,他“企望着让带灯活灵活现于纸上”!
贾平凹的这种努力并没有白费。《带灯》甫一问世,便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带灯》的电子书版,单本定价十五元,借助腾讯阅读平台大量的用户群基础及强势的推广传播,获得了单月过万册的销售成绩”,而“结合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及各民营书店等实体渠道,今年年内《带灯》销量有望突破五十万册”。在文学日趋边缘化的今天,一年五十万册的销售量,在中国当下的阅读市场,无论如何都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不过,对于《带灯》细致而专业的评论,并没有如读书界的强烈反响那样同步跟上。相反,迅速出现的倒是几篇挥舞着大棒、逻辑混乱的“酷评”——这似乎已成了近年来文坛的一个规律。当一个在文坛享有盛誉的作家推出一部新作时,总是先有那么几篇断章取义、哗众取宠的骂派文章出现,譬如前几年余华的《兄弟》、莫言的《蛙》,均是如此。这其实是媒体时代司空见惯的恶习,不如此,媒体便不能吸引人们的眼球;不如此,批评家也难以获得人们的关注。
这次担任“酷评”重任的是两篇文章,均发表于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文学报》的“新批评”栏目。一篇是石华鹏的《带灯: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其主要观点是:
尽管贾平凹先生在表达上做了努力,也有对中国现实发言的想法,但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带灯》,其生命力还是出现了问题,正如一个古稀之寿的老人一样,浑身的钙质流失了,身体和精神都松垮下来了。
或许,缘于我们对贾先生的每一次写作都很在乎,期望在他那里读到真正出色的中国小说,所以才提出了非一般的挑剔与苛刻。但是遗憾的是,《带灯》在即将出色的最后一两步止住了,作者没有勇气真正地创造人物,去升华题旨,没有勇气去突破写作最后那道红线。
另一篇是唐小林的《〈带灯〉与贾平凹的文字游戏》,其大致观点是:
《带灯》换汤不换药的写作,只不过是贾平凹对其以往众多作品的一次大炒冷饭和文字大杂烩。贾平凹只不过是将《秦腔》中的张三,变成了《古炉》中的李四,再将《古炉》中的李四,变成了《带灯》中的王五。正因如此,《带灯》的外包装虽然有所改变,但其中的诸多细节和人物对话,都是贾平凹对其以往旧作的自我抄袭和重复书写。
一个与活色生香的现代生活如此隔膜的作家,贾平凹对陕西农村的描写,永远都是停留在其几十年前农村生活的灰色记忆之中。因此,即便是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今天,贾平凹笔下的陕西农民们始终个个都是土得掉渣。
尽管对于一部作品的评论,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尤其是一些在文坛有着重要影响的作家,自然还应该接受更为严格的检视与挑剔,不过,任何批评也都应该建基于对作品的认真审读之上,建基于公正、客观的评价体系之上。在反复阅读并思考以后,我们认为,《带灯》不仅不是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也不是一部自我抄袭与重复的文字游戏,恰恰相反,这是一部有着深邃的思想内涵与老到的艺术技巧的创新之作。它不仅在贾平凹的文学创作道路上是一次重大的突破,而且在中国文坛上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带灯》的突破,主要在于贾平凹采取了他以往小说中从未有过的“俯视眼光”。这种视角,既不同于他过去驾轻就熟的、从农村底层观察与描写的民间视角,也不同于当下文坛流行的、站在历史和道德的高度对社会丑态与官场黑暗加以揭露的反腐小说。
贾平凹出身于偏僻、落后的陕南,并在那里生活了十九年,自然,家乡便成为他最初,乃至很长一段时间的文学土壤。他的想法是:“以商州作为一个点,详细地考察它,研究它,而得出中国农村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以及这个大千世界的人的生活、情绪、心理结构变化的轨迹。”《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商州》、《浮躁》、《秦腔》、《古炉》等一系列作品,都可以看作是故乡给予他的哺育与滋润。“从生下来到十九岁离开,故乡我其实只呆了十九年,但是这十九年吧,这记忆一生都改变不了。比如说我现在回到我家乡一天时间,了解的情况比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比如说到一个工厂去蹲上一个月,收获要大。”贾平凹将他的故乡理解为“写作的根据地”,他从这里汲取到源源不绝的艺术养分与灵感。“十九年后,我离开故乡到了城市,但每一年最少回去三次四次。而且进城后,我的家几乎成了商州驻西安的办事处,家乡的人到我这儿很多……一来就在我这里住下来,或者还有来旅行结婚的,赴省告状的。这三四年来,我光为家乡人写状子,也不下五六份……所以,我身虽未回去,但也可谓是‘秀才不出门,却知天下(应该是商州的天下)事’了。”
但是,环境与身份的改变也必然会使作者萌生出新的创作理念,获取到新的文学素材。一九九八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高老庄》,抒写的是语言学家高子路教授携年轻、漂亮的画家妻子返归故里高老庄探亲的故事。高子路对故里的深深眷恋与失望,对传统文化的迷恋与忧思,显然表达的是长年在外生活的贾平凹对民间传统文化复杂性的揭示。而二〇〇七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高兴》,主人公刘高兴,《秦腔》中的书正就是以他为原型的,是与贾平凹在家乡一起长大的小伙伴。而他现在已随着滚滚的打工人潮来到了西安,在城南干起了拾破烂的活计。这可以看作是贾平凹对故乡商州人物的跟踪描写。“秦岭的南边有棣花,秦岭的北边是西安,路在秦岭上约三百里。世上的大虫是虎,长虫是蛇,人实在是个走虫。几十年里,我在棣花和西安生活着,也写作着,这条路就反复往返。”因而,除了商州的乡下,现在西安的城里也吸引了贾平凹文学注视的目光。
不过,《带灯》仍然与《高老庄》、《高兴》等作品不同,他所调动的是贾平凹已经有了四十余年之久的城市生活经验,是他作为文化名人和级别不低的公职人员的亲身感受。尽管《带灯》所反映的依然是他极为熟悉的商州故乡,然而,它表现的已不再是匍匐于土地上的普普通通的农民和简简单单的农村,而是将目光上移,关注于那个“辖管几十个村寨”、有着好几万人口的大镇,关注于那个上通下达、各种矛盾纠结与交错的镇政府。在《商州》、《秦腔》、《古炉》中,级别最高的主要人物往往是村支书,而在《带灯》中,他着力揭示的是权力大得多的镇政府以及镇长、书记,乃至在他们背后的县委卢书记、市委黄书记。
在一篇《精神贯注——致友人信之四》的文章中,贾平凹这样记述着他近年来忙碌的生活:“从元月起我一直在开会,过了春节,还要开会,可能四月前都在会上忙着。我是市人大代表,又是全国政协委员,各级的会议不能不参加……”除了市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之外,他的实职还有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美文》杂志主编,等等。对于自己的官职,贾平凹并不是特别在意,甚至有时还自我嘲讽。在《辞宴——答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六月十六日粤茶馆的饭局我就不去了。在座的有那么多领导和大款,我虽也是局级,但文联主席是穷官、闲官,别人不装在眼里,我也不把我瞧得上,哪里敢称做同僚?”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说:“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怀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但我有致命的弱点,这犹如我生性做不了官(虽然我仍有官衔)一样……”
“局级”、“官衔”、“著名作家”,是贾平凹在离开农村之后获得的另外一种身份认同。他若即若离,游离其间,在前呼后拥、豪华宴席之后,他常常陷于苦闷:“当官的开会是他们的工作,而我开完会后自己的业务还没有干呀!”
得失常常是在无意之间。当他在长时期的开会、应酬、视察、汇报、总结之后,对于那块生他养他、爱恨纠缠的商州土地,慢慢便有了新的领悟。从商州看商州,往往并不能发现问题的实质。以前,他感慨:“商州曾经是我认识世界的一个法门,坐在门口唠唠叨叨讲述的这样那样的故事……遗憾的是总难免于它的沉重、滞涩和飞得不高,我归结于是我的宿命或修炼得不够。”而现在,当他顶着“官衔”,熟悉了官场内部的游戏规则和内幕后,便恍然大悟于生活在偏僻商州土地上的农民,他们的生与死、爱与恨、穷与富,其实大部分都受制于商州之外的世界,是比村支书高得多的人物主宰着他们的命运。
如此想来,贾平凹在这次新作《带灯》中,将聚焦的视点对准了他认为是农村很多矛盾根源的镇政府。比起棣花街、古炉村,小说中的“樱镇”是一个要大得多的行政单位。它是一个纽带,下面是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的普通农民,上面则联结着形形色色的衙门与官员。中国的农村问题,必然会在镇政府这一层面聚集、纠缠与冲突。
在改革开放初期,正如贾平凹在商州系列中描写的那样,农村联产承包、个体经营、外出打工、种植贩卖,一切都还单纯与简单,然而,在三十多年的发展以后,深层次的矛盾愈益显示出来。就如《带灯》中所描写的那样:
以前镇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催粮催款和刮宫流产。后来……但不知怎么,樱镇的问题反倒越来越多。谁好像都有冤枉,动不动就来寻政府,大院里常常就出现戴个草帽的背个馍布袋的人,一问,说是要上访。上访者不是坐在书记镇长的办公室里整晌整晌地不走,就是在院子里拿头撞墙,刀片子划脸……
体制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法制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政治的问题、环境生态的问题,就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贾平凹的感慨是:“正因为社会基层的问题太多,你才尊重了在乡镇政府工作的人,上边的任何政策、条令、任务、指示全集中在他们那儿要完成,完不成就受责挨训被罚,各个系统的上级部门都说他们要抓的事情重要,文件、通知雪片似地飞来,他们只有两只手呀,两只手仅十个指头。而他们又能做什么呢?”来自上面和下面的矛盾都集中于镇政府,而镇政府负责来访的综治办便成了一切的火山口。这种对农村新状态的认识,并不仅是贾平凹一人。二〇一二年,刘震云的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表现的也是一个与当下生活关系密切且敏感的上访题材,李雪莲的上访乃至最后结局,都反映出了在矛盾日益尖锐的今天,改革已经进入到了深水区的关键时刻。而贾平凹正是凭着多年来对农村生活的熟悉,以及后来对于我国现行权力体系的运作与社会关系网的洞察,在《带灯》中给人们带来了他对农村问题的新思考,并进而在他的创作道路上形成了新的突破与迈进。
在《带灯》中,小说的高潮是使书记镇长仕途受挫、并使综治办主任带灯受到行政降级处分的、因争夺淘沙权而引起的特大型恶性群殴事件。对于元家和薛家的这次死伤多人的械斗,类似的情况在贾平凹以前的商州系列作品中,往往是被处理成家族之间的陈年恩怨与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而在这部小说中,贾平凹则注意到了事件的外在力量,并指出正是这种外在力量使得元、薛两家的矛盾越来越激化。由于大工厂基建的需要,元黑眼瞅准商机,给镇长送去两条烟四瓶酒,同时也顺便给综治办的带灯主任捎上四小桶蜂蜜,在许可证尚未办好的情况下就大张旗鼓地办起了沙厂。眼见利润丰厚,薛换布到县上托人找县委书记的秘书,秘书给县河道管委会宋主任打招呼,最后镇党委书记在明知河道狭窄、极易发生纠纷的情况下同意换布办起了第二家淘沙厂。其结果是斗殴造成死亡一人,致残五人,伤及三人,为十五年来全县最重大的恶性暴力事件。人们可以指责元黑眼、换布唯利是图、视钱如命,然而,官员之间的权力寻租、徇私枉法、贪污腐败,这应该才是造成许多百姓无辜伤亡的根本原因。这显然比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家族恩怨与文化差异要深广得多,也准确得多。
最典型地调动了贾平凹官场经验的,是小说中对市委黄书记的描写。作为“局级”的市委黄书记,与作为“科级”的樱镇书记似乎有着十分遥远的距离,不过,当镇“书记”活动了好长时间终于将黄书记请到樱镇来视察时,充分表现了中国政治的官场内幕。当黄书记即将到达樱镇时,县委县政府作了具体的行程安排与部署,其主要要点有:
……黄书记喜欢吃甲鱼,一定要保障。如果有条件,午餐期间有民间歌手献歌或农民诗人咏诗。一定要收拾布置好黄书记饭后休息的房间。
……组织一些村民与黄书记交谈,保证有各个阶层的人,必须有抱儿童的……去另一村子的一户人家访贫问苦。这人既要生活贫一些又要干净卫生,要会说话。黄书记要当场送一床新被子和三百元慰问金,镇政府提前准备好……
……讲话稿不用镇上准备,但多准备几个照相机,注意照相时多正面照,仰照,严禁俯拍,因为黄书记谢顶……
此几段要点让人发噱,又让人叫绝。如果不是同样身为“局级”的贾平凹细心观察,断不会在作品中有如此鲜活而真实的揭示。在这场热热闹闹、煞有介事的视察之后,镇政府的侯干事来报销的黄书记的“伙食费”是:“猪肉五十斤,菜油二十斤,萝卜一百斤,葱三十斤,羊肉二十斤,牛肉二十斤,鸡蛋三十斤,豆腐三十五斤,土豆六十斤,盐二十斤,花椒十斤,蒜十二斤,面粉八十斤,大米六十斤,木耳二十斤,黄花菜蕨菜干笋豆角南瓜片都是几十斤,各类鱼八十斤,鳖十八个,还有野猪肉、锦鸡、果子狸、黄羊,还有酒,酒是白酒四箱,红酒八箱,啤酒十箱,饮料十箱,纸烟三十条……”此外,还报了现金三万二千元,“镇政府放了一星期假”。在那样一个人均年收入仅有一千三百元的落后乡镇,如此的胡吃海花,银子花得像水似地流,怎能指望樱镇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呢?又怎能阻止穷红了眼的贫穷百姓一拨又一拨地上访呢?
在我们看来,小说中的“书记”,这个樱镇的党委一把手,是一个倾注了作者的许多心血并刻画得栩栩如生的人物。他是贾平凹小说人物形象画廊中的一个新收获。“书记”原是县长的秘书,没有什么文化,然而却人情练达、投机逢迎,在樱镇几次大事件中总能沉着应对,抽身而出。对于镇政府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与危险性,他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正如镇长所说的那样:“我也是学着书记哩,可就是学不会么,在镇上干了这几年,能体会到解放初期为啥国民党的高官反倒没事,枪毙的尽是乡镇干部,啥朝代里,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就是乡镇干部,乡镇干部也必定会罪大恶极……”“高官”好当,“乡镇干部”难做,这几乎是中国历朝历代的规律。在这背景下,“书记”练就了一身欺上瞒下、浑水摸鱼的本领。当上访专业户王后生捏着一条单头蛇将“书记”堵在办公室时,“书记”轻蔑地一笑:“哦,单头蛇,单头蛇毒不大性欲大,你没有在手帕上让猫尿了,让蛇爬上去排精液,那样手帕在女的口鼻前晃晃,女的就迷惑了会跟你走?”一席话将王后生说得懵在那里,抖抖索索地说:“书记你还懂得这些?”“书记”喝道:“泥里水里过来的人,我啥事没经过?!”刚一交锋就将王后生的气焰压下去了。不过,事情并没有结束,“书记”也没有派人去通知派出所,而是支开了带灯,将王后生留在办公室单独密谈了一会儿,后来,王后生是笑眯眯地离开了镇政府大院。到小说后来“大矿区又运回了尸体”一节中,读者才会发现“书记”与王后生的密谈内容与高超“手腕”,那就是镇政府每月给王后生四百元钱,让他在山上看林防火,试图将他控制住。而对于上级,“书记”则又是另外一番手段。他虽在樱镇工作,然而每个下午便回县城,整晚都有应酬,为自己升迁谋门路。当樱镇因为常年水利失修、洪水泛滥出现十二人死亡的特大灾情时,镇长吓得抱头痛哭,“书记”则临危不惧,将失踪的、雷击的、触电的,一一排除,最后只落实下女同志马八锅和她孙女是在这场洪水中“牺牲”的。“她肯定是让大家都避水防洪,累得头晕脑胀的,在新房里没留神屋的土塄变化而牺牲的……”以“烈士”申报材料,争取在全县树个典型。如此一番处理,果然使他又一次成功脱险。
视角的变换,必然会带来观察结果的差异。
一九八七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发表,被评论界认为是他“商州系列”的集大成之作,引起广泛反响,并获得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伴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全国知识界兴起的文化寻根热潮,小说通过州河两岸古老的人际关系的描述,在新一代青年金狗与田、巩两家大姓的斗争中,对以权力、家族为中心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从而使人们对当时农村的社会心理与情绪有了充分的了解,作品也具有了深广的文化批判精神和文化历史内涵。与《浮躁》中的“文化视角”不同,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时间演变与角色转换之后,贾平凹在《带灯》中将思考的目光放到了我国现行管理体系和官员腐败上来。他的感觉是:“……我通过写《带灯》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农村,尤其深入了乡镇政府,知道了那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者的精神状态。我的心情不好。”他的“心情不好”,主要在于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比之于“文化”,他现在的视角显然要更能找到问题的根源。
在刚到综治办时,带灯感到樱镇是气囊上满到处的窟窿,十个指头都按不住。上访专业户王后生就说:“那是干部屁股底下有屎么,咱穷是穷,脑瓜子不笨么,受谁愚弄啊?”上访户张正民的想法是:“……他们又在饭店里海吃浪喝了。他们不贪污救灾款哪能这么吃喝?咱老百姓吃的啥,拉的啥,屎见风就散了,你去镇政府厕所看看,屎黏得像胶,臭得像狗渮的!”在一段时间的接触后,那些死搅难缠的上访户,竟然让综治办主任带灯萌生了深深的同情之心:
……山里人实在太苦了,甚至那些纠缠不清的令你烦透了的上访者,可当你听着他们哭诉的事情是那些小利小益,为着微不足道而铤而走险,再看看他们粗糙的双手和脚上的草鞋,你的骨髓里都是哀伤和无奈。
而更让人感到吊诡的,也是小说中的神来之笔,是多年来从事上访者管理的综治办主任的带灯,竟然无辜地成了那场械斗事故的替罪羊,被撤消掉主任职务,行政降两级,最后精神错乱。而她在综治办的助手竹子,最后也不得不加入到王后生们的上访行列之中。而作为事故真正罪魁祸首的书记、镇长等人,却一个个逍遥法外,继续鱼肉百姓。当然更不会伤及到县委卢书记、市委黄书记的一根毫毛。
历史的讽刺就在这里。贾平凹正是凭着他多年对官场内幕与腐败现象的观察,凭着他几十年来因身份转变而形成的“俯视眼光”,一针见血地触及了中国农村贫穷、落后、混乱的要害。比之于以前的商州系列作品,《带灯》显然是突破了,也更让人震撼了。
二〇一一年,贾平凹在给散文新著《天气》所写的“序”中,表达了自己艺术风格转变的原因:“年轻时好冲动,又唯美,见什么都想写,又讲究技法,而年龄大了,阅历多了,激情是少了,但所写的都是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真正体悟的东西,它没有了那么多的抒情和优美,它拉拉杂杂,混混沌沌,有话则长,无话则止,看似全无技法,而骨子里还蛮有尽数的。”这种貌似琐碎而实际上“蛮有尽数”的写法,在《秦腔》、《古炉》中已有充分的体现,而这次在《带灯》中则变成更为自觉的追求。在写作时,他正在看欧冠杯足球赛,欣赏着巴塞罗那队表面上显得毫不在意然而突然就踢进网中的技艺。他认为:“这样的消除了传统的阵形和战术的踢法,不就是不倚重故事和情节的写作吗?那繁琐细密的传球倒脚不就是写作中靠细节推进吗?”他宣称:“我得有意地学学两汉品格了,使自己向海风山骨靠近。”
因而在小说中,贾平凹始终保持着足够的耐心,始终避免直接跳出来发表议论。当在作品结尾时,看到以前何等意气风发、为上访户打抱不平的带灯患上夜游症,半夜在空旷的大街与疯子相遇,像片树叶,在巷子的墙上贴来贴去时,作者的痛恨与愤懑已跃然纸上。而当马副镇长用这样的话劝慰带灯时,我们甚至为作者稍稍地捏上了一把汗。“带灯说:又要刮大风?马副镇长说:这天不是个正常的天了,带灯,这天不是天了!”我感到,面对如此触目惊心的描写,当石华鹏先生认为《带灯》是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时,显然是没有真正读懂小说的含意。
而如此沉郁、悲凉的意蕴,同样也显然不是如唐小林先生所认为的文字游戏。小说不仅区别于《秦腔》、《古炉》,而且也区别于更早前的《浮躁》等商州系列作品。它拥有了新的观察农村生活的视野,也凝聚了作者多年来对农村问题的新思考。甚至,他有时已几乎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
在写作《带灯》时,贾平凹常常感到有一个声音在提醒自己、鞭策自己:“写了几十年了,你也年纪大了,如果还要写,你就要为了你,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去突破和提升。”
在细细研读以后,我们觉得《带灯》,无论是在贾平凹的创作历程中,还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确实都是一次突破,一次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