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信《释门自镜录》茶事辨
2013-11-04丁以寿
■ 丁以寿
怀信《释门自镜录》茶事由来
姚国坤等《中国茶文化》载:“东晋名僧怀信,在《释门自镜录》中说:‘跣足清淡,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食可择甘旨,使唤童仆,要水要茶。’”
王玲《中国茶文化》载:“佛人饮茶的最早记载正是晋朝,见于东晋怀信和尚的《释门自镜录》,文曰:‘跣足清淡,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食可择甘旨,呼童唤仆,要水要茶’。可见当时的和尚戒律不严,可以和文人道士一般谐谑,‘要茶要水’也不过助清谈之兴,与清谈家没多大区别。”
丁以寿等在《中华茶文化的酝酿》一文中也曾说:“晋僧怀信《释门自镜录》:‘跣足清淡,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食可择甘旨,使唤童仆,要水要荼。’魏晋之际,析玄辩理,清谈风甚。佛教初传,依附玄学。佛徒追慕玄风,煮茶品茗,以助玄谈。”考虑到晋时“茶”字还未发明,于是改“茶”为“荼”。并且此文后来发布在互联网上,被互联网广为传播。
当代多种茶书和许多论文在论及茶与禅及佛教的最初渊源关系时,均引用怀信《释门自镜录》“要水要茶”此段文字。但是姚国坤等也好,王玲也好,丁以寿等也好,所引怀信茶事文字,应是本于陈椽《茶业通史》。原文是这样的:“东晋名僧怀信夸言他一生幸福、长寿,都是佛的庇佑,离不开茶水。他在《释门自镜录》序文最后说:‘跣足清淡,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食可择甘旨,使唤童仆,要水要茶。’”

陈椽《茶业通史》所引《释门自镜录》“要水要茶”这段文字则是来源于范文澜《唐代佛教》:“僧人怀信著《释门自镜录》,序文说:‘我九岁出家,现在已过六十岁了。我能够住大房子,逍遥自在,衣服被褥,都轻软安适,生活闲逸。天还没有大亮,精撰已经陈列在前,到了午时,多种食品摆满桌上。不知耕获的劳苦,不管烹调的烦难,身体长到六尺,寿命可望百年。谁给我这样的福气呢?当然是靠我释迦佛的愿力呵!我估计过去五十年中饮食用米至少有三百石,冬夏衣服,疾病用药,至少费二十余万钱,至于高门深屋,碧阶丹楹,车马仆隶供使用,机案床褥都精美,所费更算不清。此外,由于思想和邪见,胡乱花用,所费更是难算。这些钱财,都是别人所生产,却让我享用,同那些辛勤劳动的人,岂可用相同的标准比较苦乐。可见大慈(佛)的教太好了,大悲(菩萨)的力太深了。何况佛以我为子而庇护之,鬼神以我为师而尊奉之,帝王虽贵,不敢以臣礼要求我,即此可知僧人的高贵。父母虽尊,不敢以子礼要求我,即此可知僧人的尊崇。再看四海之内,谁家不是我的仓库,何人不是我的子弟,只要我提钵入室,人家收藏着的膳食立即摆出请用,携杖登路,人家松懈的态度立即变得肃然起敬。古人有一饭之恩必报的说法,何况我们僧人,从头到脚都是靠如来的养活,从生到死都是靠如来的保护。假如我们不遇佛法,不遇出家,还不是要早晚犯霜露,晨昏勤耕种,衣不盖形,食不充口,受种种逼迫,供别人奴役。那有资格扬眉大殿之上,曳杖闲庭之中,跣足清谈,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食可择甘旨,使唤童仆,要水要茶。’”此段文字又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和《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二册。
从中国茶史来看,有关晋代茶事资料屈指可数,怀信《释门自镜录》中“要水要茶”理应是一条重要茶史文献资料。但是,《释门自镜录》究竟是怎样的书?怀信其人事迹如何?为何爱茶?却无人对此进行论述。
怀信其人其书与茶
笔者近日撰写一篇文章,涉及到对茶与佛教的最初渊源关系的考证,于是决心对《释门自镜录》中得茶事问题重新考察一番。由于手头没有纸质文献,于是就从互联网上检索,通过百度在“中华电子佛典协会网”上果然检索到了《释门自镜录》全文。反复检读序文和正文,都没有涉茶内容。不仅无茶,怀信也非东晋或晋代人。因为在该书中,收录多条唐代僧人的事迹。显然,作者怀信只能是唐或唐代以后的人。
《释门自镜录》是怀信编纂的一部书,书中摭拾了大量僧人因造恶业而遭致种种报应的故事。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共十录,卷上:业系长远录一、勃逆阐提录二、轻毁教法录三、妒贤嫉化录四、忿恚贪鄙录五、俗学无裨录六、懈慢不勤录七;卷下:害物伤慈录八、饮噉非法录九、悭损僧物录十。十录所收凡七十三条(雅诰二章,事迹七十一人,附见十四人)。也就是说,正条叙录的文章有二篇,僧人的业报故事有七十一则,附见的别的僧人的业报故事有十四则。每则事例均立有标题,标题下附注附见者的名字,有的还注有出典。凡属作者第一次编录的,均注云“新录”。十录所记叙的事例,大多是关于僧人品行方面的,如偷盗行窃、侵用僧物、毁坏经卷、折损佛像、谤黩高行、诬陷善人、矜傲嗔恚、贪鄙悭吝、滞酒荒惰、食肉伤生,以及其他犯戒行为等。少数是关于小乘学者或非传统教派(如三阶教)批评大乘经和大乘教义的,以及原是沙门后来转为道士,利用佛教的概念义理编撰道教经典和充实道教教义的。他们受报应或变作畜生、毒蛇、蜘蛛之属,或下到地狱遭受地狱无量苦楚。因都系僧人所受报应事,以供佛教僧众镜戒,故称《释门自镜录》,又名《僧镜录》。
在“蓝谷沙门怀信述”,也即序文里,怀信自述“余九岁出家,于今过六十矣。至于逍遥广厦,顾步芳阴,体安轻软,身居闲逸。星光未旦,十利之精馔已陈。日彩方中,三德之珍羞总萃。不知耕获之顿弊,不识鼎饪之劬劳。长六尺之躯,全百年之命者,是谁所致乎,则我本师之愿力也。余且约计五十之年,朝中饮食,盖费三百余硕矣。寒暑衣药,盖费二十余万矣。尔其高门邃宇,碧砌丹楹,轩乘仆竖之流,机案床褥之类,所费又无涯矣。或复无明暗起,邪见横生,非法弃用,非时饮噉,所费又难量矣。此皆出自他力,资成我用,与夫汲汲之位,岂得同年而较其苦乐哉。是知大慈之教至矣,大悲之力深矣。况十号调御以我为子而覆之,八部天龙以我为师而奉之,皇王虽贵,不敢以臣礼畜之,则其贵可知也。尊亲虽重,不敢以子义瞻之,则其尊可知也。若乃悠悠四俗,茫茫九土,谁家非我之仓储,何人非余之子弟。所以提盂入室,缄封之膳遽开。振锡登衢,弛慢之容肃敬。古人以一餐之惠犹能效节,以一言之顾尚或亡躯,况从顶至踵,皆如来之养乎,从生至死皆如来之荫乎。向使不遇佛法,不遇出家,方将晓夕犯霜露,晨昏勤陇亩,驰骤万端,逼迫千计,弊襜尘絮,或不足以盖形。藿茹飨食,或不能以充口,何暇盱衡广殿,策杖闲庭,曳履清谈,披襟闲谑。避寒暑,择甘辛。呵斥童稚,征求捧汲。……”范文澜所译就是此段,仅是怀信整个序文的前半段。所谓“跣足清淡,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食可择甘旨,使唤童仆,要水要茶”就是对“曳履清谈,披襟闲谑。避寒暑,择甘辛。呵斥童稚,征求捧汲”的译文。且不说译文是否准确,将“征求捧汲”译成“要水要茶”也是想当然。佛门饮茶固然在当时是惯常,但是“捧汲”未必就是仅指汲水烹茶,汲水煮饭、汲水清洁等也不是不可。因此说,将“征求捧汲”译成“要水要茶”是把可能当真实。事实上,从怀信序文原文来看,与茶无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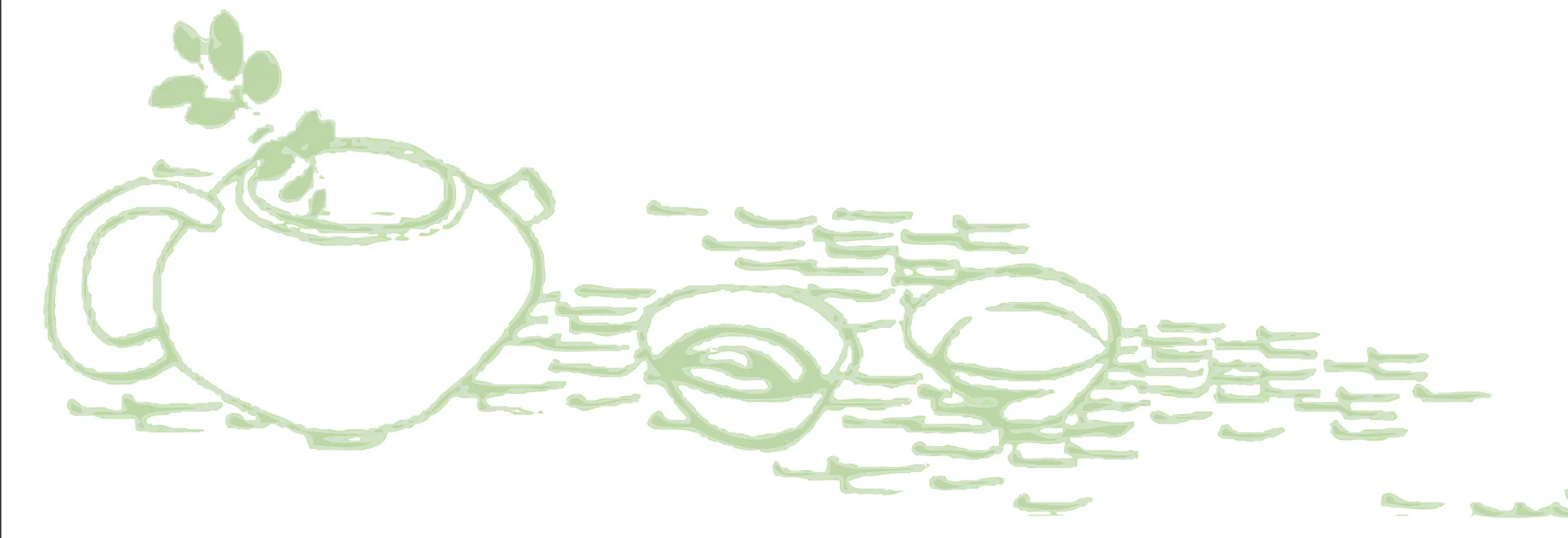
怀信事迹不详,在佛教史上知名度不高。范文澜书中没有涉及怀信生活时代,陈椽则称其为“东晋”人。其实,怀信是扬州西灵塔寺和尚,曾与洛阳白马寺和尚觉救(佛陀多罗,阿富汗人)、武昌大寂院和尚无等、汾州开元寺和尚无业、天台山和尚惟则、惟亮等结伴云游到桂林。一路游览诸山,题名石壁。在游览广西桂林七星岩普陀山栖霞洞时,怀信即兴题诗一首,被刻于岩壁:“石古苔痕厚,岩深日影悠。参禅因久坐,老佛总无愁。”在桂林城西北芦笛岩洞里的石壁和通道两侧,也有怀信等人留下的题名石刻:“无口、怀信、口口、惟口、元春、惟亮,元和十二年九月三日同游记。”另外,在城南的南溪山元岩,怀信一行也在那里留下了题名石刻。元和是唐宪宗李纯年号,元和十二年值公元817年,属于中唐。考虑怀信游览桂林等地时当属青壮年之时,结合其序中所说年过六十,大抵可以判断怀信应是中晚唐时期人。
结论
由上可知,怀信非东晋或晋代僧人,他应是生活在中晚唐时期的一位僧人。怀信《释门自镜录》序文并没有直接涉及茶的文字内容,可以说与茶无涉。即便承认“征求捧汲”就是“要水要茶”,这段晚出的材料也无多少文献价值。因为中晚唐时期,中国饮茶习俗普及化,社会各个阶层靡不饮茶,佛门茶事文献比比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