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票
2013-10-27欧阳娟
□欧阳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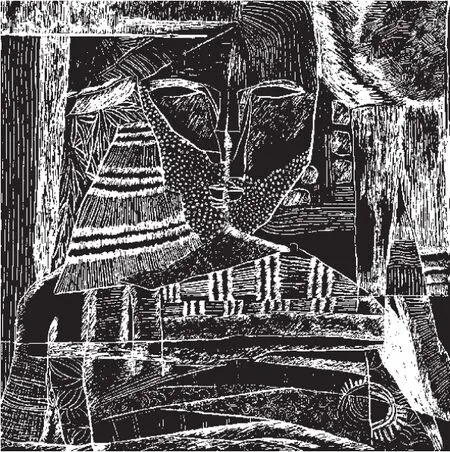
一
菊芹的笑容和她的名字一样,正午艳阳下野菊明晃晃的黄,清晨露珠里香芹亮闪闪的绿,两种颜色揉杂在一起,又清新又耀眼。
小时候妈妈带她去祠堂里拜汤公,她跟小伙伴们蹲在门口过家家。
花花说:“我以后结婚,要买洗衣机,电冰箱,彩电……”
锦锦说:“我要买席梦思……”
轮到菊芹,她就那么咧嘴一笑,黄的绿的颜色撒了一脸:“我要去北京。”
“去北京?北京那么远,怎么去?”
“我有票。”菊芹空着手往花花掌心一拍,“给!”
“什么?”
“车票啊!”
举头三尺有神明。菊芹妈说:“不能说谎。”
说了谎会怎样?
说了谎……说了谎……菊芹妈撩开半垂的帷幕往上一指……说了谎汤公就会惩罚你。
“汤公!你怕不怕?”菊芹妈竭力做出狰狞的表情。
怕。菊芹懂事地点点头。
那个汤公是个披红挂绿的大塑像,端端正正摆在祠堂正中央,跟六、七岁的菊芹比起来,它巨大的体积确实有些骇人。不过大东西菊芹也见得多,家里的老水牛那么大,菊芹还不是每天骑着它?
如果不怕大人打,花花、锦锦和她菊芹,包括村里的大多数小朋友,都巴不得骑到汤公脖子上去“打马马”。
只有大人才怕汤公。
菊芹有一次就听她爸爸说过:“那个汤公的眼睛,雕得真像!你站在哪个地方都好像他在瞪着你,走哪儿跟哪儿,吓死人!”
菊芹觉得汤公的眼睛没爸爸可怕。爸爸的眼睛跟过来,棍子也能跟过来的。汤公光看着你干瞪眼儿,他又动不了,眼睛也发不出飞镖。
大人们怕汤公,却用汤公来吓唬小孩子。小孩子怕挨大人的打,也跟着说害怕汤公。这样说起来,好像整个浅庄的人都怕汤公的。
可是汤公是谁?菊芹小时候问过很多人,没有谁告诉过她。
“汤公就是汤公!这有什么好问的?这丫头是不是有点傻?”这是菊芹妈的回答。
二
搞不清汤公是谁,菊芹也照样一天天长大。搞不清很多事情,菊芹的个儿照样卯足了劲糊里糊涂往上蹿。蹿到小学五年级,比班上的女生们足足高出一个头。
学习成绩却不见长。
光长了个儿,没长心眼儿。
试卷上老师用红钢笔批着分数——38。她瞅个空偷跑进办公室,拿了老师的钢笔把3字的两个半圆填满。
毕竟做了亏心事,心里有些惴惴的,回家之前先去了祠堂问汤公。
“问汤公”是菊芹从妈妈那里学来的。每逢什么重大决策,妈妈就会带了一条鲫鱼三根香,毕恭毕敬给汤公磕上三个头,征求他的意见。有一回家里没鱼,左邻右舍也没得借,天又冷,不能去河里捞,菊芹妈就用家里一条木头雕刻的鱼代替了,还说:“就是那么个意思,菩萨明白。”
菊芹毕恭毕敬托着一张练习本上撕下的纸,纸上用铅笔画了个中间大两头小的东西,小心翼翼放到神案上,一本正经地说:“就是那么个意思,汤公公你明白。”
汤公大概不是很明白,菊芹闭着眼睛等了半天,没等到什么东西对她说话。她心里疑惑,为什么妈妈每次磕完头一闭眼,不到两分钟就说“明白了,多谢菩萨指点”?
菩萨不指点,难道是嫌供品不像?菊芹把神案上的纸页拿下来,对着祠堂明瓦里透进的光看了看。确实不像。
她咬了咬下唇,坚定地从书包里抽出课堂作业本,挑了中间最挺括的一页,用两个手指头拈着,一点儿一点儿慢慢往下撕,力求不留半点痕迹。菊芹举起撕下的纸页对着汤公晃了晃,意思是说:“用这么好的纸给你画鱼哦!”没有桌子,她就匍匐在地上,找一块比较平整的地方画了起来。阳光透过明瓦照在身上,像舞台剧的追光灯,凸显着她小小的身形,看上去就像一个蜷缩在菩萨脚下即将现出原形的老鼠精。
老鼠精磕了半天头,闭了半天眼,汤公只是一言不发地看着她。她想了一下,从书包里掏出试卷,正面对着汤公放了一阵子,背面对着汤公放了一阵子,然后学着妈妈的样子“嚯”地一下站起来,利索地拍拍裤腿上的灰尘,说:“明白了,多谢菩萨指点。”
长长的书包带一甩,菊芹心满意足趿腿跳着离开“追光灯”,完成了她人生第一次自导自演的独幕剧。
齐整丫头读不出书。这是村里人的看法。菊芹爸是土生土长的浅庄人,自然也就这个见识。当年为了菊芹读书的事情,无缘无故把菊芹妈揍了一顿。那时候一年级报名费十块钱,菊芹爸心疼,舍不得拿出来,反正读了也是白读。同龄的孩子都上学了,菊芹就在家里放了一年牛。村里人倒又议论开了:“这么齐整的妹子不让人上学,真是造孽。”说读不出的是他们,说造孽的也是他们,还让不让人活了?菊芹爸猛灌了两碗水酒,揪着老婆的头发就是一顿痛打,打完后把大团结往桌上一拍:“拿去报名!读不好我窝心脚踹死你!”菊芹妈被打得摸不着头脑,也顾不上摸什么头脑,拿了十块钱摸摸平整,倒是舒心地笑了。
窝心脚子一路追着踹,踹到小学四年级,考试成绩的十位数开始从9字起,以考试的场次为单位倒计时,之后稳定在3字上,再怎么踹也踹不动了。十几年下来,菊芹倒是练就了一身铜皮铁骨,挨打的时候憋着气,头皮一麻就过去了,过不去的话大不了再憋一次气,再麻一两回。她就是不忍心看着妈妈跟着挨打。
画了纸鱼问了汤公之后,菊芹没再挨过打,反正每回都是3字改8,方便快捷,不留痕迹。她学会了织毛衣。这编织活儿一上手,什么“鱼骨头”“扭八字”“柏叶花”……一看就会,还自创了不少新样式。浅庄的娘儿们喜欢拿着花样子来找菊芹,她照着图样儿就能编出花儿,照着花儿能画图样儿,小小年龄无师自通,成了浅庄编织界的总设计师。眼睛干瞪着试卷上的应用题,手指在课桌里翻飞,两节连堂考试下来,用拆下的旧毛线给老师织了件毛背心。
妈妈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不能说谎。
妈妈拿了木头鱼去拜汤公,拜完还把木头鱼带回家,妈妈说,就那么个意思,菩萨明白。
菊芹做不出数学试卷后面一大堆用语文字写出来的题目,菊芹改了老师打出的分数,菊芹用打了一千个结的旧毛线给老师织背心——就那么个意思。
老师看着毛背心很是犯难。要也不是,不要也不是。
菊芹双手托着背心咧着嘴,一脸黄黄绿绿的笑意,在浅庄小学灰秃秃的教室中间,像乌云下的一个忽闪。
只见电光不闻声响的,安静而美丽的忽闪。
三
毛背心穿着有点大,菊芹妈扭捏地转动着腰身:“你老师比我胖。”
“我拆了给你改一改。”
“还是多念点书吧,当心哪天被你爸发现……”
话没说完,后门外哗啦一阵金属撞击的乱响。
那个年代,每一个在乡村生活过的孩子都应该熟悉这种声响,那是春耕秋种时,早晨开工和晚上收工时最悦耳的声音。铃叮叮,出发了。铃叮叮,回家了。与这声响同在的,还有老水牛呵出的青草气,以及父亲带着烟味儿的汗臭。
汗臭扛着犁头和那根铃叮作响的铁链进了屋,伸手往菊芹后脑勺一拍:“考了多少分?卷子拿来看。”
菊芹从书包里抽出试卷,露出写着分数的一角,在父亲眼前晃了一下:“86。”
“嗯。”父亲满意地哼了一声,仿佛喝了一口好酒,“这段时间成绩比较稳定。”
菊芹抬眼看着母亲一笑,笑容照亮了8字左边那两个半圈的阴影。
难得这么早收工,菊芹爸显得很有兴致:“回来一路上看见你同学在说题目,我才知道你们又发卷子了,有一道什么思考题,你做出来了吗?”
“啊?”菊芹一下没明白过来。
“有一道思考题,”菊芹爸皱了皱眉,“你们班长汤家琛都不会做的,你做出来了吗?”
菊芹妈一激灵:“菊芹……菊芹,快跑!”
跑?为什么要跑?
菊芹疑惑地看了母亲一眼。
母亲的眼神有点慌乱,仰着头以一种伺机而动的神态观察着丈夫。家里的土狗也学着母亲的样子仰着头,伺机而动。
菊芹爸狐疑地站起来。
菊芹妈双手往前一推:“跑!”
菊芹和土狗同时好似离弦之箭,呼啦一下冲向前门,跨越门槛时彼此绊了一脚。土狗“缸啷”一声叫。菊芹没有喊。
脚后跟刚刚飞出门槛,菊芹听见母亲闷声倒地的声音。
奔跑的菊芹像一阵龙卷风,左邻右舍的女人们都被她从家里刮出来了。
“做什么做什么?”女人们围拢起来。
“作死!臭丫头作死!”菊芹爸打雷般怒吼。
“准是那丫头改分数的事被她老子爷发现了。”原来大家都知道。
天塌下来了。老子爷哪能容得这份羞辱?
菊芹爸回屋拿了拴犁的铁链:“今天不打死那小婊子我就不是她亲爹!”
“做什么做什么?有这么打孩子的吗?”女人们又围拢起来了。
菊芹爸一意孤行,又揪着老婆的头发打了两下,女人们就不敢再围着他了。
一家三口在浅庄的大屋小巷里追逐着。菊芹像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遇山开山,逢河渡河,钻了东屋钻西屋,过了马路钻胡同。
“快跑快跑!”她们都这样喊。
快跑!快跑!像急速的鼓点,为菊芹舍命的奔逃助兴,她是一个炫技的演员,在浅庄晦暗的舞台上表演飞毛腿。
其实菊芹一直没太弄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跑。妈妈叫她跑,她就跑了;村里的三姑六婶叫她跑,她就跑了;她老子爷手里拿着铁链子叫她“站住,站住”,她就跑了。
跑来跑去,她慢慢搞清楚了,原来不过是为了躲开一顿打而已。
不就是一顿打吗?
用得着这样昏天黑地地跑?
她不怕挨打。不怕痛。
打惯了。痛惯了。再痛也不觉得有多痛。
她也不怕死。
穷人的孩子不怕死。
他们只怕累。
穷人的孩子只怕累。
穷人的孩子在早晨五点下地,晚上七点收工,历经了十四个小时的体力劳动之后,他们怕累;穷人的孩子在八九岁的小肩膀上压上几十斤的干稻草时,他们怕累;穷人的孩子在四十几度的高温天气,身穿厚实的卡叽布脚踩烫人的泥浆水时,他们怕累。
有些劳累是他们小小的身体承受不住的。每回“双抢”时总有几个孩子一边被大人追打,一边哭喊:“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打死我算了。”
花花和锦锦都曾经跟菊芹谋划过自杀的事情。有一回花花偷来了家里的半瓶农药,指着自己溃烂的肩膀说:“我明天不想再挑秧了。”他们躲在菊芹家的柴棚里,把印着骷髅头的瓶子传来传去,狗一样嗅着瓶口里散发出的阴险气味。
菊芹在被一个叫做“老子爷”的人赶着满村子狂跑了半个多小时之后,眼前浮现的就是这个情景。
她累了。
她趿着爆了边的解放鞋踢踢拖拖地走着。
“嘿!你还在荡路啊?不怕你老子爷追上来打死?”走过每户人家门口,他们都嘻笑着这样问。
“打死就打死。”菊芹回。
“看到没?”他们指着菊芹给自家的小孩做品德教育,“乱改老师的分数就是这个下场。”
刚刚还担忧着她的村民,一眨眼间形势大变,每个人都幸灾乐祸起来,巴望着那根链子快些招呼过来,让菊芹给孩子们来一场活体挨鞭子表演。
菊芹似乎窥透了某些秘密,心不甘情不愿地继续跑了起来。
跑了起来,所有的讥笑都变成怜悯。
菊芹反复实验:跑起来,经过的门窗里都传来关切的安慰;停下来,关切都转化成责备。
她并不惧怕那根铁链子。可是她一路坚持跑下去。
奔跑只是一种形式。
一种交待。
她再次听见了叮叮当当的金属撞击声,那伴随着朝露的新鲜和暮霭的酣甜而起落的叮当声。老子爷追了上来,他熟悉的面孔在皎洁的月色下变得陌生,像来自远古的先人。菊芹想不起自己有哪个早晨或夜晚是不用遭受打骂的。每次拳头扬起时,她都会看见父亲陌生的脸。那个痛打她的父亲,她并不认识,因而那些打骂,她也并不记恨。在她明晃晃亮闪闪的心田,每一个早晨都是凝着露珠的,每一个夜晚,都有星光透过窗椽。
长长的铁链像电视里武林高手的神鞭,以气贯长虹之势劈面而来……菊芹感觉自己被举了起来,被一双双手臂从低到高举了起来。那些嘻笑着说她在“荡路”的乡亲们把她举了起来,那些用她做反面教材告诫孩子的乡亲们把她举了起来,那个没穿毛背心的老师把她举了起来……
菊芹被塞进一个巨大的稻草垛。穿过那个草垛就是祠堂。她一头扎进祠堂,躲进汤公宽大的红袍子里。回头看时,才发现自己刚刚扎进来的地方是个大狗洞,而那个夯实的稻草垛,底部早已被孩子们钻出了好几个窟窿。
这个奔逃的夜晚,十二岁未满的夜晚,菊芹似乎摸清了浅庄所有的密道。
四
再次出现在父亲面前时,菊芹俨然一副成人做派。
“我不读书了。”
“不读书干嘛?”
“织毛线。”
“织毛线能当饭吃?”
“能。”菊芹显得比她老子爷更有主意,“织毛线拿去卖。”
“谁要买你的?”
“菜市场有人买。”
所有的出路都已想好了。钻过狗洞的人,四面都是路。
“卖不出饿死你。”
“饿不死。”
草垛子里都能找出现成的窟窿,菜市场里还能饿死人?
“白给你缴了这些年学费。”
“四年半,一共一百八十五,我卖了毛线还给你。”
句句铿锵,字字如铁。老父亲相对无言。
退了学,换了母亲的纸壳子鞋。青涩的身体搭配着稳健的姿态,一个小妇人出现在村民中间。
“我自己不读的,我爸爸给了我好多钱。”
草垛子里找出了窟窿,祠堂墙上摸清了狗洞……父亲的软肋,捏巴了清楚。
那顿铁链的鞭子,抽给村上人看的。
演完了,看过了,主角登场。
并非谢幕。
是真正的开章。
昂头走出村口,沙子路上招手叫车。
“五毛钱一个。”
“我有钱。”
哪里有钱?欠着一百八十几块的债呢。
上了车再说。
司机催着买票。
“我有钱。”
上了路再说。
逼得没办法:“我是浅庄汤贤苟的女儿,今天忘了带钱,明天给你。”
已经将要进城了,这么半大的孩子,把她扔在路上?
一来二去,线路上的司机都熟了。心眼小些的,见她招手就紧踩油门加速离开。心肠软些的,停了车喊她上来,票也不用买了。
“我自己不想读书,我爸爸给了我好多钱。”逢人就这么说。
“是她自己不愿读了,我出了好几百块钱让她到城里去学手艺。”父亲也跟着这么说。
读不进书,跟着城里师傅学手艺。这样的安排无可指责。
要指责也只能在心里指责了。
人家心里的事,菊芹一家管不了。
堵得住人家的嘴就够了,还能堵住人家的心?
菊芹一家抬头挺胸在浅庄做人。
菜市场里从没卖过汤菊芹的毛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钱买毛线,空着两只手,手指戳烂了也织不成衣服。汤菊芹沿街各家布店去问,但凡布店里开着裁缝铺的,她就猫在缝纫机下瞧着。瞧了一天两天,有的把她赶走了,有的,给她端碗白饭吃。
端白饭的那家布店是专做寿衣的。不是拜寿的衣服,是给过身的人缝衣服。菊芹就在寿衣店里待了下来。
小县城的人迷信,一般人家的闺女不愿学这个手艺。菊芹愿意。每天就是一碗白饭的酬劳,菊芹愿意。
两年学徒做下来,菊芹十四岁。
每天搭免费的车来去,挣一顿中饭。
十四岁的少女正是莎士比亚笔下最美的精灵。那寿衣店女裁缝的丈夫,显然有着莎翁同样的兴致。
兴致勃勃的裁缝丈夫沉醉在菊芹闪电般炫目的笑容里:“吃香的喝辣的,我带你去。”
菊芹跟着去。皮薄肉满的馄饨,辣油汪汪的米粉,甚至是软糯甜腻的绿豆饼……菊芹长了见识。
沟通了肠胃,触及到身体。菊芹虽未通人事,也多少有些懂得那有意无意掠过胸脯的手指。她懵懂地笑着,看上去无知无觉,心里知道有什么东西正在越逼越紧。但究竟是什么东西,她并不明白。
来不及弄明白,还欠着老子爷百多块钱呢。央裁缝的丈夫给自己找了份零工,中午吃饭的间隙到一家快餐店挑潲水,每天能挣五块钱。
两个月不到,还清了欠老子爷的债。
有了余钱,菊芹喜笑颜开。
裁缝丈夫享受着她的顺从,春风得意脑门发光,指着商店里一条桃红的裙子说:“做我野老婆吧。我买这个送给你。”
野老婆三个字足以令十四岁的少女胃部泛酸,菊芹强忍着不适,只往那裙子上的绣花看。在男人眼里,似乎这少女完全倾倒在这样一条廉价的裙子里。
就连这样廉价的裙子,他也并未当真打算买了给她呢。三两天后,这裙子穿在了女裁缝略嫌肥大的身体上。
“下次再给你买。”仍是一脸无耻的笑意,伸手搂抱她的腰肢。
不说这一句还好。不说这一句,那涨鼓鼓的脓胞还裹着一层薄薄的皮。话一出口,坏死的皮被捅破了,黄的绿的恶心的东西流了一身。
菊芹觉得那男人满身黄绿恶臭的液体,再不肯靠近。男人就常常借故撒气:“不想干了就给我滚!”女裁缝却有不同建议:“白养了你两三年,好不容易上得手干点粗简活儿了,想走没那么容易!”
菊芹仍是每天勤勤恳恳。偶尔从埋头苦干中直起身来,想起以前裁缝丈夫给的那一点点包藏着脓胞的甜头。那甜头虽然险恶,如今却连这险恶的甜都没有了。她诧异自己居然会对那段时光有所怀念,然而再诧异,她终究也还是怀念的。吃着苦长大的孩子,人生第一次尝到了甜,又哪管得了它是白糖,是甘蔗,还是邻苯甲酰磺酰亚胺?
十五岁生日那天菊芹走得很晚,她跟女裁缝说想把剩下的两套寿被做完。九十年代中期县城的夜晚已经热闹起来,斜对面二楼舞厅里的旋转灯光明明灭灭照了进来,满墙的寿衣寿被像新房的帷幔,她是作古的新娘,独自举行着隔世的婚礼。心里还是紧张的,虽然已经酝酿了大半年。她把那些窸窣作响的假缎面一件一件收进塑料袋里,不过七八件,已经装得鼓鼓囊囊。她用脚踩着,将那些缎子压实一些,又往里面塞了两件。好了。从十四岁开始她就能够独立做完整套活计,按理应该给她支付工钱的,这样算起来,上十件假缎子,并不足以抵销那些工钱。
菊芹提着满满一袋子大红大绿的缎子,像个出门给富家小姐置办衣料的丫鬟,默然地穿过车流不息的街面,穿过栉比鳞次的高楼,穿过露天卡拉OK广场,走向她黑暗的与这个年代隔绝的世界。
十公里路程拦不倒贫穷的少女。凌晨时分菊芹进了浅庄。这时候的村庄是静默的。除了各家狗洞里萤萤的绿光,整个村庄都隐没在黑暗中。菊芹坦然地行进在那些绿光里,没有半点不安。如果是生人,那些绿光立刻就会骚动起来。从第一声犬吠开始,整个村庄将会迅速淹没在一片狗叫声中。但菊芹的到来不会惊动它们。它们最多是跑过来,在她身上嗅一嗅,看看有没有带回什么可吃的食物。
祠堂的狗洞显得有点小了,那是因为菊芹急剧发育的臀部。她有些费力地将脂肪囤积最多的部位从狗洞子里拖进去,坦然地把塑料袋塞进汤公宽大的红袍里。最好的那块缎面铺在汤公面前,菊芹当然不会忘记用最挺括的布料画上一条鱼。画鱼的工具是她裁衣服的画粉。
没有什么不安。
只要汤公不责怪,她没有什么不安。
五
女裁缝带着丈夫跑到家里来闹过,无奈寻不出任何证据。
菊芹爸当着女裁缝的面,劈哩叭啦把女儿痛打了一顿。打她的理由是没锁好门,害店里丢了东西。
左邻右舍偶有议论,菊芹爸又是揪着女儿一顿打,打得没人再敢探听半句。
每次挨打,菊芹总是即时关闭所有的思维。她就那么硬起头皮扛着,不躲,不避,也不流眼泪。那个打他的人并不是父亲,虽然他借用着父亲的身体。那是浅庄汤家所有祖辈的总和,他们有着一式一样的相貌,但他并不是他们。她对那些早已死去的人和僵硬的规矩无多兴趣,因此并不支付感情。
隔几天出门,三姑六婆们倒是围了上来:“菊芹哪,没事儿吧?”
没事儿。她总是那么安静地笑笑。
有了布料,还缺一架缝纫机。有了缝纫机,布料才能变成钱。
堪堪十五岁,就有媒婆来提亲,菊芹爸气得赶了出去。
“十五岁吗?看起来足足有十八。”媒婆们都这样说。
再有人上门,菊芹说,看看也行,反正看一眼又不少什么。
还是年轻人开通。
媒婆带了人来,也不过是十七八岁的男孩子,年龄倒是相当。
都是没读过什么书的,穷人家的孩子,不然这个时代,哪有人家这么急哄哄着找媳妇?越是困难的家庭,越怕年龄大了不好找。
再穷的人家,对于菊芹来说,也是殷实的。
从浅庄到城里的车费已经涨到一块钱了。菊芹每次相亲都要约在城里,她是见过世面的人了。十点左右出门,小县城里转一圈,中午到老街的馄饨店里吃碗包面。只固定在那一家吃,那是全城最好的包面。菊芹是见过世面的。
但凡见过菊芹的男孩,没有一个不满意的。菊芹只想要一架缝纫机。
缝纫机有了,她就点头应下了那个男孩的婚事。
两家把三代以内的亲戚叫到一起吃了饭,这就算订亲。
十五岁,菊芹订下了婚事。
假缎面都做成了寿衣寿被,菊芹拿到菜场去卖,碰到浅庄小学新分配下来的青年男老师。
那男老师骑着一辆崭新的二六型凤凰自行车,远远地一按铃,叮当当响,像菊芹爸春耕秋种时套犁的铁链响。
“汤菊芹!”
“聂老师。”
两个人隔着攘攘人流站着,只是笑。
“汤菊芹,我载你回去。”
菊芹显然有些为难,看着蛇皮袋子上铺满了的寿被:“这个,我怕不吉利。”
“汤菊芹,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这么迷信?”
什么年代了?
旁边卤菜店录音机里传出一个略带沧桑的女声,无限深情地唱着: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 让它牵引你的梦
不知不觉这尘世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
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
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度无眠的日子
……”
菊芹抬眼看着身边来来去去的青年男女,穿着粉蓝的、淡紫的西服,皮带上别着小型录音机,走起路来脚步一踮一踮……她觉得自己像是头一次降临在他们中间。
订亲的男孩骑着一辆二八型载重自行车来接她,那车子突然显得异常丑陋,男孩身上的衣服也显得异常丑陋,虽然那衣服是为了订婚临时新做起来的。
他们都不是这个年代的人。菊芹悲哀地想。
可,什么是年代?这是什么样的年代?菊芹并不清楚。
“听说现在大城市的人都不时兴早婚。”这是刚刚聂老师告诉汤菊芹的。
“我也听说是。”男孩也这样说。
“听说他们三十岁以下都不结婚。”
“是啊,”男孩说,“三十岁,是你的两倍。”
“两倍……”菊芹伸长脖子看了看天。
天上回旋着聂老师亲切的脸。
汤菊芹!这把声音仿佛还在耳边。
订了亲的男孩从来不叫她全名,不光是全名,小名也不叫的,他只叫她“哎”。
爸妈也不叫她全名。村里人全部只叫小名,除非是恶作剧骂人的时候。
称呼全名是不尊重的。这是浅庄人的见识。
聂老师叫她全名。聂老师这样叫的时候,菊芹一点没感觉不尊重,反而是一种新鲜的亲密。
“汤菊芹!”他这样称呼她的时候,带着一种刺激性的欣喜。
她把缝纫机还了回去。
汤菊芹挑着缝纫机经过排水沟时水秀婆婆叫了起来:“哎——快看你们家菊芹。”
菊芹爸正在田里打药,伸着脖子向着这边张了张。
“你们家菊芹那挑的是什么?”水秀婆婆又喊。
在田里打药的人都停了下来,伸着脖子往这边看。
菊芹爸撂下药水瓶冲着排水沟跑过去。汤菊芹也用尽了全力快跑,可汤菊芹不能撂下缝纫机,没跑两步就被老子爷逮了个正着。
“臭丫头你干嘛?”
“我要退婚。”
“退婚?我看你是发了羊癫疯了。赶紧给我回去。”
汤菊芹不回去。
老子爷推她。
汤菊芹不回去。
老子爷搧她。
汤菊芹不回去。
老子爷揪着头发使劲儿拽。
汤菊芹不回去。
老子爷还要打,田里干活的人都围拢来了。
“别打了别打了,菊芹她爸,孩子还小,也不容易。”
菊芹挑着缝纫机,继续沿着排水沟走了。
退婚是要算账的,什么买东西的钱,请客的钱,请媒婆的钱,包括两人见面时坐车的钱,吃包面的钱……统统都得还上。
菊芹爸气得又要打她,菊芹躲了一下。
这是第一次,菊芹只往旁边闪了一下,老子爷就不再近逼。
隔在他们中间的,是一只硬纸壳子叠成的钱夹。
“都有了。”菊芹说,“还帐的钱我都有了。”
菊芹爸狠狠吐了口唾沫:“赔钱货!累死累活挣下两个钱,全部赔掉了。”
赔掉了,换来什么呢?
“汤菊芹!”有一天聂老师终于再次碰到了她,“听说你退婚了?”
“退婚了。”她就那么一笑,椭圆形的面孔上艳光一闪,像一张灰黄的宣纸上被人猛然泼上了明黄与嫩绿交杂的颜料。
“退得好。”聂老师说,“小小年纪结什么婚?”
“不结婚。”菊芹还是笑。
聂老师喜欢看电影。她悄悄尾随了去。验票的时候往身后一指:“我有票。在男朋友手里。”
“我有票。”
我有票。
我有票。
她一次次顺利地混了过去。
等待那个蓦然发现她的声音:“汤菊芹,你也喜欢看电影?”
“喜欢看电影。”
“是要多看一点电影。”
“是。”
左邻右舍都说,汤菊芹退了婚是想去缠聂老师。
缠聂老师。缠聂老师。她一次次经过那些讥笑的嘴唇,脸上挂着心满意足的笑意。
直到聂老师和她并肩而行,所有的讥笑戛然而止。
“你们家菊芹有眼光,有志气。”
有志气的汤菊芹得不到缝纫机,也得不到其他物质方面的东西。
聂老师的恋爱方式不是缝纫机,是一张张电影票,一首首流行曲。聂老师买了双卡录音机,聂老师买了电子琴,聂老师从来不提订婚的事。
汤菊芹还是汤菊芹。
汤菊芹去向聂老师辞行:“我要去服装厂做事。”
“好啊,这是好事,总窝在家里不是个事儿。”聂老师说,“我会到服装厂来看你。”
“不了。”菊芹说,“你不要来看我。”
“为什么?”聂老师说,“为什么不让我去看你?”
“我已经过了恋爱的年龄。”看多了电影听多了流行歌曲的汤菊芹,说起对白来变得很文艺。
“你才十八岁。”
“我已经十八岁……”
应该担负起养家的责任。这是她没有说出口的后半句。
还有没有说出口的很多很多句。
她跟他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当他为了选择哪一款电子琴而烦恼的时候,她正在田间地头挥汗如雨;当他坐在电灯下阅读名人名作时,她的家人因为点不起媒油灯,在漆黑的屋子里摸索前行。
在前往床铺的路上经常被绊倒的人,有什么资格在成人以后继续虚无缥缈的爱情?
她不难过。
在新一轮的嘲笑面前,她不难过。
她们都说汤菊芹被聂老师甩了。
她一点儿也不难过。
六
菊芹每个月定期给家里寄上一千块钱时,浅庄的村民们就原谅了她不太光彩的情史。
“你们家菊芹回来了。”每次回家,总有好事的村民把消息带到田间地头,传到菊芹妈耳朵里。
你们家菊芹回来了。你们家菊芹回来了。
浅庄的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喜欢菊芹。
汤公也没有对她做过任何惩治。
家里的电灯通了,电器也一样样慢慢备齐。
菊芹妈还是那样省俭。
“菊芹回来了,我给她煎个鸡蛋。”煎鸡蛋是菊芹妈对亲人最隆重的招待。
这些年在外面,菊芹也品尝过各种美味了。厂里的负责人喜欢她,带着她一起吃香喝辣。菊芹从不拒绝这种包藏祸心的邀请,穷人的孩子没资格啜饮纯粹的甘甜,她习惯了在铤而走险中收获一些小小的乐趣。但每次回家时,看她老娘宝贝似的在有限的几个鸡蛋里面挑选,菊芹仍然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吃的东西。
七八个鸡蛋颠来倒去地数,菊芹总能从那些反反复复的数字中,听出谁也不能体会到的幸福的滋味。
菊芹的弟弟要结婚。
结婚是喜事。
办喜事总是要花钱的。
按照当地农村的规矩,再差些,至少要给女方十五万礼金,还有这爆了半边墙的老房子需要翻新。
菊芹无声地微笑着,听母亲唉声叹气地诉说。
这是什么年代?菊芹已经知道了。这是二十一世纪,一个全新的时代。
这是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
她的步履蹒跚的家庭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村里的百万富翁已经一抓一大把了,而她的老母亲,还在反复清点着竹笼子里的七八个鸡蛋。用二十世纪挣钱的方式应对二十一世纪的生活,必败无疑。
二十一世纪挣钱的方式是什么呢?
北京。那个幼时的信号再次在菊芹胸间响起。
北京。北京。去北京。
进入到二十一世纪的心脏里去。
两百多块钱的车票是母亲一个月的口粮,菊芹舍不得买。趁着人多混上车去,一路默念,我有票,我有票。检票的时候列车员经过身边,前后左右都问了一遍,居然独独放过她去。
她一路站到保定,补了张保定到北京的坐票。毕竟也算是坐着进了北京城,菊芹很满意。
这一去,除了一张张寄回来的汇款单,两年时间杳无音讯。
菊芹妈只能从逐步递增的汇款金额里猜想,女儿在那个遥远得无从想象的城市,终究应该是越活越好。
什么是好?能吃饱,能穿暖,不残疾。
多少外出打工的孩子,离家时还是好端端完完整整,回来时就少了一个手指,添了两条疤痕。
菊芹比母亲想象得还要好。家里新房完工时,她带回了一个男人。
那男人四十五六岁,鬓角有些难以掩饰的苍老,但心思活络,人也大方,一次性给了家里两万块的红包,算是见面礼。
一个见面礼就拿了两万,那结婚的聘礼呢?
菊芹说,男人不是北京人,只是在北京做生意。男人老家封建,他父母嫌菊芹八字不好,怕影响家里的生意,所以暂时不同意他们结婚。
不同意结婚带到家里来干什么?
带到家里来了,男人就可以安心地支付“聘礼”。
这回一次性给了二十万,菊芹交了十五万给母亲。
接受那二十万之前,菊芹带着男人去祠堂问了一次汤公。
汤公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汤公了,菊芹不太认识。祠堂里新添了好几尊菩萨,菊芹在母亲的指点下,兜兜转转绕了好几圈,才找到一个位置跪了下来。
菊芹也不是那个拿着铅笔画鱼的小姑娘了,她掏出胸口带着热气的红包,小心翼翼放到汤公面前。这红包,是菊芹从北京带回来的保存得最挺括的一个。从当年由课堂作业本上撕下的那一页纸起,菊芹一直是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留给汤公。
祠堂开了大窗,用不着明瓦了。菊芹在这新鲜的环境里重新开始上演了新一轮的独幕剧。
她掰着男人的肩膀,前面照一照,后面照一照,要把那男人的样子照进汤公的眼睛里。
汤公会帮她记住,她汤菊芹曾经从北京那样的大城市带回过一个男人,不管这男人是不是已婚,是不是将近五十岁。
离开浅庄的时候那男人对她说:“你们老家真落后,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汤菊芹回:“你们大城市看起来四面八方都是路,其实没有路。我们穷地方看起来没有路,其实到处都是路。”
他不是她的丈夫。他只是她的一条路而已。
她问过了汤公。汤公对她选择的道路没有异议。尽管这个全新的汤公,菊芹还不是十分熟悉。
她也是他的路。他的父母一直想要个男孙。他在北京找不到这样的路,还是摸到农村来,才有机会了却父母多年心愿。
繁重劳动打磨过的体质,才胆敢应允这样的要求。
七
一年后的秋天,菊芹穿过整个浅庄站在了母亲跟前。
母亲埋头在辣椒地里施着肥。是那种尖细油亮的小米椒,衬着墨绿的叶子,煞是好看。
菊芹叫一声:“妈,我回来了。”
菊芹妈腰杆子一挺,八路军中枪般僵直着身体,眼里白茫茫空无一物,三秒钟后,她慌乱地扯了扯缩水的上衣,踮着脚跑到小水沟边洗了洗泥,用沾着水草的手往后拢一拢蓬乱的白发。
“菊芹回来了。咱们家去。”
菊芹跟着母亲再次穿过浅庄。那些探寻的目光得以确认,是了,应该没错,确实瘪了。
瘪了。
吹过的气球,再怎么排空气体,也回不到原样。
菊芹的身体是被吹饱过了的。
虽然浅庄人都没见过菊芹腹部被膨胀起来的样子,但他们敏锐的目光还是发现了这是一只被排空过的气球。
她走路的姿势一点儿没变,仍然是绷直了大腿,微微颔着下巴,看不出什么异样,但在众目睽睽之下,那异样却又如此明显,每个人都窥透了其中的秘密——在她交替的步履之间,有一种叫做朝气的东西已经无声地流逝。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又那么一目了然地存在。村民们互相交换眼色,彼此对双方的发现心领神会。
浅庄的村民屏气静声,好像他们再呼出一点气流,菊芹又要饱涨起来似的。
饱涨过的菊芹成了浅庄讳莫如深的秘密,人们小心翼翼地避开与之相关的话题,偶尔触及,也只是拖长了音调总结一句:“他们家的事哪个搞得清?”
“他们家”成了菊芹家的代称。
他们家有人跨出大门,整个浅庄为之噤声。他们在热闹的目光和冷清的话语里沉默生存。
三个星期之后,菊芹站在门口石阶上刷牙时,有人撩开嗓门朗声招呼了一句:“汤菊芹。”
浅庄的村民也学会称呼全名了。
“汤菊芹,刷牙呢?”
“汤菊芹,打麻将去。”
汤菊芹转眼又成了浅庄的红人。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喜欢她的好脾气。汤菊芹二十六年的人生里究竟发生过哪些故事?搞不清。来不及搞清。物价一天天上涨,各人奔忙在挣钱花钱的苦辛里。
八
菊芹妈跟菊芹讲过她年轻时候的事。
菊芹妈能够拿出来讲一讲的,可以称之为事的,只有这一件。
她那时候还是十六岁的大姑娘,用爱看电影的菊芹的话来说,那叫情窦初开的年龄。她在情窦初开的年龄经媒婆介绍认识了菊芹爸。菊芹爸年轻的时候哦,那个长相哦,那个标致样儿,那真是百里挑一。菊芹妈矮矮瘦瘦,长得像根咸菜,村里人都叫她叉鱼,就是叉尾鱼(叉尾鱼又叫叉尾鮰,淡水鱼,在分类学上属于硬骨鱼纲,其体形前部较宽肥,后部较细长,属底层鱼类)的简称。
叉尾鱼为了能跟大帅哥在一起,粗活重活抢着干,操犁打耙样样来,挨打挨骂无怨言。
“亏得你爸好看,才能生出你这样儿来。”叉尾鱼咧嘴笑了开来。
这一笑,是浅庄过去二十六年来,所有春天的花开。
她赢了。
不光得了个大帅哥,还白捡了个漂亮闺女。
她也赢了。她织过了毛衣,做过了缝纫,还去过了小时候向往的北京,爱过一个衣裳上飘荡淡淡香皂气味的青年男教师。
她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也就不去在乎,在获取这一切的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艰辛。
她们总是笑着。
她们不笑的时候……
不笑的时候,菊芹长相也算平凡。黄黄的脸,眼睛不大,鼻子有些塌,略微突出的嘴括,低垂着的穷人家的女儿特有的倔强的嘴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