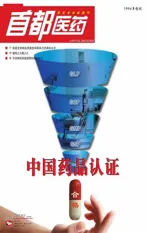开启鲜药实验室研究的新时代
——记鲜药实验室研究第一人郝近大教授
2013-10-19陈广晶
□本刊记者 陈广晶

▲2010年,郝近大教授(左)与国药大师金世元合影
曾经以无线电为最大爱好的郝近大,为什么会走上鲜药研究前沿?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郝近大教授讲述了他与中草药结缘的经历。
多彩童年 儿时偏爱无线电
1951年,郝近大出生在北京的铁厂胡同。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母亲因为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和二尖瓣膜狭窄一直在家休养,全家只靠父亲帮人开车维持生计。一家人住在大杂院里,生活虽然清贫但也苦中有乐。
郝近大童年印象最深的就是经常搬家。母亲由于身体不好,人又比较迷信,身体一不舒服就认为
鲜药曾经在中医药界倍受青睐,过去许多药铺的后院都有专门种植鲜药植物的园地。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鲜药变得可有可无起来,甚至被当成是“中医药故弄玄虚”的“铁证”。曾经也有一些学者想为鲜药正名,但他们大都通过临床观察对比或理论研究去说明。1986年,郝近大教授在《中药材》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鲜药的论文《常用鲜药品种及其功效》,从此鲜药研究进入了实验室研究的新纪元,郝近大也因第一个以实验数据为鲜药正名而为业内所熟知。是风水出了问题。郝近大只在铁厂胡同生活一年多,家里便开始频繁搬家,前后搬了三四次,直到他上小学二年级才终于在珠市口东大街过街楼附近定居下来。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参加了学校的无线电兴趣组。
当时学校有很多课外兴趣小组,跳舞、唱歌的都有,而郝近大最感兴趣的却是无线电。在老师的辅导下,他很快做出了简易收音机:“从煤堆里找一块亮闪闪的自然铜,用小铁片固定住做为一极,另一极用一段小铁丝……就可以听到广播了!” 时隔数十年,郝近大再次提起这段往事依然兴趣盎然,仿佛当年那个酷爱无线电的孩子现在仍未长大。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郝近大已经做成了人生中第一个正儿八经的收音机,可以清晰地接收广播信号的收音机。零件是郝近大一点点攒出来的,攒了好几年。

▲当年在草原牧区下乡生活照
当时家里生活条件不好,虽然当司机的父亲收入较高,但要养活一家五口只能勤俭度日。房间里的电灯只有25瓦,如果哥哥姐姐都写完了作业,母亲就连这25瓦的电灯也会关了,只给他开一盏8瓦的小灯。就在这昏暗的灯光下,郝近大掌握了最基础的文化知识。虽然从小学到高中他的成绩都很优秀,但钟爱无线电的郝近大却无法如愿考取无线电专业,时代的疾风暴雨之中,他已很难把握自己的未来。

▲在杭州雷峰塔下与彭司勋院士合影
深受打击 军旅之梦终难圆
1967年,郝近大中学毕业,而“文化大革命”早在一年前已经开始席卷全国,考大学是不可能了,参军是那个时代青年人共同的梦想,郝近大当然也迫切希望参军。
本来,郝近大家里成分很好,各方面表现也不错,似乎一切都没有问题,但现实却第一次给了他重大打击:新中国成立前,郝近大的父亲曾经在旧政权的交通队开过车,虽然时间不长,却是穿过警服。
尽管没有做过坏事,但这种经历已经足以让郝近大的参军梦想泡汤,甚至连他叔叔家的孩子也受到牵连。郝近大回忆说:“那一年,我连续两三次报名参军,都因为这个理由遭到拒绝,后来只能上山下乡了。”
1968年8月,郝近大来到了内蒙古草原的西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位于锡林郭勒盟东部,是一个既有牧业也有林业的地区。那里山峦起伏、碧草蓝天的美丽风光,淳朴的民风,都深深刻在了郝近大的记忆中,化成了最深情的眷恋。
在他的办公室里很显眼的地方一直摆放着一张大照片,照片里的牛羊静静地吃草,云朵静静地飘荡,远处的小山包渐行渐远,碧绿的草地、辽远蔚蓝的天空……一派宁静安详。郝近大告诉记者,那就是他“上山下乡”的地方。
广阔天地 游牧生活苦乐参半
刚到内蒙古,郝近大和其他知青一起被安排在牧民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郝近大个性随和、乐于助人,他喜欢聊天,爱交朋友,加之有较高的语言天分,很快学会了蒙语和蒙文。在草原上,他在无线电方面的特长发挥了很大作用。当地牧民很喜欢听广播,几乎家家都有收音机,但是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蒙语台自身信号的问题,收音机经常会出现问题,郝近大用他的无线电知识帮助牧民解决问题,他不但能够修好机器,还有“独门秘籍”可以让蒙语台信号更强,声音跟汉语台一样清晰。所有这些都让郝近大在当地人缘颇好,很快就和牧民们打成了一片。
草原的生活很艰苦,但似乎比农区生活要好一些,至少粮食是够吃的。当然那里的危险也是农区的知青无法想象的。
1969年9月,下乡的第二年,知青们开始离开牧民的蒙古包独立生活。郝近大和另外两个知青一起住在一个蒙古包里,负责1000多只羊的放牧。当时最大的难题是吃饭问题,粮食好歹是够吃的,但是怎么把饭煮熟成了大问题。当时煮饭需要烧牛粪,可知青们不会储存牛粪,就只能上山去砍柴。一次,郝近大和一个当地青年各拉一辆牛车去山上砍柴,时值10月初,正是野海棠果实成熟的季节,满山遍野的小果子甜美可口,两个人一路走一路吃,不知不觉离开居住的蒙古包已有五六十里,等到找到可以砍的柴禾,已经到了下午两三点。
两人砍了满满两车柴禾往回走时天色已渐渐转暗,只能壮着胆子摸着黑往回赶路,却不料其中的一辆车翻了。重新装好牛车刚要继续赶路,就听到一阵阵悠长的狼嚎,夜色中十几个绿荧荧的小亮点不断闪烁。他们马上意识到是遇到了草原狼,只得壮着胆子握起斧头扶着车辕继续前行。所幸当时的草原狼还不会主动攻击人,他们才终于顺利地回到蒙古包,其他同伴早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草原的生活艰苦危险,但是“娱乐”生活也很丰富。牧民们很重视老人的生日,特别是家里老人49岁、61岁、73岁生日时都要隆重庆祝,通常会在这一年的夏天办一次“生日那达慕”,摔跤、赛马,载歌载舞……说起自己当年爱唱的歌,郝近大禁不住打起拍子,轻轻哼唱起一首优美动人的草原牧歌。
机缘巧合 随喇嘛学民族医药
郝近大真正开始了解中草药就是在上山下乡这段时间,当地有一个合作医疗站,医疗站的医生是两个喇嘛,郝近大到草原不久就已学会蒙语蒙文,正巧此时医疗站的喇嘛需要助手,郝近大就被推举做医生的助手,这也是他与中草药接触的开始。
郝近大学习蒙医蒙药的学习资料就是一本油印的小册子,还是“6·26”医疗队来时留下的。他跟着喇嘛学习采药和管理药品,还负责医疗站的药品采购。至今郝近大还保留着当年的学习笔记,记录着各种药方、配比、价格等。跟喇嘛去采药是一件辛苦活,每次都是天刚亮就出发。按照牧民的习惯,喇嘛要喝透“早茶”才能走,说是早茶其实相当于早饭,有奶豆腐、砖茶等。所以每次采药都要起得很早,而药材集中的地方距离医疗站有五六十里,他们赶着牛车即便是一大早走,到那里也已经中午了。草原人野外生存能力都很强,随车带着锅灶食物,在地上挖个坑就可以埋灶做饭。晚上把牛车卸下来,喇嘛睡在车里,郝近大和另一个青年就铺上毡子睡在车下,第二天再赶回去。郝近大就这样完成了中药材的启蒙学习,在实践中了解了中草药的基本特性和用途。
蒙药的用法与中药不太一样,喇嘛带着郝近大只是把采回的药材晾干压碎再过筛子,把能用的部分筛出来,比较细的就直接用水冲服,比较粗的就放到茶缸子里用火煮一煮再喝。
郝近大说,以前人们对民族医药有一些误解,觉得蒙古大夫恶治,但其实他们跟中医一样也是号脉开药,也有中药铺里常见的药碾等加工工具。那时候内蒙古缺医少药,蒙药虽不是神药,但是对常见的感冒发烧、风湿、消化系统疾病还是很有效的。特别是对没有用过蒙药的人,药效更加显著。当年郝近大刚到内蒙古的时候有一次感冒发高烧,烧到39℃,喝了当地常用的一个方子“玛瑙西汤”,有四味药,包括菊科的青木香、山南、苦参、还有当地的一味草药,弄碎喝了,当晚烧就退了,喝了3次基本就恢复了。后来他还经常把这个方子推荐给其他知青。
几经辗转 开启中药材研究之旅
人说好事多磨,郝近大“回城”的经历正应了这句话。1973年,郝近大等到了一次上大学的机会。当时他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如果通过考试就能上大学。郝近大是“老三届”,基础知识扎实,90人参加考试,郝近大考了第二名,他报考了清华大学无线电专业,也进入了录取名单。郝近大很高兴,回到旗里就开始打点行装,把用不到的东西都给了身边的人,过冬的皮袄、四五匹马也都分给了同学和牧民,草原好像一下子开满了花,到处都是歌声和欢乐,通知书一到,他就可以出发了。但令郝近大想不到的是,就在考试结束后不久,中国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白卷英雄”张铁生,他在给“上级”反映情况的一封信中建议高考不要只重考分不重政治表现,考试成绩排名靠前的郝近大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因素被别人顶替下来。等到其他人陆续拿到通知书去上大学,郝近大才得知已经没有自己什么事。
幸运的是,第二年,郝近大再次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这一次他很低调地选择了北京农业大学中药材专业。这个专业没有竞争,也与他这些年的学习内容有关,是很好的选择。就这样,他走上了中药材研究之路。
1977年,郝近大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中医研究院(现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后来一次机缘巧合拜到中药大师谢宗万先生门下,跟随谢老做中草药考证工作。

▲1992年与谢宗万先生(左)一起
峰回路转 鲜药研究大有作为
中草药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对中国人有特殊的意义,但是中草药在不断的传承中也在不断地更新演变,不断有新的品种加入进来,也不断有一些品种被淘汰掉,基础的中草药考证工作意义深远。但是一直以来,国家和学术界对此都不太重视,谢老提出的课题申请总是无法通过,研究阻力很大,郝近大几乎无事可做,他希望能够在工作上另辟蹊径,但是苦于找不到方向。
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有位老专家——谢海洲,他与谢宗万先生并称为“二谢”,两个人关系很好,有一次,谢海洲对郝近大说,鲜药可能是个很好的方向。谢海洲讲了很多鲜药的知识,也讲了当时大多数临床医生对鲜药的看法。他说,鲜药历史其实比干药还要久,神农尝百草肯定尝的也是鲜药,后来有了医药行业才渐渐有了干药,因为干药更利于携带和保存,但是以前的中药铺也还是有鲜药的,后院里种一些也就够用了。特别是温病学派出现后,用鲜药更多,他们认为鲜药有降温、润体的作用,可补充温热病造成的人体津液枯损。民国时期曾经还有一次鲜药应用的辉煌时期,施今墨等四大名医都很擅长应用鲜药。
上世纪60年代以后情况变化很大,当时中国人口骤增,门诊量大,鲜药供应不足,而且过去药店都是小本生意,鲜药成本高,过了时限没卖出去就没人用了,逐渐人们就开不出鲜药了。及至对其连续加热后,这种成分就消失了,此外,鱼腥草里的癸酰乙醛也叫鱼腥草素也是这样,鲜品鱼腥草有一种类似鱼的腥味儿,干燥后腥味消失,就是因为癸酰乙醛对热敏感,易挥发。1986年,郝近大的《常用鲜药品种及其功效》、《中医临床鲜药应用流源初探》陆续在《中药材》杂志上发表,开创了对鲜药的实验研究。文革后期,临床医生理论观点受西医影响更深,认为鲜药与干药没有大的区别,只是水分的差别。鲜药甚至成了中医药“故弄玄虚”的证据。谢老说,一个是供应的问题, 一个是思想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导致临床鲜药应用萎缩。其中,思想的问题是最主要的,鲜药与干药的差别究竟是不是水分?这个需要做很多工作。
郝近大成了谢海洲家里的常客,在谢老的书房里,郝近大初步定下了鲜药研究的方向。思想的问题必须先解决,那就从基础工作做起。回到研究所,郝近大开始着手鲜药的实验室研究,他的设想并未得到更多支持,同事们都不建议他做这项研究。但是实验结果给了他最大的支持。郝近大对生姜、干姜,鲜地黄、干地黄,鲜石斛、干石斛等做实验对比,用实验数据说话。事实证明药材的鲜品与干品差异很大,决不仅仅是水分差异,各成分含量都有所不同,有些甚至连成分谱都不相同,有的成分干品里有,鲜品里没有;有的成分鲜品里有,干品里没有。郝近大说,中药材由鲜到干的过程中,无论是日晒还是烘烤都要有一个加热的过程,而且时间都不短,甚至要经历十几二十天时间,药材的化学成分就会发生变化,有些物质如维生素对热很敏感,70℃以上就会分解或氧化。在对葛根的研究中就发现,葛根鲜品中有一种成分叫黄酮,

▲2012年赴日本参加学术活动与日本同道互赠学术著作
在郝近大进行实验室鲜干对比研究之前,人们对鲜药的研究还停留在临床观察或文献研究上,证明鲜药的作用也只能说张仲景的某个方子里用的是鲜品,或者某位名医常用鲜品等,虽然有些古方里既有生姜又有干姜,似乎可以说明鲜干品的作用不同,但还是很难令人信服。实验数据使人真切地看出鲜品与干品区别,思想的问题也就渐渐被解开了。今天人们已逐渐承认了鲜药的作用,郝近大的工作内容也在不断深入。他说,我们研究鲜药并不是说都要用鲜药,我的观点是鲜药有它的特色,也有它的局限性,研究是希望正视鲜药的作用,在临床上该用鲜品的时候用鲜品,该用干品的时候用干品,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
除了鲜药的进一步研究,郝近大也在做中药材品种草本考证,谢宗万主编、郝近大副主编的《实用中药材鉴别》一书在台湾和大陆都颇受欢迎,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此外,郝近大还在2010版《中国药典》的制定中提供了咨询服务。药典出版后他又主编了解释性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辅助说明》的药材及饮片分册和中成药分册,书中详细列出了药典中每种药品的真品和伪品,及其形状差异与鉴别方法。同时郝近大也在做科普宣传的工作,希望更多的普通人了解鲜药、用好鲜药。
人物小传

郝近大,男,汉族,1951年4月生,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中国药学会常务理事兼中国药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学会药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药学会理事兼中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鲜药研究学术委员会副主委兼秘书长等。为国家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劳动人事部联合确定的首批全国名老中医药学专家学术继承人,师承全国著名生药本草学家谢宗万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药材品种及资源调查、鲜品中药保鲜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及药学史等方面的研究。在有关中药材品种的历史沿革、常用药材品种的经验鉴别及鲜品中药的特殊作用机理等方面具有较深的研究造诣。
曾获1987年度卫生部孙氏鼓励医学三等奖、国家中医药局1992年、1993年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工作有奖征文一等奖,其他各级科技进步三等奖3次,曾获2009年度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已发表专著20余部,中医药方面的科学论文100余篇,科普文章300多篇。
目前承担北京市中医局3+3薪火传承项目“谢宗万名家研究室”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