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拍之下港式喜剧的北上症候
2013-10-11谭政张燕
谭 政 张 燕
责任编辑: 霍明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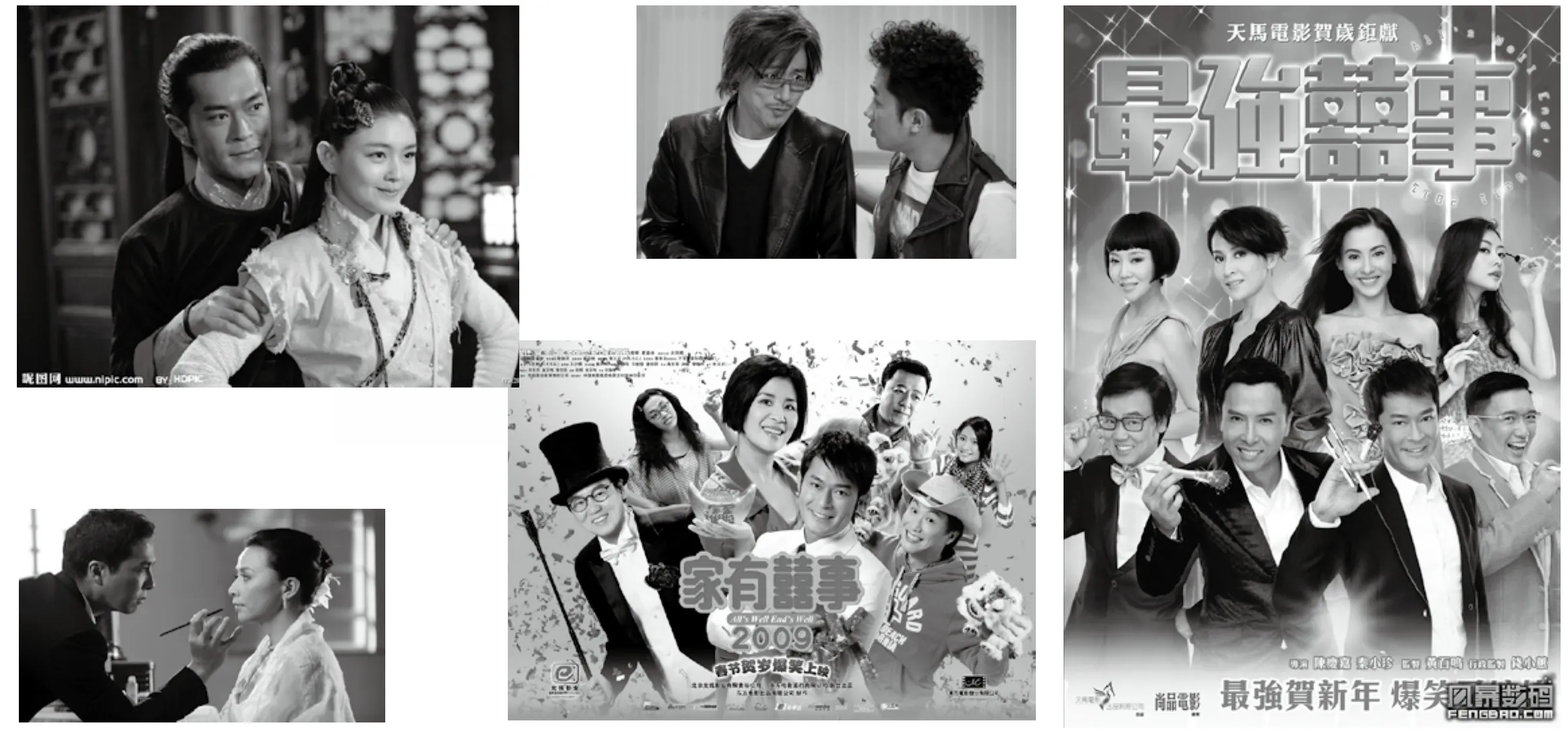
九七回归以来,特别是2004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及《关于加强内地与香港电影业合作、管理的实施细则》正式实施以来,香港电影与内地的合拍热潮火速升温。两地合拍片数量突飞猛进,由1997-2001年间年均低于10部迅速攀升至2004年以来年均30部以上的数量,成为每年度两地电影创作中的重要主流。除了市场影响大、票房高的《功夫》(2004)、《霍元甲》(2006)、《叶问》(2008)、《十月围城》(2009)、《龙门飞甲》(2011)等众多动作片之外,每年生产量几乎占到合拍片数量三分之一的喜剧片创作也不容小觑。尽管诸如《家有喜事2009》、《大内密探灵灵狗》(2009)、《东成西就2011》、《河东狮吼2》等港式合拍喜剧多为中小成本投资,整体品质没有达到大制作动作片的豪华精良,面对内地广阔市场与观众时也常常水土不服,导致很多影片并没能成为合拍潮流中最优秀的作品,但不可否认的是,合拍喜剧片确实是最能融汇香港电影港式形态和北上探索的创作样式,也是最能凸显“香港性”与“内地性”文化碰撞,检视两地合拍片优良得失的重要载体。
一、香港喜剧电影的“香港性”
未进入合拍进程之前,经过传承20世纪上半叶内地喜剧文化精粹和下半叶本土创作的渐进式摸索,香港喜剧电影形成了其浓郁独特的港式特征,包括港人情怀与意识、小人物故事与语言体系、跳跃式喜剧思维等方面。
香港喜剧电影始终呼应着香港社会历时性发展时间轴,关注普通小市民的社会境遇、生活情感,典型呈现特定时期的港人意识与文化身份。20世纪50年代香港社会经济百废待兴,移民潮南下影响到整个香港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主导生态,喜剧电影聚焦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生存困境与情感故事,以朴素写实为风格,推出众多描摹人情世故、家庭伦理的喜剧作品,比如笑中有泪、泪中有笑的朱石麟电影,社会讽刺与黑色幽默的李萍倩电影等。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在香港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变革刺激民众本土意识觉醒、大众文化日渐兴起以及二战后香港成长的青年一代成为主流观众等影响下,香港影坛出现了以许冠文市民喜剧为代表的粤语喜剧片热潮,以荒诞情节、搞笑动作和夸张台词,对底层小市民生活情感进行描摹、调侃和讽刺,充满浓烈的本土现实气息。八十年代“九七回归”问题导致香港社会一定的动荡,温情生活喜剧和无厘头搞笑喜剧应运而生,在银幕上承载起情感抚慰与心理渲泄的社会意识。
香港喜剧电影一以贯之的主角是小人物,而且小人物形象与语言体系都呈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无论五六十年代生存困境与传统温情中的工人、移民、光棍等贫困人群,七十年代处于现实生活弱势却满怀幻想、既可爱又可气的小市民,还是八九十年代以后叛逆社会、鬼怪精灵、刁滑自嘲、唱衰回归的反英雄式升斗小民,香港喜剧电影中的小人物都被裹挟在各个时期特定的香港社会意识和文化潮流中,沉浮于现实生活困境与幻想理想图景中,以底层姿态被调侃、被讽刺地结构于故事中,并以契合于各时期香港底层小市民的流行口语、乡土俚语、时尚俗言等多种语言样式的小人物语言体系,或巧妙幽默家庭情趣与人间真情,或温情调侃社会热点与焦点事件,或辛辣讽刺社会黑暗与意识形态,独具港式文化与智慧。
无论许冠文喜剧、周星驰喜剧等,香港喜剧电影的构思另类大胆,情节结构夸张跳跃,古代现代灵活穿越,复杂时空随意架构,动作、爱情、家庭伦理、惊悚等多种类型元素巧妙杂糅,细节或噱头的密集呈现,这是香港喜剧电影独特的叙事特征。此类神经质的喜剧思维,尽管不乏“过火”、“癫狂”、“恶搞”、“低俗”等贬义评价,但正如专家所言“张狂的娱人作品,其实都包含出色的创意与匠心独运的技艺”,港式喜剧乖张的叙事形式与内在的香港文化内涵是精彩融合的。
二、港式喜剧电影北上后的创作表现
2004年以来在内地电影政策利好的推动下,两地合拍框架之下的港式喜剧片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创作态势,动作喜剧(《功夫》、《宝贝计划》等)、爱情喜剧(《全球热恋》、《月满轩尼诗》等)、家庭喜剧(《家有喜事2009》、《家有喜事2012》)等多种类型影片依次推出,王晶(《大内密探灵灵狗》、《美丽密令》等)、黄百鸣(《花田喜事2010》、《八星报喜2012》等)、刘镇伟(《东成西就2011》、《情癫大圣》等)、马伟豪(《河东狮吼2》等)等影人创作活跃,在两地电影市场具有比较强的竞争力。这类以香港编剧、导演、演员为主导的港式喜剧,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前面已分析的香港喜剧电影的“香港性”,尽可能在情节架构、个性表演、细节营造、语言方式等多方面继续“港味”创作:

2、叙事布局随时转向,现实想象随意切换,时空样态自由转换,叙事策略丰富多变。相对于内地喜剧或幽默写实、或寓言表达的喜剧风格来说,想象力丰富、奇思妙想的故事讲述绝对是港式合拍喜剧最突出的优势。刘镇伟电影《情癫大圣》继续经典作品《大话西游》的癫狂搞怪,不仅大胆突破中国传统文化形象让唐僧谈情说爱,而且还安排了金箍棒任意变换、上天入地,整个故事也随意飞梭于神话传奇、古代想象和现代科技时空中。《2012我爱HK喜上加喜》中,当垂垂暮年的天气预报员和初恋女友共同历险后认识到彼此真爱时,故事时空马上切换至一段戏仿台湾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中校园罚蹲马步、初恋情人相互鼓励的幻想时光,更超乎观众想象的是,突然之间初恋时青春样貌又转换成年老样态,但时空还在那个青涩浪漫的校园,这种既穿越又混杂的现实与幻想,较好地达到了温情幽默与无厘头融汇的喜剧叙事效应。
此类港式喜剧的多样化创作,实际上直接得益于此前香港喜剧电影摸索成功的多种模式:(1)爱情喜剧的追女仔模式,以爱情对象的差异性配对为娱乐宗旨,创造情感浪漫与文化定势之间的陌生感,从而产生喜剧效应。比如《美丽密令》中设置的一男多女或一女多男多角恋爱,以及刻意编排的男警官假扮娘娘腔等性别错位意识的情节等。(2)家庭喜剧的“家有喜事”模式,主要以家庭成员之间的多元矛盾与各异情感,展现亲情与爱情的温馨喜感,比如《家有喜事2009》、《家有喜事2012》、《2012我爱HK喜上加喜》等强调现代都市情感冲突与家庭伦理温情的电影。(3)动作喜剧模式,比如《神奇侠侣》、《功夫》、《追影》、《花花刑警》等,表现手法往往杂糅爱情、伦理、科幻等诸多类型元素,兼有时装、古装两种模式,但核心都是社会解构、现代意识与文化精神。合拍之下的港式喜剧,尽管很大程度上缺少了惊悚鬼怪喜剧、黑帮喜剧、警匪喜剧等类型模式的探索,但在上述主流类型中的发展探索比较突出。
3、语言台词幽默搞笑,特别是夸张饶舌的无厘头语言,将娱乐性巧妙注入小人物日常生活和生命状态,不仅契合形象特质和情境需要,传达较浓郁的都市生活气息,还能巧妙针砭社会时弊、调侃或讽刺热点现象。影片《最强喜事》中,特别借演员刘嘉玲之口说出“叶问也是很久了,不是很多人争着拍吗?你知道黄百鸣要拍,王家卫也要拍,那人家也找梁朝伟拍。拍了多久啦,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拍完”等台词,直接调侃了叶问热与王家卫拍片慢。此外,很多时候,港式喜剧片中的语言轻松智慧,在朴素平实的语言中,浓缩了丰富的生活哲理,也精炼表达了终极意义上的情感价值与社会理念。《全球热恋》中“距离100步,我先走99步,等你走最后一步,哪怕等很久”、“没有刺就不是玫瑰了”等爱情表达,《2012我爱HK喜上加喜》中“假如你知道你的人生还剩几个小时,你会做什么?有机会回去陪你家人、陪你关心的人、陪你最爱的人”等亲情呼吁,在给观众带来娱乐喜感的同时,还展现出心灵层面的正能量传递。
4、注重细节噱头的设置,于情节或场面的细微处构思经营,巧妙对接当前多元化的社会现象、流行文化与热点话题,将调侃、幽默、讽刺等喜剧精神自觉渗透进影片的内在肌理。比如对娱乐圈生活或明星、名人效应进行适度调侃打趣,可以产生事半功倍的喜剧效果:《嫁个100分男人》中三流男星艺名叫“陆超明”,意指陆毅、邓超、黄晓明等男明星们的综合体 。比如对社会拜物与奢侈消费的辛辣讽刺,《花田喜事》中设计了“姑池”、“拍打”等全国限量版包的名称,刻意调侃一系列世界名牌。比如对流行社会现象的敏锐捕捉与巧妙讽刺:《八星报喜》中采用因神曲“忐忑”走红的热点人物龚琳娜出场表演,还有“傅二代”(富二代)、“蓝一浩”(男一号)等名词设计。还有巧妙借力经典电影或卖座影片的片名、桥段,进行创意性情景开发,在轻松调侃中制造喜剧效应,比如《2012我爱HK喜上加喜》中男主角老天气预报员的艺名叫“郭靖”,与《射雕英雄传》里的盖世英雄同名,他的初恋女友名字叫沈佳宜,跟《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中女主角同名,她用的香水叫“倩女幽魂”,还有影片最后“郭靖”作为新闻主播向观众道明真相的直播方式,直接借鉴了许冠文经典喜剧《抢钱夫妻》中的高潮设计。
在众多喜剧片中,2010年《72家租客》是一部值得肯定的影片,它以致敬1973年楚原经典电影《七十二家房客》的方式,将一群小人物有泪有笑、温情活力的故事,以通俗的时代寓言和港式贺岁喜剧样式表达出来,片中喜剧桥段的高密度、快节奏和杂糅特点呈现地道的港味气质,再加上“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故事,这个狮子山下的城市,经过几许春秋风雨,留下了不少传奇故事,故事的精彩不在于情节,最动人的,是当中那份奋斗与互助的精神,岁月无声流逝,山下花灯愈夜愈璀璨,都是面貌随年月变迁,狮子山下的精神与情怀,却依然不变”这段片头字幕所点名的香港精神和怀旧情怀,使这部影片成为合拍之下理念最自觉、港味最纯粹的港式喜剧。
三、港式喜剧电影北上后的问题呈现
合拍之下港式喜剧北上发展,在创作数量、创作形态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可喜态势,但在“量”增长和市场扩展的同时,发展瓶颈却愈发凸显。截止目前,除了周星驰电影《西游·降魔篇》等极少数影片能实现两地市场通吃和高额票房之外,多数港式喜剧均处于市场一边热一边冷、或两边都冷的境地,业界评价、传媒舆论和观众口碑也都每况愈下。
如此困境的出现,核心在于港式喜剧本身艺术品质的停滞不前和提升不足。
1、创作实践呈现明显惰性,创新理念基本缺乏,原创精神大幅丧失,从根本上促发了港式喜剧的退化与停顿。具体的表现有:(1)翻拍、重拍、续拍的影片越来越多,故事题材与内容重复、雷同的越来越多,炒冷饭、啃老本的创作日渐普遍。很多电影人套用香港八九十年代成功的喜剧电影,进行没完没了的价值再利用。比如黄百鸣以90年代票房轰动的 《家有喜事》(1992)、《花田喜事》、《八星报喜》等影片为模板,连续推出《家有喜事2009》、《花田喜事2010》、《最强喜事2011》、《家有喜事2012》、《八星报喜2012》等诸多影片,尽管在市场层面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品牌效应,但是创作层面却基本没有进步,只是故事时空的简单搬移改装。(2)创作同质化趋向越来越凸显,跟风拍摄、题材重复日渐明显,恶搞、解构之风盛行,原创港式喜剧数量很少。比如《东成西就2011》、《越光宝盒》等无厘头喜剧日渐平庸,满足于对《赤壁》、《无极》、《功夫》等诸多影片恶作剧式的搞怪戏谑;《野蛮秘笈》、《我的野蛮女友2》、《河东狮吼》、《河东狮吼2》等夸张爱情喜剧一拍再拍,目前已完全没有吸引力可言,尽管《河2》加入东北二人转和小沈阳等新元素也无济于事。就长远角度和宏观发展而言,港式喜剧的上述表现实际上已近乎于慢性自杀,必然会带来港式喜剧市场与观众的消极畏缩态势。
究其原因,新世纪初面对内地不断拓展的广阔市场,以及内地喜剧娱乐生产力普遍较弱的创作环境,香港喜剧电影人参与合拍展现出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在比较容易赢得票房收益和导演机会的同时,很多创作者主观上麻痹大意,丧失了创作创新的意识,产生了满足于现状、不屑于开拓的惰性,从而使得港式喜剧日渐缺少了进一步发展的生命意识。
2、基于商业模式计算的喜剧桥段形式感日显成就乏味,很多笑点比较低俗,尤其性话题等笑点刻意媚俗,人物设计夸张粗糙、缺乏人性真情, 细节噱头的密集布局缺乏新意与变化。比如古装喜剧片《大内密探灵灵狗》中,叙事编排由始至终堆砌笑料,看似高密度、快节奏、有构思,但绝大多数都只是低劣的模仿借用,笑点极低、低俗平庸,比如开篇一段丰乳性感的宫女梳妆戏“东施效颦”于《满城尽带黄金甲》,太监对付将门后人的客栈戏模仿了经典电影《龙门客栈》,丝毫没有创意新意可言。上述这些勉强穿插进情节主线,反而导致了叙事的断裂与莫名其妙。现代时装喜剧片《嫁给100分男人》中,尽管歪瓜裂枣的负心男人怀揣超级明星梦、剩女善良渴望爱情婚姻等人物设计都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但是花花公子扮演穷司机爱上“灰姑娘”、男职员被要求扮演老板赢得美人归等喜剧情节设计,已是非常俗套且逃避现实的刻意编排,笑点很低。
大体而言,此类港式喜剧太过于沉迷香港喜剧电影俗为主调、堆砌为套路的创作模式,在北上发展中缺乏接地气的主动意识,既没能扎实捕捉内地民众的生活现实、文化心理并加以细腻新颖的喜剧构思,又很大程度上缺失了对香港底层小市民的生活关注与人文情怀,从而很多故事情节、细节噱头的编排设计都浮于表面或远离现实,流于中产阶级或富产阶层的肤浅搞笑,缺乏文化深度和思想力。
3、喜剧明星出现断层,缺乏能够独挑大梁、具有喜剧表演实力的演员。悲剧以情节取胜,喜剧则以表演见长。数十年来香港喜剧电影之所以能声名远播,其重要原因归功于明星主导的创作机制,特别是许冠文、成龙和周星驰三大喜剧明星,他们不仅创立了独特的个人喜剧电影品牌,而且还成功引领了各异的香港喜剧电影时代。但周星驰之后,香港影坛就再没有出现过具有独特气质、能够扛鼎喜剧的喜剧明星,尽管吴君如、古天乐、郑中基、黄百鸣、曾志伟等也有较高的喜剧天分,他们也不断地推出作品,但是他们都不是具有自成一格的喜剧才华和强大市场影响力的划时代喜剧明星,而且他们的喜剧表演很多时候仅有喜剧夸张之“形”而无喜剧幽默之“神”。正如香港影人文隽所说“没有喜剧明星的话,都不会在喜剧片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往往能想到很出彩的喜剧片都是因为片中的喜剧明星”,黄百鸣推出的《最强喜事2011》等系列喜剧电影,尽管聘请了甄子丹、古天乐、张柏芝、闫妮、熊黛林、杜汶泽等众多两地当红明星担纲主演,还特别突破明星固有形象进行特别编排,比如古天乐饰演内在男性气质但举手投足娘娘腔的化妆师、甄子丹饰演执着初恋爱情和化妆功夫了得的营销主管、张柏芝饰演心地善良和情商偏低的傻大妞等,但影片还不算是喜剧佳作,因为缺少了核心标识的喜剧明星和喜剧精神。
4、喜剧语言地域魅力大幅减损,语词语调表达常常搞笑有余而智慧不足,喜剧语言缺少合拍融合的自觉转型意识。香港喜剧电影原以粤语方言的地域色彩和融合乡土俚语、文言、白话、 英文等形态的多元幽默为优势,合拍之下港式喜剧则需要以普通话为主要语言,但创作上却大体延续粤语拍摄模式。“幽默是地域性的,幽默感通常高度依赖于前后的特殊背景,任何人如试图把他们认为非常好笑的笑话用外语讲给别人听,其结果只会是别人礼貌性地回应他,但却表现出很不理解的样子,很难获得共鸣。他们由此认识到幽默是很难被翻译,或者说是不可能被翻译的,不可能跨越不同语言的鸿沟”。港式合拍喜剧中粤语转换后的普通话版本常常很难获得理想的“笑”果,生硬搞笑、不伦不类。
四、港式合拍喜剧电影未来发展的几点建议
可以说,目前港式合拍喜剧的市场生存尚有不小空间,但艺术品质与文化创意却亟待转型提升。当前正值中国内地市场稳健攀升的历史当口,港式合拍喜剧更需要抓住机遇,重塑良好形象。特别在中外合拍日渐拓展之际,港式合拍喜剧应要善于借船出海,在立足内地与香港电影市场之余,放眼海外。目前已成功行销世界多个市场、创造华语电影票房全球第一的《西游·降魔篇》,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思考。
对港式合拍喜剧电影的未来发展,笔者提出几点建议:
1、创作理念与目标观众需清晰定位,合拍中需进一步尊重两地文化差异,找寻既保持个性又最佳融汇的喜剧表达方式。因娱乐传统与文化积累的不同,香港观众和内地观众的喜剧观影口味差异性很大,因此创作者如一味追求商业利润、期望以旧有粤语创作和国语转化的模式继续走入两地市场,这是不易达到的。创作者必须清楚选择或考量影片的市场定位,如果主要针对香港观众,则可以更纯粹地追求地道“港味”、通俗甚至低俗。如果主要针对内地观众,那么则需要创作者深度理解两地文化,合拍过程中要进一步尊重两地文化差异,并以此文化差异自觉调整创作理念和巧妙构思喜剧故事,构设喜剧情境与人物,找寻到最佳磨合融汇的喜剧表达方式,尽可能在银幕上创造出一种兼容并蓄、且具有独特生命力的喜剧电影文化。目前,杜琪峰和彭浩翔是香港影坛创作相对自觉的导演,杜琪峰以爱情喜剧《单身男女》、《高海拔之恋2》等主动契合内地文化,彭浩翔以小清新影片《春娇与志明》展现内地风情的爱情,而以大胆低俗的《低俗喜剧》等影片主攻香港市场。
两地文化差异综合体现在社会意识、人文历史、传统精神、流行时尚、风俗人情等多方面,而且这些文化差异在不同时代语境中更有着多元变化,对于创作者来说这既是独特创意与合拍创作的丰富资源库,也是凸显个性和融汇发展的重要难题。基于相互尊重的平等意识与尽可能“接地气”才能获得最大成功的创作经验,港式合拍喜剧中应该协调搭配两地人物形象,特别在要展现特定人物的地域文化优越性时要特别小心,以免对不同地域的观众造成不必要的情感伤害。很多港式喜剧既要求内地市场,又在创作上刻意贬低揶揄内地人形象的做法,在当前市场推行时其实是不明智的。
2、创作实践应尽可能建立双方、“双城”的主导思想,建立两地合作的和谐机制,寻找两地融合的喜剧故事,同时自觉提升和凸显喜剧语言的两地特色与智慧表达。目前,尽管诸多港式合拍喜剧已经实现了两地制片机构共同投资、风险共担、资源整合等方面的平等互利,但创作上仍基本处于香港导演、编剧、主演占据主导的不平衡状态。未来港式合拍喜剧应该尽可能改变香港影人与香港思维主导的创作机制,影响并引导越来越多的内地影人加入港式喜剧的商业创作,从而在创作思维与创作格局上逐渐实现真正的平等合作。在此前提下,港式喜剧可以进一步拓展题材内容的潜在空间,鼓励内地、香港发挥优长、取长补短,扩展喜剧创作的原创性与表现力,并自觉强化喜剧语言的地域魅力与幽默智慧,促使喜剧电影生产更丰富多样。

3、提升故事创意和创作品质为关键,加强喜剧表演人才培养是重点。口碑渐差与市场渐失的港式合拍喜剧,当务之急是大力提升影片的创意创新和艺术品质,坚决摈弃粗制滥造、重量不重质、僵化模式生产,力求娱乐品质与人文内涵相融合,切实尊重观众的审美需求和观影智慧。同时正如香港喜剧电影数十年发展实践所证明的“没有喜剧明星就没有划时代喜剧”,港式合拍喜剧也要尽快大力加强喜剧表演人才的培养,这是关系到喜剧电影未来发展的核心命题。
注释:
[1] (美)大卫·波德维尔,《娱乐的艺术:香港电影的秘密》,何慧玲译,海南出版社,2003,第14页。
[2] 文隽、列孚,《没有喜剧明星就没有划时代的喜剧》,《电影》,2011年第2期,90页。
[3] 闫广林、徐侗,《幽默理论关键词研究》,学林出版社,2010,第30-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