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凉寂寞话萧红
2013-10-08何健平
■何健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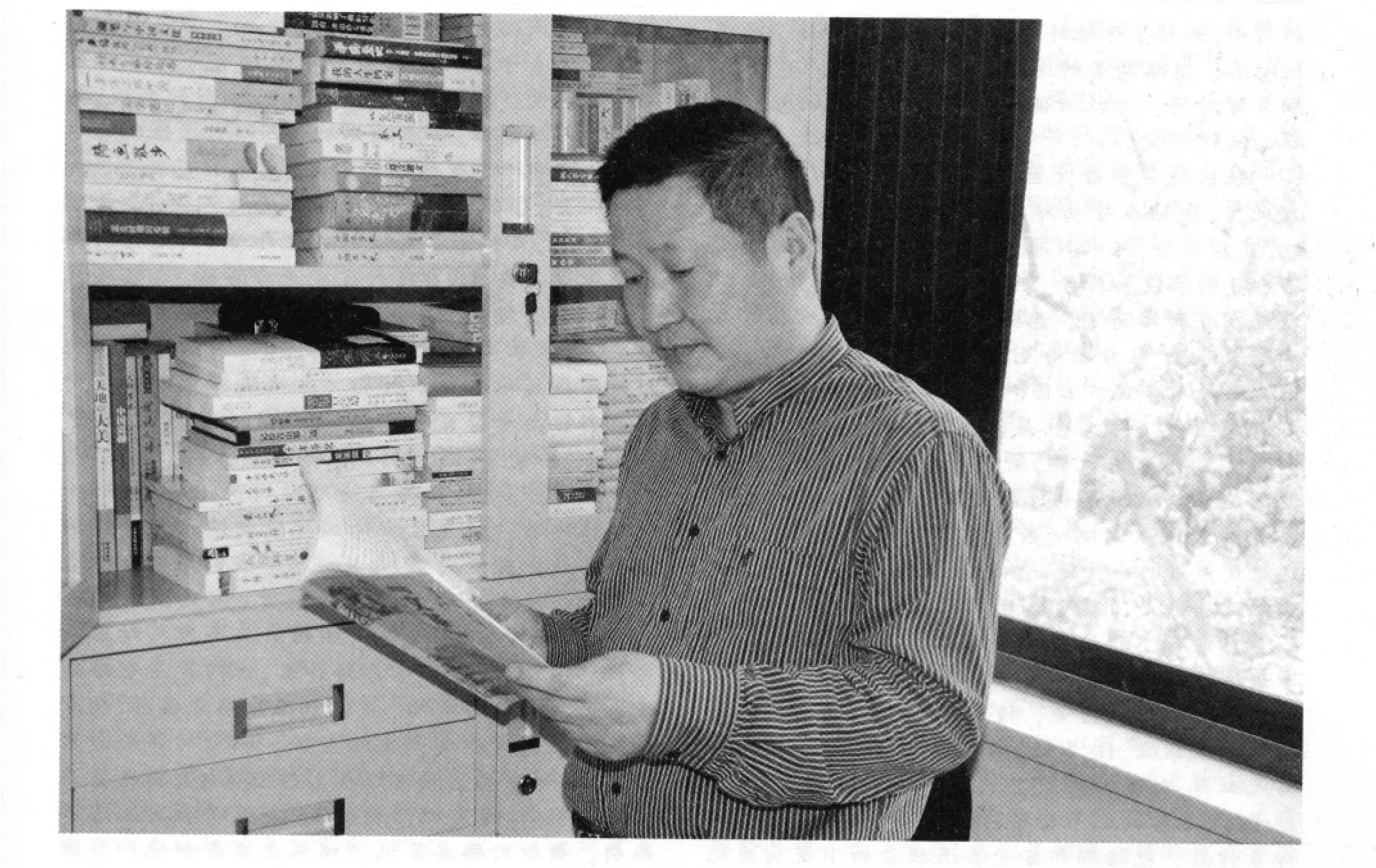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大地则满地裂着口。……严寒把大地冻裂了。”这是萧红《呼兰河传》开篇的句子。就在大地被严寒冻裂的日子里,我来到了萧红的故乡——呼兰。我相信有不少人和我一样,是因为萧红才知道呼兰的。自从10多年前读了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这个小城在我脑海里就似乎再也抹不去了。
最初知道萧红,是因为萧军。而知道萧军,则是因为中学时上语文课,学习鲁迅的杂文《三月的租界》。那时,“文革”虽然已经结束好几年,但是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活动还如火如荼,“狗头军师张(春桥)”1930年代躲在上海租界里攻击鲁迅的罪行被揭发出来广而告之。他化名“狄克”发表的,攻击鲁迅肯定的萧军的小说 《八月的乡村》那篇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作为反面材料,也附录在课文里。从此,我知道了鲁迅当年非常看好,并悉心呵护的一对东北流亡作家,就是萧军(文章里叫田军)和萧红。据说,这两个年轻作家的笔名,就包含着他们对红军的向往。
从哈尔滨市区打车出发,路很好走,尽管到处冰天雪地。70多年前,萧红正是沿着这条路,逃离了她那个冷漠的封建家庭,去投奔和追求她向往的自由,开始了伴她终生的悲凉和寂寞之旅。离市区越远,道路两旁的山河越发白净起来,不过40来分钟时间,呼兰河便像一条冬眠的蛇般蜿蜒在我们的视野里。
眼前就是萧红生前魂牵梦萦的那片土地么?寒风里,我站在呼兰河大桥上,环顾四周:白雪皑皑、荒原茫茫,河水封冻、沉寂无声,这里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浪漫和传奇。可明晃晃的太阳下,历史似乎就在我的对面了,萧红的影像也似乎就在这片荒凉里浮现,我分明看见她满怀着希望走来了。可谁能给她希望呢?王恩甲?萧军?端木蕻良?呼兰河看到的,恐怕更多的是她的挣扎吧。
过了呼兰河大桥,便到呼兰县城了(哦,呼兰现已是哈尔滨的一个行政区了)。萧红故居就坐落在呼兰区城东南隅一条多少有些僻静的街道上。这里是萧红的出生地。和许多文化名人故居一样,萧红故居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景象。院子里半个多月前留下的积雪上没有几个脚印,我且任情享用这难得的清静好了。
萧红本名张乃莹,清王朝被推翻那年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19岁时,正在哈尔滨读中学的萧红与人私奔,结果被开除了族籍。从此浪迹天涯,直到1942年初病逝于日军占据下的香港。她留下的许多作品,包括那部备受鲁迅推崇的小说 《生死场》,描写的都是东北父老乡亲的生活,字里行间常流溢出这位“从异乡又奔向异乡”的女作家对故乡的眷恋。据说,她在病逝前不久还念叨着要回故乡去,想着要写《呼兰河传》第二部……
张家大院占地面积原有7100多平方米,分东西两个院落,东院是张家宅院,西院是张家库房和佃户住所。现在作为萧红纪念馆对外开放的是东院,5间正房带3间东厢房,一溜青砖瓦房,雕花窗棂,典型的东北民居。房前是近800平方米的院子,房后有近2000平方米的花园。屋里屋外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暗自与记忆中萧红在 《呼兰河传》中的描写对照,不知为什么却总也找不到本来应该有的那种朦朦胧胧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尽管讲解员说故居是严格按照萧红在《呼兰河传》中的描写修复的。
萧红的生命是短暂的,但她留下了不朽之作:《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两部小说先后出版时,前者由鲁迅作序,后者由茅盾作序。一个青年作家,两部作品分别由这样两位文坛巨擘写序,不说空前绝后吧,恐怕也是世上罕见的。鲁迅先生对《生死场》的评价是:“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茅盾先生称赞《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然而,能写出这么出类拔萃的小说的萧红,却饱尝了人间的忧患和沧桑。萧红是一个对爱情无限钟情的女子,渴望着生命中能拥有一份值得永远珍藏的爱。然而,每一次爱的经历,对她来说,都几乎是一场灾难,都以遍体鳞伤而告终。她的第一个男人王恩甲,在她身怀六甲、困居旅店的时候,弃她而去,杳如黄鹤。她的第二个男人萧军,是个激进青年,又和她有着同样的文学专长,这样的匹配应该说是良缘了,然而现实是冷酷的,冷酷得让萧红也难以想象。一个很会用笔的男人,也很会用拳头,而这拳头不是用来抗暴,而是用来凌弱。她与萧军在患难中相识相恋,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中磕磕绊绊生活了6年。这对在外人看来“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情侣,终究没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两人决然分手后,萧红带着一颗破碎的心远走香港,直到临终前,她也无法释然那段爱情带给她的阴影和伤痛:“我爱萧军,今天还爱!我们同在患难中挣扎过。他是个非常优秀的作家,可是做他的妻子,却是一件痛苦的事!”她的第三个男人端木蕻良,也是很有才气的东北籍作家,但同样没有给她带来她所期盼的幸福。在萧红生命垂危之际,端木蕻良无疑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他当时并未与萧红离婚,却将病重的萧红托付给骆宾基(骆宾基是萧红去世前44天的陪伴者),甚至对骆宾基不辞而别。萧红对骆宾基说:“端木是准备和他们突围的。他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这对于细腻敏感、擅长刻画人物的萧红来说,该怎样用笔来抵达自己的内心?可想而知,她的心境一定是悲凉的。萧红曾写道:“孤独的内心,孤独并无所凭据……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这种悲凉,在她弥留之际,更是被她感慨到了极致:“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不甘的是什么?是她太背运了,遇到的男人都不能好好待她,还是另有苦衷?此中滋味,除了当事者自己,恐怕“不足为外人道”。
萧红的一生,坎坷、传奇、悲凉、寂寞。因为对家庭的抗争,她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一条漂泊之路,即使被寒冷、饥饿逼迫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她也决不妥协和退缩。逃婚、饥饿、流亡、失业,友情、爱情、情变、难产,忧愤、疾病、哀怨和冷遇……萧红像一叶飘忽不定的浮萍,在人生的苦海里载浮载沉。她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从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从日本回来,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如此一路,由北向南,四处漂泊,她最后停泊在31岁的冬日里。这个冬日,她终于可以得到真正的永恒的自由和安宁了。但她又是多么希望死神不要把她带走,而是帮忙把尘世的重负重新压在她的肩膀上,然后一如既往、无限期待地忍耐着,看人生到底还要她承受些什么。只是这样的萧红,似乎命中注定是悲凉的、寂寞的。许多善良的人们无不为满腹才情的萧红如此悲凉、寂寞的薄命人生而惋惜。
然而,我以为,成败皆萧何,恰恰是这无尽的悲凉和寂寞,成就了文学的萧红。她的文学作品,正是被这悲凉、寂寞所浇灌培育出来的花朵。呼兰河畔这方广袤肥沃的土地,不仅是给了她生命的地方,而且是她创作热情、力量和灵感的源泉,同时,也是她悲剧的渊薮。在她的抒写中,童年时代的呼兰河以及她走出故土后的感情生活,是她汲取灵思妙想的一口深井。前者虽然寂寞,但是却飘荡着一丝丝甜蜜和清香;后者虽有甜蜜,但是却伴随着一次次撕心裂肺般的痛楚和悲凉。天才的萧红,本能、宽博地把这些独特的经历和感受积存起来,然后像动物反刍般在长夜里细细咀嚼、消化,进而升华为审美的甘霖、灵动的文字。
尽管萧红一生漂泊,但故乡永远是她灵魂的栖息之地。她终生都带着眷恋的心情,在笔下絮絮叨叨地叙说着自己对故乡的思念,以及在故乡生活着的父老乡亲。她的命运,她的性格,她的心理和感情,无不烙着故乡的深刻印痕。远离了故土,不停漂泊、不断跋涉的萧红,故乡也依然是一座她美好记忆中有着慈爱的祖父和姹紫嫣红的精神后花园。祖父是她童年生活的情感寄托,而故乡正是存放这个寄托的月光宝盒。所以,她一次次地在自己的笔下回到了那片肥沃的黑土地。特别是到了她创作的后期,由于身体的原因,由于情感生活的不幸,她对自己生活了20年的故乡,更是产生了无以言说的追昔感念。
正是因为饱尝了不幸,所以萧红迫切地需要爱的阳光雨露,可现实却一次次无情地陷她于痛苦的黑暗之中。因此她只能在梦中,在自己营造的文字世界里,用文学的烛光照亮自己返乡的精神旅途。历经离乱和沧桑,她像一只在风暴中折翅受伤的小鸟,需要一片熟悉、安稳的林地来栖息养护自己的羽翼和心灵。而梦里故乡正是这样一片合适的林地。也正是这样,在她的感怀念旧之情浓烈到极致的时候,《呼兰河传》——这朵被寂寞和挚爱所浇灌、培育出来的乱世奇葩,终于喷薄绽放,成为她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
萧红故居庭院花坛中,耸立着一尊萧红汉白玉雕像。雕像中的她,身着古式旗袍,脖子上围着一条围巾,右手支颐,左手拿着一本书,神态安闲地坐在一块石头上,目光安详地眺望着远方,似欲穿越小镇上那些色彩斑驳的老屋,遥望从村边流淌而过的呼兰河。故居讲解员告诉我,少女时代的萧红是非常喜欢呼兰河的,家中最疼爱她的祖父常常带着她到河边去嬉戏放舟。因而,当她拿起笔来抒发情怀的时候,字里行间常常流露出她对呼兰河的深深依恋。成名小说《生死场》里有它的身影,诗性散文体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里,更表现出她对故乡这条大河的一往情深。据有关资料介绍,《呼兰河传》的收尾部分,是萧红在日寇占据下的香港九龙写完的。而当时她的肺病已相当严重,她是在病痛的煎熬中完成这部鸿篇巨制的。如果没有对故乡的深情眷恋,病魔缠身、处境艰难的萧红,怎会有如此坚韧的毅力和强大的能量?之后,她又强忍着哮喘带来的呼吸困难,写出了小说《小城三月》,其中的故事人物,无不与生她养她的这片北国小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她给我们倾诉的是一个爱情悲剧,字里行间时而透露出一股低迷、哀伤的气息,但是,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在这种文字的背后,看出她对家乡的眷念和亲热。特别是小说中描绘的开明的父亲、和蔼的继母,以及和乐融融的家庭氛围,都是她现实缺失,而内心期盼已久的。在身体病弱不堪的时候,萧红曾经对骆宾基说过这样的话:“我早就该和端木分开了,可是那时候我还不想回到家里去,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弃甲的了。因为我的身体倒下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我不是说得很清楚么?我要回到家乡去。”可以想象,在萧红的心目中,自己是已经和父亲和解了的,只是碍于一些莫名的原因,她还没有跨出实质性的一步,但她在期待着那一天。然而,恶化了的疾病终将这个曾经无比坚强的女人磨蚀得一蹶不振,也使她的心理脆弱到了极点。身体衰弱、情绪低落、内心哀怨的萧红,此时多么需要父亲的呵护啊!而自己多年来一直在与他斗争,甚至当年两人在哈尔滨街头相遇时,都没有说一句话。可是,此刻的她,却好想回到父亲的身边……但是,这个冰释前嫌、父子修好的愿望终究没有实现。这个呼兰河的女儿没有来得及回到自己的故乡,便带着满腹的遗憾在香港寂寞地病逝了。一切的期盼只能寄托在文字之中。
萧红故居前面的小路正对着呼兰河,路旁积雪融化的草地里似乎隐约可见几点绿色,河畔还有些稀疏光秃的树木,在冬日的阳光下显现出一种萧瑟寂寞的美。这有点儿像是读《呼兰河传》的感觉,“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茅盾《<呼兰河传>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