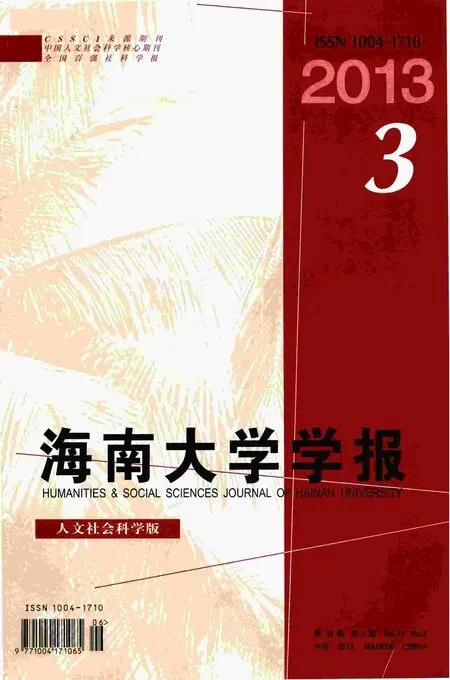论“小东坡”唐庚与苏轼的诗学渊源
2013-08-29唐玲
唐 玲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古籍研究所,上海 200234)
唐庚(1071—1121),字子西,眉州丹棱人,北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进士,曾官利州、阆中、绵州等地,后为宗学博士、提举京畿常平。大观四年(1110)冬,唐庚被贬安置惠州,五年后方遇赦北归。宣和二年(1120),请祠,提举上清太平宫,归蜀,道卒于凤翔,年五十一①注:王称《东都事略》卷一一六:“举进士,稍用为宗子博士。张商英荐其才,除提举京畿常平。商英罢相,庚亦坐贬,安置惠州。会赦,复官提举上清太平宫。归蜀,道病卒,年五十一。庚为文精密,通于世务,作《名治》、《察言》、《闵俗》、《存旧》等篇,学者称之。”《宋史》本传略同。亦可参拙文《唐庚诗集校注》第一章《唐庚生平考述》,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有《眉山唐先生文集》二十卷行世②注:《眉山唐先生文集》今存四大版本系统,分别为宋绍兴饶州刊本(二十卷);《四部丛刊》三编本(三十卷);雍正四年南陔草堂汪亮采活字本(二十四卷);嘉靖三年任佃刻本(按:有诗无文,共七卷)。参见拙文《眉山唐先生文集版本考略》,《新世纪图书馆》2011(4)。本文引文、论述均以宋刊二十卷本为据。。
刘克庄诗云:“一州两迁客,无地顿奇才。方送端明去,还迎博士来。”[1]所谓“两迁客”,即指苏轼与唐庚。两人皆为眉州人,属小同乡;晚年又都因为政治原因获罪,安置惠州。正因为有着极为相似的成长环境和贬谪经历,唐庚更能从内心深处理解苏轼,从而对其人心生敬慕,于其诗心摹手追。具体则表现为对苏诗语词意象的汲取与化用,以及对苏轼诗学思想的倾倒与尊崇。通过对苏诗的潜心学习,加上自身的反复锤炼,唐庚最终得以自成一家,同时也享有了“小东坡”的美誉,屡为后世文人所称颂。
一、唐庚对苏轼的态度——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关于唐庚对苏轼的态度问题,近年来已有学者作文探讨,如吴定球《论唐庚对苏轼的态度和评价》(《惠州学院学报》2002年第4 期)。此文通过对唐庚仕履行止的考述以及相关诗文的评析,说明唐庚一贯尊崇苏轼的文章道德,对其一再被贬深表同情,同时也对徽宗时期焚书毁碑的禁苏政策不满。
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南宋以来皆谓唐庚为善学苏轼者③注:如雁湖居士李壁曰:“唐子西文采风流,人谓为‘小东坡’。”刘望之曰:“唐子西善学东坡,量力从事,虽少,自成一家。其诗工于属对,缘此,遂无古竟,然其品在少游上。”林希夷曰:“唐子西学东坡者也,得其气骨而未尽其变态之妙,闲有直致处,然无一点尘俗,亦佳作也。”(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483页。),而清王士禛、四库馆臣则持异议。王士禛《居易录》云:“庚生三苏之乡,又前后与东坡贬惠州,而集中无一字及之,盖庚起家为张商英所荐,其贬惠州亦以商英连染,视韩子苍异趣,宜其不为眉山之徒欤?”[2]
继王士禛后,四库馆臣也认为唐庚于东坡深有微词,云:
今考庚与苏轼皆眉州人,又先后谪居惠州,宜于乡前辈多所称述,而集中诗文自《闻东坡贬惠州》一首及《送王观复序》“从苏子于湘南”一句外,馀无一字及轼。而诗中深著微词,序中亦颇示不满。又《上蔡司空书》举近代能文之士,但称欧阳修、尹洙、王回,而不及轼,又《读巢元修传》一篇,言苏辙靳惜名器太甚,良以失士心,似庚于轼、辙兄弟颇有所憾,殆负其才气,欲起而角立争雄,非肯步趋苏氏者。[3]
此实馆臣未加深究之言。刘克庄对《闻东坡贬惠州》一诗评价甚高,称“此诗甚佳,状得出”[4]26。而并不认为唐庚对苏轼有丝毫不满。刘氏虽相去苏轼、唐庚年代已远,然对本朝的政治环境与文人心理自比数百年后的清人更为了解。余嘉锡先生在辨误时亦指出:
至于集中诗文称述二苏者实不甚多,此则时势使然,非于轼、辙兄弟有所私憾也。盖徽宗君臣深恨元祐党人,而于轼、辙犹甚。……庚生于斯时,安敢于文字中歌诵苏氏,以自致钩党之祸哉!况庚受知于张商英,且以师礼事之,自称门生,商英固与苏氏为仇者,宜庚之不能不有所顾忌也。庚所上书之蔡司空,乃蔡京也。人非至愚,岂有誉苏轼于蔡京之前以挑其怒者乎?《提要》以此为疑,其亦未之思矣。其《闻东坡贬惠州》诗云:“元气脱形数,运动天地内。东坡未离人,岂比元气大。天地不能容,伸舒輙有碍。低头不能仰,闭口焉敢欬。东坡坦率老,局促应难耐。何当与道俱,逍遥天地外。”味其言,盖伤东坡以言语文字讥切当世,为世所不容,而不欲明言,不得已,乃归之于天焉。此太史公传伯夷之意,亦即李豸《祭东坡文》所谓“道大不容,才高为累”也。其悲之也深矣,何尝著一微词耶?……《读巢元修传》云:“吾闻子由立朝,謇謇有大体,然靳惜名噐太甚,良以是失士心;比其败也,士大夫诋之,又过矣。覌其书巢元修事,可胜叹哉,可胜叹哉!”夫称子由謇謇有大体,是谓其有古大臣之风,誉之者至矣;靳惜名噐,正见其公正无私,非憾词也。士大夫因而诋之,此小人不得志者之所为,庚昌言其过,所以罪熙丰之党,为子由鸣不平也。《提要》顾疑庚有所憾于辙,岂得为知言乎?盖作《提要》者未能论其世以知其人,故不晓庚立言之旨,徒见集中言及苏氏者少,求其说而不得,遂从而为之辞耳。实则庚之称述苏氏者,不止如《提要》所举三篇已也。卷三有诗一首题为《乙未正月丁丑与舍弟棹小舟穷西溪》,其诗有云:“树从坡去无人识,水出山来带药香。”此盖庚在惠州,因泛舟出游,而追怀东坡也。卷九《书大鉴碑阴记》云:“《曹溪大鉴禅师碑》,元和中柳柳州文,绍圣中苏定武书,前长老辨公立石。至崇宁初,此碑坐累毁去,今长老和公更书而刻之。唐子曰,辨老以大鉴之道,柳州之文,定武之书,三法和合以成此碑,使喜书者因字以求文,好文者因词以求道,其意以为更相发明,而不知适足以相累。”绍圣初元,苏轼方知定州,故谓之苏定武。崇宁初,此碑坐累毁去,盖指三年诏毁苏轼碑刻事。庚此文颇赞东坡书法,故不称东坡或子瞻而称定武者,所以避时忌也。庚之小心畏慎如此,其敢时时弄笔形之颂叹也耶!卷二十八《书宋尚书集后》云:“仁庙初号人物全盛时,而尚书与其兄郑公以文擅天下。其后郑公作宰相,而尚书独不至大用。元符二年,予典狱益昌,始得尚书所为文,读之粲然,东坡所谓字字照缣素,讵不信哉!”此皆称述东坡者。《提要》乃谓自《闻东坡贬惠州》及《送王观复序》“从苏子于湘南”一句外馀无一字及轼,何其不检之甚欤![5]
余氏辨误旁征博引、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视为定论。唐庚于苏轼不仅没有微词,相反还十分景仰其人品、文风。而至于诗文中涉及苏轼较少,确实是出于政治原因,不得不加隐晦,怎么可说可谓“集中无一字及之”呢?
其实,唐庚早在初游京师之际,便与苏轼结识。《唐子西文录》云:“东坡赴定武,过京师,馆于城外一园子中。余时年十八,谒之。问余观甚书,余云方读《晋书》卒,问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对。始悟前辈观书用意盖如此。”[6]446
青年时期的唐庚与苏轼有过一面之缘之后,便对其心存敬慕,也为他日后学苏埋下了伏笔。即使到了晚年,唐庚对苏轼的推崇也丝毫未减。《文录》载:“余作《南征赋》(按系赴惠州途中所作),或者称之,然仅与曹大家辈争衡耳。惟东坡《赤壁》二赋,一洗万古,欲彷佛其一语,毕世不可得也。”[6]447从人生态度上来说,唐庚虽未达到苏轼那样“奉儒家而出入佛老”的豁达之境,然贬谪时,其心态也算平和淡定,只偶尔作唧唧蛩吟而已。
政和年间厉行元祐党人之禁,士大夫们鲜敢谈论党禁中人,尤其是旧党的代表人物苏轼。此时唐庚安置惠州,曾多次寻访东坡遗迹。虽碍于禁令,却也在诗文中隐晦地表达了自己对苏轼的景慕。除余嘉锡所举者以外,如《初到惠州》:“卢橘杨梅乃尔甜,肯容迁谪到眉尖。因行采药非无得,取足看山未害廉。辨谤若为家一喙,著书不直字三缣。老师补处吾何敢,政为宗风不敢谦。”[7]卷2其中,“老师补处吾何敢”一句,方回《瀛奎律髓》云:“大观四年,子西谪惠州,乃东坡补处。”[8]1756再次证明了在唐庚心目中,一直将苏轼看作自己的老师。补处,指到过的地方,对于老师到过的地方——惠州,总抱有一份亲切与敬畏之感。
再如《水东感怀》:“往事孤峰在,流年细草频。但知其室迩,谁识所存神。碑坏诗无敌,堂空徳有邻。吾今稍奸黠,终日酒边身。”据苏轼《和陶移居二首并引》:“余去岁三月自水东嘉祐寺迁居合江楼,迨今一年,多病寡欢,颇怀水东之乐也。”[9]2191故知唐庚诗中所言“水东”者,即为苏轼寓惠时居所之一。苏轼《用前韵再和孙志举》云:“我室思无邪,我堂德有邻。”[9]2191祝穆《方舆胜览·惠州》:“白鹤观废,苏子瞻请其地筑室以居。堂曰‘德有邻’,斋曰‘思无邪’。”[10]可知,德有邻堂为苏轼在惠州时所建。多年后唐庚拜谒此地,不禁发出“其室则迩,其人甚远”[11]的感叹,更将苏轼视为“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圣人。[12]卷13《盡心上》综上所述,唐庚对于苏轼可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可见王士禛从党争角度,四库馆臣又从角立争雄角度判断唐庚对苏轼的态度,臧穀亡羊,兩俱失之。郭绍虞先生指出:“学术公器,文章优劣固非私人意气可以上下其间者。则庚在颠沛困踬之余,发为心平气和之论,其所言固当时是非之公也。考强氏与庚晤谈之时,党人之碑已立,庚固不必借东坡以自重,而庚在元祐学术将禁之前,亦不贬东坡以自高,则其为人,犹有可取之处。”[13]其实,何止可取,直是可法。
二、唐庚对苏诗的学习——语词意象,融为己出
周紫芝《竹坡诗话》云:“钱塘强幼安为余言,顷岁调官都下,始识唐博士庚,因论坡诗之妙,子美以来一人而已。”[14]可见在唐庚看来,只有杜甫与苏轼才是真正值得他学习取法的大诗人,他人皆不足道。宋人学杜之风盛行,江西诗派而外,唐庚亦云“作诗当学杜子美”[6]447。通观唐庚诗集,与其说他学杜,还不如说他学苏更为中的。
如前文所述,唐庚视苏轼为“前辈”、“老师”,对其充满了敬仰之情,故而在诗歌创作时,他往往会有意无意地模仿苏轼。首先,在语汇意象方面,唐庚诗集中不仅有遣词造句直接袭自苏诗的,也有意匠经营间接化自苏诗的,略举数例:

唐庚与苏轼诗句对比

④按:卷数据宋刻本《眉山唐先生文集》,下同。⑤按:页数据中华书局本《苏轼诗集》,下同。
从唐庚诗对苏诗语句意象的承袭或化用来看,其于苏轼诗可谓烂熟于胸。特别是那些化用的诗句,经过唐庚的锤炼推敲后,基本摆脱了单纯的步趋模拟,意象整合自然熨帖。
其次,除了在语句上直接引用或间接化用苏诗之外,唐庚也试图营造出如苏诗一般高妙幽深的意境。如其名篇《醉眠》:
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馀花犹可醉,好鸟不妨眠。世味门常掩,时光簟已便。梦中频得句,拈笔又忘筌。[7]卷3
此诗颇具庄子所谓“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者”之美,其幽深新奇的意境,在某种意义上也和苏轼旷达的心态、流丽的诗风相合。罗大经《鹤林玉露》云:
唐子西诗云:“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煑苦茗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竹,与麛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潄齿濯足。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笔迹、画卷纵观之,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一两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边,解后园翁溪友,问桑麻,说秔稻,量晴校雨,探节数,时相与剧谈一饷。归而倚杖柴门之下,则夕阳在山,紫绿万状,变幻顷刻,恍可人目。牛背笛声,两两来归,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谓妙絶。然此句妙矣,识其妙者盖少。彼牵黄臂苍,驰猎于声利之场者,但见衮衮马头尘,匆匆驹隙影耳。乌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则东坡所谓:“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15]
罗大经家在深山之中,偶读“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之句,顿生心有戚戚之感。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此诗“妙绝”之处正在与苏轼诗境的暗合。苏诗“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强调的是一种“静”的境界,是一种与世无争、物我两忘的静穆与平和。而《醉眠》一诗,从表面上看似乎与苏诗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唐庚正是将这种在静穆中所得之趣,通过“山静”、“日长”、“馀花”、“好鸟”等一系列意象的组合自然清新地表达了出来,摆脱了字词的约束,在意境深处达到了与苏诗的共鸣。罗氏于此诗可谓已得骊珠。
三、苏轼诗学观对唐庚的影响——言简意长、属对精工
苏轼作诗富于想象、长于博喻、善于体物,尝言“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其古诗则纵横奔逸、议论开阖;近体则言简意长、属对精工。唐庚对东坡后一种诗学思想极为服膺,每每叹“其叙事简当,而不害其为工”。在平日的诗歌实践中,他也极力贯彻“简约”、“精工”的诗学观。
钱锺书《宋诗选注》言:“(唐庚)在当时可能是最简练、最紧凑的诗人。”[16]此评可谓一语中的。唐庚作诗之所以简练、紧凑,实际上是取法东坡“以约词纪事”之风,追求语简意长。
《文录》云:“谢固为绵州推官。推官之廨,欧阳文忠公生焉。谢作六一堂,求余赋诗。余雅善东坡以约词纪事,冥搜竟夕,仅得句云:‘即彼生处所,馆之与周旋’。然深有愧于东坡矣。”[6]445细品其句,亦颇简约明晰,而诗人仍自觉“深有愧于东坡”,于此不难想见唐庚对于苏诗的倾倒了。
《文录》中还有关于苏轼纪事简约的记载,如:
东坡诗叙事言简而意尽。惠州有潭,潭有潜蛟,人未之信也。虎饮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东坡以十字道尽,云:“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则知虎以饮水而召灾,言“饥”则蛟食其肉矣。[6]445-446
潜蛟食虎,他人或数十言不能达,而在苏轼笔下,仅寥寥十字便已刻画得淋漓尽致,难怪唐庚会对其心悦诚服。
再反观唐庚自身诗作,他确实在力求简约的道路上身体力行。以其名篇《讯囚》为例,诗云:
参军坐厅事,据案嚼齿牙。引囚到庭下,囚口争喧哗。参军气益振,声厉语更切:“自古官中财,一一民膏血。为吏掌管钥,反窃以自私。人不汝谁何,如摘颔下髭。事老恶自彰,证佐日月明。推穷见毛脉,那可口舌争?”有囚奋然出,请与参军辨:“参军心如眼,有睫不自见。参军在场屋,薄薄有声称。只今作参军,几时得骞腾。无功食国禄,去窃能几何。上官乃容隠,曾不加谴诃。囚今信有罪,参军宜揣分。等是为贫计,何苦独相困。”参军噤无语,反顾吏卒羞。包裹琴与书,明日吾归休。[7]卷4
此诗用反讽的语调、简练的笔法揭露了官场上的黑暗与不公,一反“大官威,小官卑”的固定模式,向世人展现了一幕精彩的堂前审判。诗中参军的形象被唐庚刻画得入木三分,先是一副据案啮齿、威严庄重之态,其训斥囚徒之语更是正义凛然、针针见血。至此处,诗人忽然笔锋一转,重点描写囚徒奋然出列、据理力争的场景,囚徒之语无疑是对当时官场的深刻嘲讽,令人啼笑皆非。诗结尾处,诗人又作了出人意表的处理,突出了参军的无言以对、自惭形秽,反讽意味达到极致。这个参军,其实正是作者自己。唐庚《书宋尚书集后》文云:“元符二年(1099),……予典狱益昌。”[7]卷18其职当为司理参军。统观全篇,语言凝炼而生动,纪事达意而传神,可谓深得东坡“善以约词纪事”之风。
唐庚为文亦循意简言赅之法。如《惠州谢复官表》一文,虽为应用文体,行文却也简明流畅,故能为人所称道。南宋周煇《清波杂志》载:“顷年,番江初刊成《唐子西集》,时寓公曲肱熊叔雅来见先人,偶案间置此书,顾辉曰:‘曾看否?第九卷第一篇《惠州谢复官表》,首云:“始以为梦,既而果然。”语简而意足,可法也。’”[17]
除简练、紧凑外,唐庚诗作屡为后人所嘉许之处还在一个“工”字。如《九日怀舍弟》:“重阳陶令节,单阏贾生年。秋色苍梧外,衰颜紫菊前。登高知地尽,引满觉天旋。去岁京城雨,茱萸对惠连。”[7]卷2方回《瀛奎律髓》云:“唐子西诗无往不工。此政和辛卯年谪居惠州时。用‘单阏贾生’对‘重阳陶令’,工矣。‘苍梧’、‘紫菊’又工。‘登高’、‘引满’,‘地尽’、‘天旋’之联,又愈工。末句用‘茱萸’事思弟,尤工也。”[8]600
方回一语即道出此诗属对之工、隶事之切,更进一步称赞“唐子西诗无往不工”。究其原因,唐庚正是受了苏轼追求属对精工诗学观念的影响,并在不断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工”的诗风。
苏辙尝云:“东坡律诗最忌属对偏枯,不容一句不善者。”[18]诚然,苏轼作诗极讲求属对精工,容不得半点偏枯与生硬,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诗的优劣。其作《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云:“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9]2246,可见,晚年苏轼自感欣慰之事正在一个“工”字,这尤其表现在用事和对仗方面,如《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9]2155;《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令作诗》:“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9]523;《别黄州》:“桑下岂无三宿恋,尊前聊与一身归”[9]1201,等等。
唐庚虽受苏轼诗学思想的影响,追求简约与精工,然他们在通往“精工”的道路上,却并非沿同一轨迹。众所周知,苏轼律诗之所以贴切精工,是由其才大及饱学所致。《苕溪渔隐丛话》卷二五引惠洪《冷斋夜话》云:“韩子苍曰:丁晋公海外诗:‘草解忘忧忧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世以为工。及读东坡诗:‘花曾识面香仍好,鸟不知名声自呼’,便觉才力相去远矣。”⑥注:今本惠洪《冷斋夜话》卷六引作“花非识面尝含笑,鸟不知名时自呼”,与苏集、《丛话》不同。[19]按:苏轼此诗题为“惠州近城数小山类蜀道,春与进士许毅野步,会意处饮之。且醉,作诗以记。适参寥专使欲归,使持此以示西湖之上诸友,庶使知余未尝一日忘湖山也。”“花曾识面”,知蜀道亦有此花;“鸟不知名”,则言鸟为川中所无,两句皆与家乡相扣。
又如叶梦得《石林诗话》云:“诗之用事,不可牵强,必至于不得不用而后用之,则事辞为一,莫见其安排斗凑之迹。苏子瞻作人挽诗云:‘岂意日斜庚子后,忽惊岁在巳辰年。’此乃天生作对,不假人力。”[20]按:贾谊《鵩鸟赋》云:“单阏之岁,四月孟夏。庚子日斜,鵩集于舍。”[21]《后汉书·郑玄传》:“玄乃以病自乞还家,五年春,梦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既寤,以谶合之,知命当终。”[22]《两汉书》信手拈来,干支之对既工,隶事又不见斧凿之痕。
唐庚显然没有苏轼如此高的天赋和才力,故只能通过“日锻月炼”和“冥思苦吟”来达到“工”的境界。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即指出:
他和苏轼算得小同乡,也贬斥在惠州多年,身世有点相像,而且很佩服苏轼。可是他们两人讲起创作经验来,一个是欢天喜地,一个是愁眉苦脸。苏轼说:‘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唐庚的话恰好相反:“诗最难事也!吾……作诗甚苦,悲吟累日,然后成篇……明日取读,瑕疵百出,辄复悲吟累日,返复改正……复数日取出读之,病复出,凡如此数四。”[16]
换句话说,唐庚虽然受苏轼影响而推崇精工的诗风,然而他很清楚自己与苏轼在追求“工”的道路上有着质的差别。《文录》载:
诗在与人商论,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闲一字,放过则不可,殆近法家,难以言恕矣,故谓之诗律。东坡云:“敢将诗律斗深严。”予亦云:“诗律伤严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难易二涂,学者不能强所劣,往往舍难而趋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
同样是面对苛严的诗律,苏轼往往可以信手拈来、潇洒自若,似乎有“愈战愈勇”之势。而唐庚虽觉“诗律”之严近乎法家之“寡恩”,因而“作诗甚苦”,但仍“悲吟累日”,反复修改,以求其工。这使我们不由得想起颜回的力学孔子而得“具体而微”之誉[12]卷3《公孫丑上》此其所以为“小东坡”欤?
世人知唐庚者少,知“小东坡”者多矣!南宋林希夷云:“唐子西学东坡者也,得其气骨而未尽其变态之妙,闲有直致处,然无一点尘俗,亦佳作也。”[23]惜唐庚晚出,未得及苏轼之门,然自青年时期与其有过一面之缘之后,便心生敬慕,纵使后来入张商英门下,犹初衷不改。在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上,他更以苏轼为宗,视己为其私淑之门生。故刘克庄云:“唐子西诸文皆高,不独诗也。其出稍晚,使及坡门,当不在秦、晁之下。”[4]26唐庚一生尊苏、学苏,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与执着,终于自成一家,不仅在北宋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开启了南宋诗坛学苏之风,终无愧“小东坡”之美称!
[1]刘克庄.唐子西故居二首其一[M]∥全宋詩卷3081:58 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王士禛.居易录:卷11[M].王渔洋遗书本.
[3]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55[M].北京:中华书局,1997:2187.
[4]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2[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22[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1199-1201.
[6]强行父.唐子西文录[M]∥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9.
[7]唐庚.眉山唐先生文集[M]∥中華再造善本据宋刻本影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8]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43[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9]苏轼.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祝穆.方舆胜览:卷36[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1]毛亨,郑玄,孔颖达.毛诗注疏:卷4 东门之墠[M].清阮刻十三经注疏本.
[12]赵岐,孙奭.孟子注疏[M].清阮刻十三经注疏本.
[13]郭绍虞.宋诗话考[M].北京:中华书局,1979:48.
[14]周紫芝.竹坡诗话:卷1[M].百川学海本.
[15]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4[M].北京:中华书局,1997:304.
[16]钱锺书.宋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17]周煇.清波杂志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151.
[18]苏籀.栾城先生遗言:卷1[M].百川学海本.
[19]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2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72.
[20]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M].百川学海本.
[21]萧统.文选:卷13[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604.
[22]范晔.后汉书:卷35 郑玄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1211.
[23]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1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