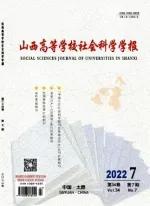新绛东岳稷益庙壁画艺术特色浅析
2013-08-15张云志
张云志
(太原大学应用艺术系,山西 太原 030032)
东岳稷益庙位于新绛县城西南15公里的阳王镇阳王村,俗称“阳王庙”,为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在仅存明代遗留的正殿五楹和戏台一座。此庙创建年代久远但建筑规模不是很大,据庙内碑文记载,元、明、清都曾经重修或增建过。东岳稷益庙在当地的宗教信仰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东岳稷益庙壁画概况
东岳稷益庙的壁画均绘制于正殿的东、西、南四部分墙面上①南壁有门、窗户,南壁壁画分两部分,分别绘制在门窗两侧的东梢间和西梢间上。,大约有130平方米左右。
东岳稷益庙壁画绘制工作完成于明武宗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据记载由翼城县画师常儒与其子常耒来、常耜,其门徒张絪和绛州画士陈圆及其侄陈文、门徒刘崇德所画。此处壁画为情节性的工笔重彩壁画,其内容与其他寺观壁画不同,是题材特殊的历史风俗画。东岳稷益庙四部分墙面都绘有一个主题,主题画面绘制得庞大且精美;其他情节性画面较主体画面小,绘制于主题画面的外围,非常便于观赏。画面中的人物形象生动,形态各异,动物、植物栩栩如生,房屋建筑、器皿物品绘制精美,使观赏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二、东岳稷益庙壁画题材分析
我国现存的寺观壁画的题材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以佛教人物、佛教经变、供养人为题材,佛寺中即以这些为题材绘制壁画。如:山西平顺县大云院弥陀殿观世音菩萨像;山西高平开化寺大雄宝殿西壁华色比丘尼经变;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供养人。二是以道教神祗、道教故事为题材,道观即以此题材绘制壁画。如:山西芮城永乐宫三清殿《朝元图》。三是以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水陆法会为题材。如山西浑源永安寺传法正殿东壁所绘天地水三官众、南壁东梢间所绘往古九流百家众。四是新绛东岳稷益庙壁画的题材较为罕见,与其他寺观壁画有别,它既不以佛教内容为题材,也不是反映儒道合流,因为东岳稷益庙壁画是以我国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为题材的,其中还穿插了许多自然景观和带有浓厚晋南民俗的生活场景,所以可以称之为历史风俗画。是以我国古代历史传说和神话传说为题材,把赐种典礼及官民朝拜东岳、后稷、伯益时的场景和有关后稷、伯益的传说以及各种晋南民间生活、生产情节绘于壁上。巧妙地将道教信仰和祖先崇拜结合了起来,既迎合了我国祖先崇拜的牢固的民间习俗,也迎合了当时中国宗教信仰世俗化的潮流。这些从民间传说中提炼出的故事情节和从当时社会实践中凝炼出的生产、生活场景,既拉近了人们所崇尚、祈福的理想未来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增加了所供奉人物的可信度;又使壁画内容通俗易懂,增强了画面的观赏性。
三、东岳稷益庙壁画的场景构图
有效传达壁画内容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场景描绘②传达壁画内容的手段还有榜题等。,而合适的构图是画面场景描绘的前提。东岳稷益庙的《赐种、朝拜典礼图》《朝拜图》将人物、建筑、植物等的比例、结构、形态以一种写实的手法分别绘制在正殿东、西两面墙壁上,这种实景式的构图法营造出了具有浓厚的现实生活气息的真实场景。从而使画面以一种直观、写实的叙事方式向观者展现出“赐种、朝拜典礼”,“朝拜”场面宏大、人物众多的高潮场景。
《赐种、朝拜典礼图》《朝拜图》的构图均采取俯视的视角,画面中的人群、建筑、植物等均为对称形式陈列,但形态又各不相同,这种在对称中求变化,寓变化于统一的构图方式,将观者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中心情节上,使观者仿佛亦置身其中。
四、东岳稷益庙壁画中的人物类型
东岳稷益庙壁画描绘的人物众多,约有四百余人,造型生动形象、动静结合,人物身体比例适度、动作协调,神态表情也表现得惟妙惟肖,是此殿壁画精彩之处。所绘人物的造型因其身份不同而造型各异,大致可分为六类。
1.帝王。绘于东西两壁的六位主像,或头戴十二旒冠冕,或戴乌纱折上巾,或戴王冠显示出他们与众不同的帝王身份。为了突出东西两壁这六位主像的地位,他们的身体比例大约是文武群臣的两倍,画者又以仰视的视角表现,更显出其地位的尊贵。
2.官吏。画者按官吏身份和地位的高低绘制,排列有序,他们或专注、或交谈、或拱手、或捧笏板、或拿宗卷、或驻立、或行进,姿态各异。
3.侍女。画者依其身份和所在场合不同而所绘有别,侍奉帝王者多衣饰华丽,在厢房劳作者衣饰相对朴素。侍女们有聚有散的被安排在画面中,或低语交谈、或眉目传情,使整个画面充满了生机和意趣。
4.武将。此殿中的武将大致可分为武士和护卫两种。武士类位于东、西两壁中部人群前,他们身形高大,动作造型极富形式感。护卫主要位于东壁殿前两侧、西壁主像身后及拜坛前两侧,他们或肃穆静立、或回首低语,有静有动,统一中有变化。
5.神仙鬼卒。画者在绘制神仙鬼卒时已经将他们完全人格化了,只是在描绘神仙鬼卒的面孔时用了比较夸张的手法,大都面目狰狞,但他们的体态、装束与常人并无不同。
6.农夫。东岳稷益庙壁画中最有特色的是画面中描绘了非常多的普通农夫,有的押巨蝗前行,有的在田间劳作。东壁左下角绘有一群押巨蝗前行的农夫是画面的高潮。这些劳动人物的造型绝不是从壁画粉本上临摹来的,而是画者从生活实践中亲身体验得来的,使画面中的情感更靠近观赏者的认知。
五、东岳稷益庙壁画中的山水画
东岳稷益庙壁画中的山水画因殿堂壁画的功能决定其只能以背景和环境衬托的形式呈现在观者面前的。尽管不是主题也没有单独成幅描绘,但东岳稷益庙壁画中山水画的风格仍值得一提。
以中国古代山水画的发展及各个流派为参照,对比观察东岳稷益庙壁画中的山水画所描绘的山峦、岩壁、溪流、松柏、林木,发现多以水墨绘制而成,注重笔墨结合,皴擦点染浓淡相宜。山石多用斧劈皴,使之山势如削,松柏树木勾勒之后更注重皴擦,使之苍劲挺拔,山水、树石为了整个画面的需要恰当地穿插在画面中,虽是背景或环境之衬托,但在艺术表现上极其讲究经营位置和笔墨意境的表达,从而呈现出一种高洁的风骨和典雅的气韵。由此,不难确定东岳稷益庙壁画中的山水画以水墨山水画为主,并稍有赋色。我国古代水墨山水始于唐,成于宋,盛于元、明,绘画发展过程中各门类间的融合,对壁画的绘制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下笔遒劲、设色清润并以大斧劈皴画山石峰峦等这些技法和用笔来看,东岳稷益庙壁画中的山水画似马远之风格,但从画面中丰富的措景和注重生活实感来看,也融入了明初浙派中杰出者戴进(亦取法马远、夏圭)之风格。此种情形符合历史实际,因为明初山水画坛以崇尚宋代绘画的浙派为主流,画院内外,追随戴进画风者极多,画手遍于宫廷与民间,由此可以看出,浙派的影响之广,也可以看出,水墨山水画对壁画的影响,正是这种实质性的影响使东岳稷益庙明代壁画具有“现存宋、金以至元代壁画所不可比拟的”[1]129典雅风格且脱颖而出。
六、东岳稷益庙明代壁画的线条和颜色
首先看线条。我国古代壁画中的线条是画面上所有艺术形象的骨骼,谢赫提出的“六法”中,就提到了“骨法用笔”,即运用线描表达对象形体、特征的笔法要求,将表现物象的结构与笔法联系在一起。如此看来中国古代画家对用线条塑造形象且注重笔法,关注已久。随着历代画家对线条表现力和笔法的不断研磨,创造出了例如“吴带当风,曹衣出水”等极具线条表现力的风格样式和“十八描”等具体的线描法,这些风格技巧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且一直为画家们学习、研究。
东岳稷益庙壁画中的线条,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传统绘画中“骨法用笔”的优良传统,画面线条运用兰叶描、钉头鼠尾描、铁线描等线描方法,笔法流畅自如,线条劲健有力,人物面部的勾勒工整、精细,所绘须发笔笔见功,衣纹短线转折遒劲有力,长线圆润流畅,人物之绶带、宽袖有“吴带当风”之余韵。通过线条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将画面中物体的造型、人物的动态描绘的准确而生动,从而将中锋线描的丰富表现力发挥到了极高的水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东岳稷益庙壁画线条的疏密组织和简练写实的表现方法。例如:西壁东岳像其身体右侧线条密,左侧线条疏,通过这种精妙的疏密组织,生动地将人物的动态和衣纹走向表现了出来。再如:东壁左下方的束蝗农夫,画者用简练概括的线条将其动态、神韵表现得写实而传神。因此,东岳稷益庙壁画中除了宏大的场景和丰富的内容,画面中极具表现力的线条也是其艺术魅力之所在。
其次看颜色。画面色彩的运用是表现壁画艺术效果的关键。东岳稷益庙壁画着色以青、绿为主,红、白次之,另以黄色、黑色穿插点缀。画面中山石、树木、宫殿、人物衣饰多用青绿,使整殿画面呈现出一种古朴典雅的格调。而帝王、官贵、侍女等所着的红装和殿堂红柱、红围栏以及黄色的点缀使画面呈现出一种华丽、热闹的气氛。农夫衣饰和护卫围领多为白色,一方面区别身份,一方面白色又使画面有明朗之感。乌纱、须发、树干、岩石的皴擦则用黑色,使画面不流于艳俗而有沉稳之感。
在着色方式上,人物面部及裸露肌肤用传统的层层晕染着色的方法,尤其是画中侍女面部用了“三白法”,增强了人物面部的立体感;山水树石多以水墨方法绘之稍有赋色;其余人物衣饰、物品、宫殿等多采用重彩平涂的着色方法。近处场景色实,远处山水、人物色淡,突出了主题,增强了壁画的层次感和装饰效果。
七、东岳稷益庙壁画艺术价值
新绛东岳稷益庙壁画是山西现存寺观壁画中的精品之一。
首先,此处壁画是目前我国北方现存寺观壁画中题材较为特殊的一例,所体现出的宗教信仰有其独特的价值意义。此处将东岳、后稷、伯益供奉于一殿之中,巧妙地将道教信仰和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反映了当地百姓因为他们功德卓著对他们的崇拜和尊敬,也反映出当地百姓对丰收和繁衍的重视。所描绘的情节都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人物、情节多与农业有关,据记载,古代绛州人“勤稼穑”、“喜祀神”①据《山西通志》(明·成化版),绛州人喜祀神,“人性刚悍,多勇敢。然勤稼穑。好储蓄,民生质实,不事奢华。好读书,勤耕织”。[2],深知“生必本于稼穑”的道理。他们不仅自己对待稼穑兢兢业业敢于同自然灾难斗争,还把希望寄托于神灵,希望不由自己掌握之事能在神灵的庇佑下遂其所愿。东岳稷益庙壁画既是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宣扬亦是对后世勤劳和勇敢民众的鼓励和启迪。
其次,东岳稷益庙壁画在人物塑造和场景构图上有其独到的艺术经验和贡献。画面描绘人物众多,画者因其身份不同而造型不同,各类人物姿态相异,动静结合,画者还充分利用人物之间的感情交流来加强画面构图的内在联系,在人物画走入低谷的明代,有此佳作传承,其艺术影响和贡献是不可忽视的。画面场景中的房屋、花草树木、动物、山峦等绘制得非常精致,画面构图讲究,在对称中求变化,寓变化于统一,将庞大的场景、复杂的内容合理美观地安排在画面上,“把历史传说、民间信仰和社会生活结合在一起,把天上、人间、地狱融为一体,既展示出传统技法、又具有时代的创新精神。”[1]128
再次,画者精湛的艺术功力,在古代寺观壁画艺术的传承和研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全国范围来讲,宋、金以后,随着宗教教势的衰微,寺观壁画远不像唐代那样隆盛了,优秀作品未见记述,实物已荡然无存。”[3]随着文人画的盛行,壁画的画者不再是宫廷画师而变成了民间画匠,加上重卷轴轻壁画、尊文人轻工匠之风的盛行,明代壁画技艺日趋平庸,佳作大幅减少。然而东岳稷益庙壁画画面中极具表现力的线条、典雅的画面设色以及没有单独成幅只作为背景和环境衬托却超凡脱俗的山水画,均体现出画者对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深刻领悟和熟练掌握。在我国寺观壁画走向衰败之时留下如此佳作,对壁画艺术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
东岳稷益庙壁画是山西明代寺观壁画中出类拔萃的一例,表现了民间画工的精湛的技艺和极高的艺术修养。是宋明之际壁画艺术由庙堂走入民间转折阶段之典型风范[4]。
[1]柴泽俊.山西寺观壁画[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2]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明·成化版[M].北京:中华书局,1998:41.
[3]柴泽俊.山西古代寺观壁画之艺术价值,文物[J].1999(1):54.
[4]品 丰,苏 庆.历代寺观壁画艺术之新绛稷益庙壁画、繁峙公主寺壁画[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