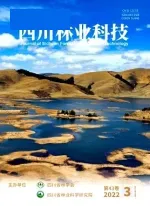森林资源调查与林业碳汇计量耦合性的探讨
2013-08-15赖长鸿王丽丽
张 文,赖长鸿,张 诚,王丽丽,刘 波
(四川省森林资源和荒漠化监测中心,四川 成都 610081)
1 与LULUCF相关的国际公约及我国的行动纲领
1.1 国际公约及其主要规定
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国际社会先后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京都议定书》、“波恩政治协议”和“马拉喀什协定”、《巴厘岛行动计划》等政治协议,各国就缓解气候变化问题中与林业有关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根据UNFCCC的规定,所有缔约方均有义务采用缔约方会议(COP)同意的、可比的方法学,定期编制、更新、公布和递交人为活动引起的、《蒙特利尔进程》未予管制的所有温室气体源排放和汇清除清单,即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并尽可能降低不确定性。林业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是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底,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组织完成了《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好的做法指南》(GPG LULUCF)。GPG LULUCF解决了《京都议定书》中有关LULUCF活动的碳计量方法,将所有土地及其转化统一定义为有林地、农地、草地、湿地、居住用地和其它土地及其之间相互间的转化,针对每一地类及其转化,分5大碳库计量碳贮量变化和非CO2温室气体排放;针对《京都议定书》关于造林、再造林和毁林(ARD)的条款,关于森林管理、植被恢复、农地管理和牧地管理的条款、有关LULUCF项目的温室气体源汇计量提供了方法学指南;计量上提供了由简单到复杂共3个层次的计量方法(Tier1~Tier3),使各国根据其本国的活动水平和排放或清除因子或参数的可获得性,选择适合的方法。具有高质量详细数据的缔约方可选择较高层次的方法,使不确定性得以降低。而数据缺乏甚至没有数据的缔约方也可根据国际上统计或估计的活动水平数据和默认的排放/清除因子或参数,完成LULUCF计量。目前,大部分附件I国家对森林及其与森林有关的土地利用变化使用了Tier 2和Tier 3方法以及国家参数。3个层次的计量方法分别简述如下:
Tier1,采用IPCC-1996-LUCF的基本方法,及其提供的、或者IPCC-GPG-LULUCF更新的排放和清除因子和参数的默认值,活动水平数据来自国际或国家级的估计或统计数据;
Tier2,采用具有较高分辨率的本国活动数据和排放/清除因子或参数;
Tier3,采用专门的国家碳计量系统或模型工具,活动数据基于高分辨率的数据,包括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的应用。
2006年制定了《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反映了以前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优良作法指南和不确定性管理》(GPG2000)和 GPG-LULUCF的主要成果并进行了适当修改,成为指导各个国家编制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指导文件。《2006 IPCC指南》中将 IPCC-GPG-2000中的第4章(农业)和 IPCC-GPG-LULUCF进行整合,但仍采用GPG-LULUCF 的分类结构[1,2]。
这些指南对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温室气体清单编制的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我国未来林业温室气体清单的编制面临更大的挑战。因此,为准确掌握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的碳汇潜力,给我国参与国际气候变化战略谈判提供技术支撑,提高我国未来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温室气体清单的编制质量,降低不确定性,更好的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我国迫切需要制定相关符合我国林业实际的林业碳计量体系,提高林业清单的编制能力。
1.2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纲领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2007年中国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同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下称《国家方案》)并开始实施,2008年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这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战略性文件。在《国家方案》中,明确把林业纳入我国减缓气候变化的6个重点领域和适应气候变化的4个重点领域当中,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中,指出林业是我国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行动的重要内容。2009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我国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宣布我国确立到2020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 ~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hm2,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m3。
提高森林覆盖率、恢复和保护森林资源是减少碳排放、缓解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之一。中国政府极为重视林业碳汇,《国家方案》中把林业纳入我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2009年6月召开的中央林业工作会议指出: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林业具有特殊地位,并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必须把发展林业作为战略选择”。为贯彻落实《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赋予林业的任务,2009年11月6日国家林业局发布《应对气候变化林业行动计划》(下称《林业行动计划》),将《国家方案》在林业领域进行具体化,确定了5项基本原则、3个阶段性目标,实施22项主要行动,作为指导各级林业部门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纲领性文件[3]。
我国确定的减排目标,既是我国政府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也是我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巨大努力,是我国向国际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国家方案》明确了林业碳汇在实现我国减排目标中的重要地位;《行动计划》则对今后的林业碳汇的原则、目标、措施给予了明确的指导和确定。
2 开展森林碳汇计量的基础与必要性
2.1 开展森林碳汇计量的基础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共分五大部门来分别编制,包括能源、工业、农业、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废弃物。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最复杂和不确定性最大的部分。
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研究森林生态系统的生物量和生产力,在自寒温带至热带地区的主要森林类型和一些典型区域进行了一些研究工作,为全面推动我国在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方面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我国域广阔,拥有自寒温带至热带的气候地带变异性和特殊的地理区,对各种类型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均不够,加之经费投入不足,研究基础差,所获得的研究数据和成果不成系统。同时,大部分研究没有与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和其它履约需求紧密结合。在林业温室气体清单计算中的大多数参数均采用国际上的缺省值,与我国实际情况相比存在较大的误差;采用的部分国内参数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使得我国首次林业温室气体清单的不确定性高达±50%。
2.2 开展森林碳汇计量的必要性
2.2.1 是增强国家气候谈判筹码的迫切需要
森林是陆地碳循环中重要的汇和库,林业碳汇计量和监测的研究是开展森林生态系统碳汇功能研究的基础,逐渐成为了国内外生态学领域中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主要的研究内容是森林生态系统的固碳功能及其时空变化。根据2007年IPCC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林业是未来30 a~50 a内增加碳汇的成本最低,最经济可行的措施。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极重要力量,我国只有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和规则的制订,才能避免“碳减排、碳关税”被动,才能为国家发展赢得更好的国际环境。只有通过大尺度、比较精确的碳计量研究,才能提供可靠的森林碳储量的存量、变量以及时空分布数据,在碳汇领域才能提得出科学的证据,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因此碳计量体系的研究作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基础,显得更尤为迫切和尤为重要。
2.2.2 是履行国际公约的基础工作
我国定期编制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报告温室气体排放是必须履行的国际公约义务。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生态系统类型多样,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的类型复杂,规模较大,使得我国林业碳源、碳汇的计量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采用IPCC最新指南编制我国林业温室气体清单面临许多挑战。首次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不确定性高50%,不仅不符合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也严重不适应国际形势发展。有必要在国家宏观层面研究成果的科学总结基础上,采取宏观探讨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办法,开展数据采集与数据处理示范研究,整合相关科学和数据资源,借鉴国际先进做法,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林业碳计量方法体系,提高林业碳计量系统科技含量,降低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系统误差,研发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林业碳计量体系,提供政策决策和国际公约谈判科学依据,最终满足我国履行气候公约及制定国内可持续发展政策的需要。
2.2.3 是服务林业碳汇发展的科学基础
林业碳汇项目的发展存在较多困难。从技术层面上讲,服务于碳汇发展的现代经营学、现代经理学相关理论与实践有待进一步丰富与完善,尤其是森林营造、经营调控和森林抚育。从操作层面上看,碳汇项目的组织与实践与传统林业项目差异悬殊。林业碳汇项目不仅单纯的营造林工程项目,而且更多的内涵在于森林碳汇的交易,是经济学的新兴领域。林业碳汇项目的成功离不开林业工程造林,更离不开国际碳汇市场的把握与掌控。碳汇造林技术和交易规则在林业碳汇项目发展中十分关键,特别是有关碳汇的计量标准、监测手段与核实办法,只有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在汇的计量、潜力与监测等方面提供强有力的科学依据,才能让国际社会更多地、更信服地采纳和借用中国方法和标准,不仅增加我国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发言权,而且更好地服务林业碳汇的发展。
2.2.4 是现代林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林业既是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国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资源。现代林业的发展要求赋予了林业新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要求,“在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在生态建设中具有首要地位,在西部大开发中具有基础地位,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具有特殊地位”、“实现科学发展必须把发展林业作为重大举措,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把发展林业作为首要任务,应对气候变化必须把发展林业作为战略选择,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把发展林业作为重要途径”。
森林是陆地上最大的储碳库和最经济的吸碳器,与工业减排相比,森林固碳具有投资少、代价低、综合效益大的优点。发展现代林业,增强森林碳汇功能,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林业碳汇计量体系建设,可以综合掌握森林碳汇储量、变量时空分布,从而能够从科学发展的高度优化森林碳汇时空布局,能够从又好又快发展的高度调整发展方向和重点,起到最大可能增加储量、最直接有效规避风险的安全保障[4~6]。
3 森林资源调查体系与四川省森林资源连续清查
3.1 森林资源调查体系与特点
3.1.1 森林资源调查体系
森林资源调查是全面掌握森林资源现状及特点的一项专业技术工作,也是林业行业管理、政策辅助决策的基础性工作。根据不同的需要或不同尺度和区域的特点,森林资源调查的目的、手段和方法都有所区别。我国已经建立了适应我国森林资源特点和管理制度的调查体系,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国的森林资源调查体系可以概括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是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即一类清查。连续清查以省为总体进行抽样调查,全国以5 a为一个调查期间,每年完成1/5的省份调查工作,1979年连续清查体系建立,到2011年,全国正在开展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第8次复查。第二层级是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即二类调查。规划设计调查以森林经营单位或县级行政区为调查总体,对总体内面积进行区划调查,对蓄积进行目测与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全面调查,一般以10 a(一个森林经理期)为调查周期。四川已先后完成了两期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第3期调查工作已陆续启动。第三层级是森林资源专题调查,即三类调查或专业调查。专题调查是以某一作业任务或专题为调查目的,采用与之相适应的调查方法,对关心的主题进行深入调查,从而达到掌握现状与分布的目的。三类调查在行业日常管理应用中最多,如各种作业设计调查、森林土壤调查、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等。第四层级是森林资源状况年度核查调查,是以满足特定工程、特定项目为对象,对其实施情况和实施成效进行现场检查和调查,达到评价工程或项目实施情况的目的。
3.1.2 森林资源调查体系的特点
从调查体系层级可以看出,不同的调查等级适应不同的管理需要。一类清查首先满足国家掌握森林现状与动态的需要,只对全省做出总体估计,不对信息进行地理位置上的落实;二类调查要求落实森林类型和分布,满足森林经营单位开展规划设计总体需要;三类调查是对二类调查信息的进一步丰富和细化,满足特定专业和专题规划、实施的基本要求;检查验收是以评价工程实施为目的而展开的检查性质的现状调查。一类清查成果能够提供国家和省级应用;二类调查成果仅服务于森林经营单位;三类调查服务于森林经营单位特定经营措施。在这些调查中,从省级应用角度看,二类调查是基础,专题调查和年度核查是年度更新和动态变化的依据。
3.2 四川森林资源连续清查
四川省森林资源连续清查体系始于1979年“四五”清查。在当时情景下,根据对森林面积与蓄积、人工林面积与蓄积的抽样精度要求,在四川范围内(包括重庆市)布设了23588个地面调查样地。
1979年初建体系调查后,经研究发现样地数量太多,工作量太大,抽样体系过于臃肿,加之四川地形复杂,个别区域交通通达条件特别困难,故在1988年第一次复查时,将全省分为金沙江雅砻江原始林区、盆周西缘陡险山区和其余区域3个副总体分别布设样地、分别调查方法进行复查。前两个副总体限于交通等条件限制,采用资料推算方法进行资源更新;余下部分样地2/3为固定,1/3为临时,固定与临时都进行地面调查,为体系优化与完善做基础。
1988年体系经1992年、1997年两次复查,在国家对生态环境的日益重视,抽样体系表现出了不能完全满足国家宏观决策和四川林业发展的客观需求的缺陷,故2002年在第四次复查工作准备过程中,对抽样体系进行了进一步优化完善研究。将原3个副总体合并为1个总体,统称四川省总体。以4×8和8×8 km(平均6×8)两种间距进行样地布点,共计布设10098个样地。
四川森林资源连续清查从1979年建立到第5次复查(2007年),其布点体系一直处于优化与完善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不断研究、不断优化与完善的体系。在优化与完善过程中,布点体系、样地位置保持了稳定,从而保证了连续清查体系的延续性。在历次复查中,地类、林种、起源、优势树种、龄组以及每木检尺、优势树种平均高等基础内容都得到了较好的调查与延续。这些资料,为计算林分的乔木层的碳汇变化提供了最关键的基础数据。
4 林业碳汇计量基本要求与资源调查体系间的耦合性分析
4.1 林业碳汇计量的原则要求
根据IPCC-2006-GPG LULUCF,首先,碳汇计量要求区分6大类土地利用类型(林地、农地、草地、湿地、聚居地、其他土地),并量化它们之间的相互转换,即计量时点的现状(Current Status)与转移矩阵(Transfer Matrix)。其次,碳汇计量应尽量体现不同汇源的差异性,即生态区域(Ecological zones)、经营管理(Management)、森林类型(Forestry Type)以及起源(Origin)、年龄(Age or Age Groups)等都差异因素都属体系考虑范畴。第三,较高方法学(Tier3)不仅要求数量(Quantity)的准确性,还应应用遥感(R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必须满足空间分布(Spatial Distribution)基本要求;第四,碳汇计量不仅是总量的估算,还要求分别5大碳库(地上部分、地下部分、死木、枯落物、土壤有机碳)进行核算。第五,汇与源(Sink and Source)分别计量,估算净增量。对各种森林经营活动的排放要进行源的计量。最后,需对计量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进行系统分析和报告。根据2006年IPCC指南-LULUCF,温室气体清单中与LULUCF相关的章节中,应估算出林地和转化为林地的土地上的5种碳库变化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应论述5种碳库和相同土地区域内不同碳库池(carbon sink)之间的碳转移,包括人类活动引起的管理森林的碳库变化,例如人工林的营造或采伐、商业性采伐、火烧木采集、其他管理做法等,此外还包括火烧、风灾、病虫害或其他扰乱引起的CO2排放或非CO2排放。
4.2 森林资源调查体系与碳汇计量的耦合性分析
4.2.1 适应性分析
(1)数据时效性强,成果可对比性好。从调查体系上分析,无论是一类清查,还是二类调查,都有相应的调查时效的规定,因此,多期森林资源调查成果基本能够满足碳汇计量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相互转换的需要。而且同等调查在多次重复时,其技术体系与方法要求差异都不大,其成果能够较好地满足碳汇计量基础数据的同口径性、可对比性。
(2)能够较好地满足乔木碳汇计量。传统森林资源调查最大的优点是对地类、树种及组成、郁闭度、树高、胸径、年龄以及单位面积蓄积与株数等内容进行了系统调查,且有严格的精度要求。有了这些内容,可以通过适当的方法满足森林乔木层生物量的估算,从而达到乔木碳汇量的计量。再结合一些经验模型,也可以进一步按IPCC要求的差异性计量乔木的枝、干、叶等器官生物量和碳汇量。
(3)可以提供灌草碳汇计量资料参考。灌木、草本的简要信息在森林资源调查中有所反映,如种类、盖度和高度,如果仅是粗略地估算灌草碳汇量,可以结合乔木相关信息,采用经验模型进行推算。
4.2.2 久缺性分析
从“采用较高方法学(Tier3)、降低不确定性”原则分析,森林资源调查成果在满足碳汇计量应用中仍存在下列欠缺。
(1)森林土壤信息欠缺。土壤碳在全球碳平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森林土壤有机碳储量变化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作用。土壤有机碳(1500 Pg~2000Pg,1 Pg=1×1015g)是全球陆地生物量碳(620 Pg)的2.4倍(2.5倍,是大气碳库的3倍)。森林土壤碳占全球土壤碳的73%,是森林生物量的2倍~3倍。土壤碳库0.1%的变化将导致大气圈CO2的浓度发生百万分之一的变化。全球土壤有机碳10%的变化。目前森林资源调查中,虽然对土壤种类、土层厚度、石砾含量等基本信息进行了调查和记载,但应用于碳计量,明显存在两方面的缺陷:一是信息准确性差、可靠性低,不符合碳计量精度要求;二是土壤信息不全,如土壤细根量、土壤分层碳含量等有关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关键因子没有具体调查,不能完全满足土壤有机碳储量估算的基本需要。
(2)森林经营信息欠缺。目前森林资源调查对森林的发生、演变与发展趋势等基础信息基本上没有调查与反映,尤其是森林经营相关信息。在碳计量中,经营信息差将会直接导致两个内容无法估算或者精度达不到要求的结果:一是林地类型转移矩阵无法建立,对两次调查期间小班森林经营状况没有调查,就无法提供森林演变信息,就无法满足编制IPCC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的要求,也就说明不了森林经营增加碳汇的基本情况;二是无法估算森林经营碳源和碳排放的历史数据。
(3)层次划分信息欠缺。森林群落一般有成层现象,由于所处环境条件的差异,森林群落在发生与演变过程中其结构都有所差异,尤其是天然林。不同结构的森林其碳储量的大小与能力差异十分明显。目前森林资源调查对森林结构的层次划分与信息调查不足,主要体现在:树种组成调查比较简单,仅用“十分法”反映森林树种组成,不符合碳计量精度提高的基本原则;由于没有分层调查,缺失各层平均高、枝下高、平均胸径等基础信息,即使应用蓄积量转换生物量方法进行碳计量,其精度也大打折扣;在估算碳储量时,灌木、草本盖度和平均高度十分关键,在目前基于森林蓄积的传统方法下,对灌木、草本调查过于简单,没有基本的精度要求和保证。
(4)物种记载不够详细和明确。所有物种在森林资源调查资料中记载得比较粗放,乔木一般只记载到属或科,能够鉴定到物种的情况比较少,灌木、草本植物物种记载更简单,无法反映森林群落的结构特点和立地特征。由于同科、同属的物种之间生物学特性的差异,不明确记载物种的资料无法满足碳汇计量的精确性和降低不确定性,也不能反应样地的碳汇量,更不能代表其他同科或同属物种的样地的碳汇量。
(5)枯、倒木信息欠缺。枯立木、倒木、林下枯落物也是森林碳计量必需的内容。在目前森林资源调查中,这部分信息基本上都缺失,无法估算死有机质、枯立木、倒木、枯落物的碳库。
5 结论与讨论
陈健等用生命带法的基本原理,在全国山地森林区划的25个林区的基础上,收集历次森林资源清查、生物量调查、土壤调查、土地利用变化的气象数据等资料,在每个林区确立10个监测区,按照4×6 km的样地行间距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在每个监测区设置固定样地,用于林木生物量补充调查和粗木质残体调查,同时在每个样地内随机布设5个样方用于下木植被,森林枯落物、土壤的取样调查。文章认为,通过建立与森林连续清查体系相配套的全国森林碳汇监测体系,并构建网络信息化平台,可以建立监测信息系统,实现数据网络化管理,同时结合地理系信息化系统的应用,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基础数据和决策支持[7]。
森林资源调查是各项林业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森林增加碳汇是世界的共识,森林资源调查服务于森林碳汇计量是现代林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制定林业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迫切需要,因此,有必要对现行森林资源调查方法、内容进行必要的改革与展,赋予森林资源调查更多时代特点,拓展调查成果应用领域,扩大成果应用空间。从碳计量要求上看,完全可以在不增加太多工作量的前提下,坚持“改进调查方法、充实调查内容”原则进行优化与完善。种类信息简单、层次信息弱、经营信息差以及枯倒木信息的缺失等问题可以对现有调查方法进行改进。虽然森林土壤有机碳调查需要增加大量的野外调查、室内分析工作,但森林土壤有机碳的发生与演变时间长、变动相对小,因而完全可以采用专题调查,通过模型方法得到解决,而不需要在每次调查中展开。总体上讲,一方面是森林资源调查自身应该适应林业的发展,同时从碳汇计量角度,也需要森林资源调查进行内容与方法的改革,因此,在现代林业发展背景下,对森林资源调查进行改革是必要的。
四川省2012年将要进行森林资源连续清查第6次复查工作,有必要在四川森林资源连续清查体系中,围绕碳计量的需要,对森林土壤有机碳、灌草生物量、乔灌根生物量以及枯落物等碳汇计量内容进行研究并试点。通过试点提供森林资源调查改革有益经验与借鉴。
[1]UNFCCC.Kyoto Proyocol Rererence Munuel on accounting of emissions and asigned amount.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publications/08_unfccc_kp_ref_manual.pdf.
[2]联合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convkp/kpchinese.pdf.
[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09年度报告.http://www.ccadaptation.org.cn/WebSite/accc/Upload/File/201011/20101122210312609625.pdf.
[4]周广胜.全球碳循环[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3.
[5]Shimel D S.Terrestrial ecosystem and the carbon cycle[J].Global Change Biology,1995,(1):77 ~91.
[6]Sedjo R A.The carbon cycle and global forest ecosystem[J].Water Air Soil Pollut,1993,70:295 ~307.
[7]陈健,朱德海,徐泽鸿,等.全国森林碳汇监测和计量体系的初步研究[J].生态经济,2008(5):128~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