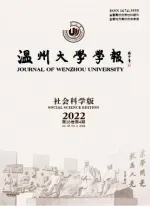论我国侦查程序中的被害人权利保护
2013-08-15骆永兴
骆永兴
(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上海 200042)
在传统的刑事司法中,一提起人权保护,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被害人的权利往往被人们忽略。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承受者,其人身、财产、精神甚至生命安全遭到了犯罪嫌疑人的侵害,他们不仅承受着财产的损失、人身的伤害,精神上也一定遭受着巨大的痛楚。他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并且能够向人们传递信息确认他们的被害人身份,他们采取积极的步骤来完成这些,主要是获得自身的满足”[1]。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中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完善侦查程序中的被害人权利保护,不仅对被害人,也必将对我国刑事司法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侦查程序中的被害人权利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一、我国侦查程序中被害人权利保护立法的不足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编的第2章是有关侦查的规定,共有11节,第2节详细规定了如何讯问犯罪嫌疑人,第3节规定了如何询问证人,却没有独立规定如何询问被害人、听取被害人意见,仅仅在第3节询问证人中规定,询问被害人适用询问证人的规定。首先,从法典的结构上弱化了被害人的地位;其次,询问证人和询问被害人的侧重点不同,方式方法也不同,简单地以询问被害人适用询问证人的规定一笔带过,不仅不能体现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也不利于对被害人合法权利的保护。
综观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在侦查程序中被害人权利保护的规定上不能形成全方位的保护体系。主要表现在许多重要的诉讼权利和权利救济途径的缺失上。美国著名法学家波斯纳说过,“诉讼为真实的或想象的不满者提供了精神宣泄。”[2]对于被害人来说,许多诉讼权利的缺失,严重阻碍了这种不满的宣泄。
(一)诉讼权利知悉权的缺失
当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犯罪行为侵害以后,被害人在寻求国家公权救济时首先接触的一般是侦查机关。侦查机关代表国家行使特定的司法职能,与被害人相比,侦查机关对刑事案件的流程及各方当事人在不同阶段享有的诉讼权利更加清楚,且我国的侦查机关担负着保护人民的职责,所以,在被害人向侦查机关报案或者提出控告以后,若由侦查机关的工作人员向被害人告知其所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对于被害人积极行使诉讼权利并保护自己将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二)侦查进程知悉权的缺失
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及各方当事人会进行多种侦查行为,且侦查程序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由于被害人的特殊身份,其肯定会非常希望了解案件进展到什么地步。侦查阶段有一套流程,除一些不能告知当事人的细节外,侦查机关应当将案件大体进程告知被害人,一方面可以对被害人起到宽慰作用,另一方面也能使被害人对侦查机关形成监督。
(三)委托诉讼代理人权的缺失
《刑事诉讼法》第 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委托律师为其辩护。第 44条规定公诉案件被害人在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两者相比,被害人可以委托代理人的时间比犯罪嫌疑人整整晚了一个阶段,在整个侦查阶段,法律都没有规定被害人可以委托代理人。一方面,从法律规定上来说,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不对等,明显体现了法律对于被害人权利的忽略;另一方面,获取专业的法律帮助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利,是双方当事人共同的愿望,尤其是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以后,身体上、心理上或者财产上都受到损害,专业法律人员的帮助就显得格外重要。
(四)调查权的缺失
《刑事诉讼法》第 50条规定,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充分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根据本条规定,侦查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吸收被害人协助调查,也可以不吸收被害人协助调查。在绝大多数案件中,被害人都非常了解案情,知道主要证据的情况,且由于被害人希望收集到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罪行,进而对其进行惩罚,所以,被害人的积极性会很高,但法律仅规定了他们可以协助调查,即使这个协助还要以侦查机关吸收他们才能进行,吸收或者不吸收的决定权还掌握在侦查机关手中,这就阻却了被害人主动收集证据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案件真相的及时查明以及有关证据的收集。
(五)撤销案件决定意见权的缺失
《刑事诉讼法》第161条规定,在侦查过程中,若侦查机关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撤销案件意味着刑事诉讼的终止,对被害人而言,国家公权机关将不再对其提供支持和救济,所以,这不仅仅是对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程序性权利的否定,也是对其实体性权利的否定。在这一终局性的决定作出之前,侦查机关无需征求被害人意见,这剥夺了被害人发表意见的权利,甚至都没有规定将撤销案件的决定告知被害人,这不仅不能体现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也不符合诉讼的精神。
(六)侦查终结决定意见权的缺失
《刑事诉讼法》第160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并没有规定是否需要征求被害人意见。侦查终结决定的作出意味着侦查程序的结束,而法律对于被害人是否还有其他要求,对侦查终结的决定是否有意见却漠不关心,忽视了被害人的存在,与被害人享有的当事人地位不符,也失去了被害人对侦查机关进行监督的途径。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法律规定的被害人享有的一些主要诉讼权利几乎没有完整的,比如知悉权,秘密受保护权,调查权等;另一方面,对于法律已经规定了的一些权利大多还缺乏救济,在实践中极易遭受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侵犯。诉讼权利以及权利救济途径的缺失是当前司法实务中被害人诉讼权利屡屡受到漠视的重要原因。
二、我国侦查程序中被害人权利保护缺陷存在的原因
(一)传统法律文化的延续
中国古代法的“最善”者、代表者《唐律疏议》的“断狱篇”规定:“诸拷囚限满而不首者,反拷告人。其被杀、被盗家人及亲属告者,不反拷。拷满不首,取保并放。违者,以故失论。”①参见: 长孙无忌. 唐律疏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即在刑事诉讼中,在被告经刑讯限满仍不服罪的情况下,依照法律应反过来拷问告发人,除了被杀、被盗者的家属外,一般的告发人都有被反拷的可能。虽然“反拷制度”设置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诬告的出现,但由此可以看出被害人在我国古代诉讼中的地位和权利保护情况。如果被害人面对的犯罪者是个“硬汉”,挺过了法律规定的可以对他施用的刑讯数,那么被害人就面临着被二次侵害的困境,最可悲的是这种侵害是由法律规定的,由审判官实施的。被害人上堂告状的目的是保护自己,不料却再遭合法的伤害,真是岂有此理!唐律汇唐前立法之精华,集唐前立法之大成,且唐后各封建朝代无不以它为蓝本,订立本代法律,虽有损益,仍不变其宗,它成了唐后这些朝代立法的楷模[3]。虽然到明朝、清朝时就取消了有关反拷的规定,但对被害人合法权利漠视的传统却被流传下来。侦查程序中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缺陷不能不说与这种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保护被害人权利观念的淡薄
当前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认识不足。司法理论界一谈及人权保障,几乎一边倒地投入到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研究之中,与之相比,只有个别学者注意到了被害人的诉讼权利问题。而在实务界,许多侦查机关工作人员认为侦查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侦查职能,并非为被害人,即使有维护被害人权益之一面,他们也认为侦查机关足以代表被害人的要求,若赋予被害人太多诉讼权利,会影响到侦查机关正常办案,对侦查机关正常的侦查活动形成掣肘。这种观念是片面的,它没有认识到侦查机关代表国家行使侦查职能与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是应当并存并重的。总而言之,人们还没有普遍认识到在侦查程序中对被害人权利进行保护的重要意义。
(三)立法上的缺陷
从前文论及的被害人在侦查程序中享有的权利以及相关分析中可知,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被害人在侦查程序中享有的权利缺陷重重,留下大片空白,不仅使被害人无法可依,侦查机关在某些情况下也无据可循。而且从法律的条文中就能看出对被害人权利的忽视,如《刑事诉讼法》第 125条规定的询问被害人适用询问证人的规定。《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诉讼权利规定的缺失、权利救济途径的缺失以及对被害人权利的漠视是导致侦查阶段对被害人权利保护不力的直接原因,也是被害人不能充分参与侦查活动,维护自己权利的直接原因。
(四)实践中司法资源的短缺
“作为人类特定实践的诉讼,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冲突主体以及统治者的主观认识中,都是一项能产生一定效果,同时又需要支付一定代价的行为。”[4]司法活动的进行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尤其是侦查阶段,要进行大量的侦查活动,若遇重大复杂的案件,则投入的司法资源更多。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无论从侦察技术,还是对司法资源的投入都不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技术的落后和司法资源的短缺必然会影响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三、我国侦查程序中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完善
(一)法制观念的转变
首先,立法者要真正意识到保护被害人权利的重要意义。保护被害人权利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方面,可以完善侦查结构,体现公平正义,也符合刑事诉讼发展的规律,且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侦查的顺利进行,可以对侦查机关形成监督减少司法腐败,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并符合国际刑事司法发展的趋势等。立法者尤其要摒弃侦查机关完全可以代表被害人的错误观念。只有从思想上端正了对保护被害人权利的认识,才能在实践中切实地保护被害人的权利。
其次,侦查人员要转变观念,树立行使国家职责和保障人权并重,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合法权益并重的观念。从情感上来说,被害人是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属于法律重点保护的对象,其更值得同情和保护。侦查人员要提高自己的法律素质,端正对被害人的态度,真正成为保护人民的卫士。同时,被害人也要转变观念。从儒家“无讼”观点发展而成的“无讼”的司法原则在中国大地上流行了几千年,可谓根深蒂固。但当前,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立,被害人应当摒弃旧时代“无讼”观中的糟粕,当自己合法权益受到犯罪行为侵害以后,要勇于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这样不仅有利于被害人保护自己的权益,而且会对侦查机关形成监督,使其更积极地保护被害人权利。
(二)具体制度的构建
1.在侦查阶段赋予被害人完善的知悉权
知悉权是指“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有了解侦查、审判机关是否立案以及诉讼进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依法享有各项诉讼权利的权利”[4]。为了完善被害人的知悉权,法律应当建立三类完整的知悉权,这并非在原来三类知悉权基础上进行完善形成的,而是在整体上重新确立的。
第一类为诉讼权利知悉权,即在被害人报案或者提出控告以后,当即由侦查机关的工作人员告知被害人享有的诉讼权利,这不仅有利于被害人,而且符合侦查机关保护人民的职责。第二类为侦查进程知悉权。在刑事诉讼的每个主要进程开始或者结束时应当告知被害人,以便于被害人根据不同的进程采取相应的维权措施。第三类为侦查决定知悉权。在侦查程序中,侦查机关会作出一系列影响侦查进程的决定,主要有:立不立案的决定,尸体解剖,侦查实验,搜查,通缉,扣押物证、书证,鉴定,申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侦查终结等。这些决定的作出,直接影响侦查进程,也会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产生影响,应当告知被害人。
2.在侦查阶段赋予被害人隐私受保护权
为了保护被害人的隐私,法律应建立完善的被害人隐私保护制度。保护的对象包括自然人被害人和法人被害人,对于涉及自然人的强奸案件、未成年人案件等,涉及法人的商业秘密案件等都应纳入隐私保护制度的范围内。在询问被害人时,与案件无关的案件细节被害人有权拒绝回答,并有向有关组织反映这一情况的权利;涉及被害人隐私的笔录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归档,禁止向外公布、透露。对于侵犯被害人隐私的侦查人员,视情节分别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任。
3.在侦查阶段赋予被害人委托代理人权
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可以委托律师,而被害人则只能在起诉阶段委托代理人,两者整整相差一个阶段。这种权利的不对等不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既然法律规定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都属于诉讼当事人,且其二者属于对立的双方,那么法律就应当赋予他们对等的权利,以体现其同为当事人的地位。犯罪嫌疑人可以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时委托律师辩护,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在与侦查机关发生联系的第一时间就可以聘请律师为其辩护,鉴于被害人毕竟与犯罪嫌疑人有所不同,犯罪嫌疑人参加诉讼是被动进入,而被害人参加诉讼是主动进入,且被害人遭受犯罪嫌疑人侵害。笔者认为,自犯罪行为发生之日起,被害人可随时委托代理人。和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只能委托律师一样,在侦查阶段,被害人委托的代理人也只能是律师。
4.在侦查阶段赋予被害人调查权
《刑事诉讼法》第 50条规定的协助调查权使被害人明显具有被动性,与其希望积极参加侦查活动形成巨大反差。被害人亲身经历案件过程,对犯罪嫌疑人及其使用的犯罪工具印象深刻,如果被害人提供的证据和线索不被侦查机关接受,就很有可能影响到整个侦查进程,甚至影响整个案件的定性,不利于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因此,法律应当赋予被害人调查权,作为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补充,不仅可以发挥被害人的积极性,减轻侦查机关压力,还能对侦查机关形成制约,最终保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5.在侦查阶段设立征求被害人意见的制度
在侦查程序中,侦查机关作出的一些重要决定,会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产生重要影响,甚至会影响侦查进展,尤其是针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的一些决定,但在当前的法律规定中,侦查机关可以直接作出这些决定,甚至无需通知被害人,这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十分不利。对于一些关乎侦查进展和被害人切身利益的决定,侦查机关不仅应当通知被害人,还应事先征求被害人意见,以做到兼听则明。这一制度不仅体现了侦查机关重视被害人,还可使被害人对侦查机关形成监督。
另外,对于其他一些已经确立但不完整的制度应当进一步完善,有些制度涵盖的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展,有些制度的救济途径需要补充。根据权利救济理论,有权利必有救济,救济为权利的实现提供了“一种程序化的保障机制”[5],所以无论是需要完善的制度,还是新建立的制度,在规定被害人享有权利的同时,还应当规定被害人对其享有的权利的救济。这包括被害人向什么部门,以何种方式寻求救济,对侵犯被害人权利需承担的法律责任等。
(三)实践中的具体措施
1.对侦查人员进行关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培训
当前,并没有对侦查人员进行专门的关于被害人培训的制度。笔者认为,在侦查人员上岗前的培训中应当加入此项内容,主要包括:一、被害人心理;二、被害人享有的权利;三、如何抚慰被害人;四、如何对待特殊人群;五、针对特殊案件的具体培训等。对侦查人员关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培训,不仅在侦查人员上岗前要系统进行,而且还应列为侦查人员日常培训的内容。
2.将被害人对侦查人员的评价作为对其考核的重要参考
在侦查终结以后,由侦查机关的特定部门组织被害人对侦查人员进行评价,作为对侦查人员考核的依据之一。这一制度不仅可以督促侦查人员注重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端正对被害人的态度,而且可以使侦查机关及时发现侦查过程中的问题,予以纠正。最终加强了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也提升了侦查机关在群众中的形象,这是一个双赢的制度。
3.经常开展侦查人员保护被害人权利的经验交流
侦查机关可以定期召开经验交流总结会,让侦查人员介绍自己的办案心得,同时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法律具有滞后性,在侦查实践中,如果侦查人员发现现行法律不能满足保护被害人权利的需要时,可以通过这种经验交流总结会进行交流归纳,并通过相应渠道向国家立法机关反映,以及时修改法律。在我国古代的唐律中就有地方官吏发现有不合适宜的法律时,必须随时向尚书省报告,经京官议定后,交皇帝处理的制度[6]。这种经验交流总结会不仅应当在侦查机关内部召开,不同的侦查机关或不同地区的侦查机关也可以相互交流,这样,一方面提高了侦查人员保护被害人权利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司法实践有了反馈立法机关的途径,促进立法的完善。
4.经常开展法制宣传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属于执法机关,也是普法的主体。笔者以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法制宣传应当形成制度,工作人员应定期以多种形式走进社区、街道进行普法。尤其是作为主要侦查机关的公安机关,更应加强有关犯罪知识的宣传,这样不仅可以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还可以未雨绸缪,使民众一旦成为被害人,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
[1] Sebba L. Third Parties: Victims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40.
[2] 波斯纳. 法理学问题[M]. 苏力,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259.
[3] 王立民. 唐律新探: 第4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
[4] 柴发邦. 体制与完善诉讼制度[M].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1: 72.
[5] 韩流. 论被害人诉权[J]. 中外法学, 2006, (3): 277-293.
[6] 王立民. 论唐律与专制统治[J]. 比较法研究, 1991, (1): 5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