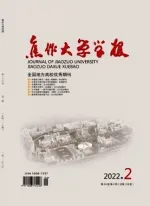以生命美学透视苏轼《江城子》
2013-08-15周晓蕾
周晓蕾
(陕西理工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是一首感情深挚的悼亡词。“苏轼十九岁娶王弗为妻,二人恩爱和睦,感情笃厚。”[1]P178王弗随苏轼官居京师,不幸于宋英宗平治二年(1065)五月亡故。乙卯是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距王弗去世整整十年。该词自问世以来,即引起了时人和后人赏读品评的浓厚兴致,然品评角度趋同,大多是从词中所蕴含的真挚感情入手,或标榜其“悼亡双璧”之一的文学地位。故此,笔者试从中国哲学所蕴含的“生命超越美学”着眼,发掘该词蕴含的“三美”,即无言之美、意境之美和永恒之美,以领悟该词蕴含的深厚美学韵味。
1.无言之美
该词分上下两片,上片写十年来生死相隔的相思之苦与自身惨淡境遇,下片写因日有所思而夜有所梦的梦中重逢与感叹。开篇“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是词人从心底迸发出郁积已久的深长悲叹之声,交代了生死相隔时间之漫长难捱、相思之弥久愈甚。十年,一个人的一生有多少个十年?相对于每个人几十年的寿命,十年并不短暂,尤其是被生死隔绝的岁月里,十年尤显得漫长和难捱。“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十年来,纵然岁月流转、世事变迁,早已物是人非、“尘满面,鬓如霜”,然惟一不变的是那缱绻心头的怀念之情和刻骨铭心的相思之苦,他不仅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她,而且思念之情历时愈久而愈深、愈浓。王菲的歌曲《我愿意》中唱道:“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然生死相隔,终不得一见。但心底的相思之情如洪水猛兽,难以困守,终要冲出牢笼,遂幻化为梦境,让饱尝相思苦痛的人儿得以一见。此时,久别重逢,有多少心里话要说,曾经的“无处话凄凉”,此时尽可畅所欲言,一吐为快了吧?非也,此时却“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郁积的波涛汹涌般的感情浪潮,在这一刻却变成了风平浪静的海面,它广阔无垠,澄净如练,“如矿出金,如铅出银”。但“相顾无言”真的是无话可说吗?这与神秘的海底世界何其相似。如庄子所言:“渊默而雷动。”在无言的深渊中有惊雷滚动,这是一种无言的审美飞跃。《二十四诗品·典雅》写的就是一种无言之境:“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2]P125在惠风和畅、竹影依依的背景下,佳人士子如秋菊般恬静自适,在无言独会中饮领自然冲和之气,心灵皎洁如月,以一颗平常心去印证万物,这是对无言之美的极好概括。“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无言之美,被作为最高的美、绝对的美,无言之境,是人去除外在干扰所切入的幽深生命体验境界,是在非知识、非功利的浑然忘我之境中所体悟的生命飞跃。”[3]P134
“中国哲学重在生命,西方传统哲学重在理性、知识。中国哲学是一门生命哲学,它将宇宙和人生视为一大生命,一流动欢畅之大全体。”[3]P2所以,远在古希腊的时候,当西方哲学家戮力向外追求、开拓,极力探索新识,发掘理性奥秘,“中国圣哲们则提倡‘反己之学’,强调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强调生命的超越。”[3]P3因之,中国哲学是生命的、体验的、向内的,注重心灵感悟的。当孔子说“予欲无言”,弟子问:“先生不言,何以领教?”孔子答:“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兴焉。”老子说“大音希声”,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指的都是无言之境。不言之美,它无需外在观照者的“审美”而获得,而以自身的存在言说,以自身存在的意义显示自身的美。这样的美,只能通过体验和妙悟而获得。
中国古典诗词中有诸多“无言”之境,它们所传达出的“无言之美”很值得品读。如李煜的“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沦为亡国之君的李后主,仰望“年年望相似”的明月,俯瞰已经易主的万里山河,他能说什么呢?他懊悔自己的纵情声色、不理朝政吗?他痛恨北宋政权的强取豪夺、取而代之吗?贵为天子的他瞬间沦为阶下囚,巨大的落差让他发出“天上人间”的慨叹!他内心的纠结和所受的屈辱岂能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又岂是我们凡夫俗子读得懂的。因此,还是“无言”吧。但我们依稀看到一个潦倒的昔日帝王倦怠的身影、沉重的步履、恍惚的神情,在默默的、孤独的、登上高高的西楼,俯仰于天地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辛弃疾的“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满腔报国之志,却苦于报国无门,可惜这一身肝胆的“辛侯”!当无忧无虑的青春年少还在“为赋新辞强说愁”故作姿态时,他眼看国事日非,却无力回天,多少感慨、多少悲怆,只化为淡淡的一句:天凉了,秋天到了!有过风雨经历的人会读懂,“天凉”不仅仅是自然界的秋天到了,也暗含人生之秋意浓、日西斜、“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等言外之意。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琵琶女“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较之前文“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更令人遐想、揣测、猜度:究竟此女有怎样的过往?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末二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并未直言诗人心绪,但一种凄凉的惜别之情却见于言外,余音袅袅。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似乎无一所指,却又无所不指。与《二十四诗品·悲慨》中“壮士抚剑,浩然弥哀”默然相契。李白的《怨情》:“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这个美人不言不语,只是暗自垂泪,但读者却隐隐听到了什么。
唐圭璋说:“此首(《江城子》)为公悼亡之作。真情郁勃,句句沉痛,而音响凄厉,诚后山所谓‘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也。”[3]P298其评价可谓力道十足,真如“霹雳悬停”,有“振聋发聩”之效。然笔者惟感耳膜胀痛,轰鸣作响,更无所言听,无所记取,正如老子所说“五音令人耳聋”。还是苏轼“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让我倍感“余音绕梁”、“三月不知肉味”,其凄美之境、不言之美,弥漫开去,让人欲罢不能,“沉醉不知归路”。
2.意境之美
林纾的“境者,意中之境”,梁启超的“境者,心造也”,王国维的“境非独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境界”等等,以上所说的“意境”都与“人”密不可分。张世英说:“我们说的‘意境’或‘心境’、‘情境’,这些词里都既包含有‘境’,也包含有‘心’,‘情’,‘意’,其实都是说人与世界的交融或天人合一。”[4]P199《淮南子·修务训》则有“见无外之境,以逍遥仿佯于尘埃之外”的说法。“‘境’已不再是物理空间的指称,而是人的精神和心理世界的表现。”[5]P270苏轼在《徐州莲华漏铭》中说:“盖以为无意无我,然后得万物之情。”[6]P81是说作家要在创作中必须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把我融入自然,万物一体,才能与造物者游。如此造出的意境不再拘泥于字里行间,不再局限于有限时空,它能够超越语言层面,呈现无限广阔的意义世界。意境作为一种审美标准,除了具备意象“情景交融”的特点,还需具有内容的包孕性、思致的深刻性,而且必须有“味外味”。叶朗先生在论意境时,强调“意境”必须具有哲理性意蕴。他说:“所谓‘意境’,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即所谓‘胸罗宇宙,思接千古’,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一方面超越有限的‘象’(‘取之象外’、‘象外之象’),另方面‘意’也就从对于某个具体事物、场景的感受上升为对于整个人生的感受。这种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就是‘意境’的意蕴。”[7]有余味、耐咀嚼,有一种难以言传、回味悠长的美感特质,因为难以言传,又体现它的丰富性,多义性,即无限可能性。司空图提出“韵味说”,即“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二十四诗品》的批评方式可称为‘境界式批评’。”[2]P136因为在《二十四诗品》中,所表达的诗学思想是通过象以及象与象之间组成的关系来营造一种独特的画面氛围(意境),然后通过这一画面传达出它所要表达的情思、意绪。因此,它的最终落脚点不是意象或意象群,而是一个浑然一体的“意境”,如“雄浑”,如“高古”。
苏轼《江城子》营造的意境是“凄凉”:这是一个凄婉渺茫的梦境,为沉淀了十年的情感寻到的一个宣泄的出口,那凄清的月色、凄寒的孤坟、凄凉的孤独、凄冷的追念,“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相思相念以及“对青春沉没的纪念已镂刻在不思难忘的潜意识之中”[8]P141。这是怎样的思念啊!且看当代流行歌曲《寂寞是因为思念谁》中的描述:“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冷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颗流成热泪。”原来这相思之泪,需用心底的热血为之解冻,使之滴落。然而,“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是怎样的意境啊!当真见了面,却已物是人非,无从相认。这是何等的悲凉?彻骨的,绝望的。从先前的有所寄托、有所期盼,到梦想成真,反而形同陌路,沧海已变成桑田,因为“尘满面,鬓如霜”,所以你“不识”我。泰戈尔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据《一颗开花的树》演绎的《三生石》更是让人肝肠寸断:我在佛前苦苦求了五百年,如何让我在最美的时刻遇见你,一世、二世、三世,而你却“无视”地走过。难怪席慕容在结尾写道:“……而当你终于无视的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 朋友啊 那不是花瓣 是我凋零的心”。中国艺术善于营造意境,意境一旦生成,既不为创造者所独有,也不会被鉴赏者所穷尽,它是一个永恒的、可咀嚼、耐回味的意蕴空间。“纵使相逢应不识”这一意境,纵然隔着几千年的历史帷幕,仍能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引发人们无尽的感伤情怀。
“小轩窗,正梳妆”是梦境中一个比较具象的描写,但同时又显得朦朦胧胧,辨认不清。我们只隐约看到一个女子,端坐在梳妆台前,用心描画,细细匀粉,那熟悉的背影、秀美的身姿,还和生前一样……此“景”融着词人无限“情”,此“境”又蕴藏词人无尽“意”,所以读来分外感人。结尾三句“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写梦醒后词人自忖:她若地下有知,在那故乡的短松冈上,孤坟一座,月明之夜,一定倍感凄凉吧?这里和“千里孤坟”遥相呼应。整首词结构严谨,上片写入梦前的相思,下片写梦中相逢与梦醒默念,全词构成了一个浑然一体的意境,鲜活真切,如在目前。
3.永恒之美
苏轼这首《江城子》因其悼念之情真挚恳切,感人至深,成为千古名篇,与贺铸的《鹧鸪天》并称为北宋词坛“悼亡双璧”,历来为人称颂,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与价值,具有“永恒之美”。
(1)这首词使苏轼在词坛不再以单一豪放词示人,而呈现出其多样化的创作风格,因此更显得异峰突起,不可匹敌。这首《江城子》,其感情婉转节制、一唱三叹,像春蚕吐丝,又似幽山流泉,其情思绵密,悠悠曲曲,欲说还休,“不以使事用典取胜,不以锻炼词句生色,纯以平常语出之,却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1]P181,凭其情深意浓、“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词风,即便立足于婉约词中也毫不逊色。苏轼在文坛的地位,也许与这首词的关系不大,它的价值并不值得特别称道,但却正是这首词,让人们把苏轼不仅仅看作一个“旷世奇才”,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他也有情有义,也有相思之苦,也有潸然泪下。此时的苏轼,不再是我们高山仰止、可望不可及的“古代先贤”苏轼,而是一个可亲可敬、可怜可叹的“寻常人”苏轼。从这个角度看,苏轼的“存在”是立体的、丰满的,更是永恒的。
(2)该词使人们记住了一个叫王弗的女人。王弗,苏轼的第一任妻子,之后苏轼的生命中还有第二任妻子王闰之、第三个女人即侍妾王朝云。她并非他的惟一,但在她亡故十年之后,他依然满怀悲切写下了这篇悼念之词,其情其状溢于言表又言说不尽。现代诗人臧克家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里体现了中国人观念中有一种超越时间的思想,即“荣落在四时之外”。“就是悬隔时间,截断时间之流,撕开时间之皮,到流动的时间背后,去把握生命的真实,拷问永恒的意义,思考存在的价值。”[3]P185在时间的帷幕下,映现的是人的具体活动场景。每个人都是从生到死一路走来,任由岁月变迁,历经人世沧桑,被无情的时间裹挟着前行,偶尔揽镜自照,惊叹容颜蹉跎了岁月。人们很容易被时间所驱使、所碾压,成为时间的奴隶。我们习惯用时间来计算“效率”、“产出”、“业绩”等等,而这时,人生在世的本真意义却悄然遁逃了。比如时间可以衡量生命的长度,却无法赋予生命以密度;时间可以测量人生在世的长短,却无法估量人死后的意义与价值。从这种意义上观照王弗的死亡,显而易见:她还活着,她不曾离去,她始终活在苏轼心中,她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都在他心底生了根,现世界一点点的触动都会令其发芽吐丝、重获生机,这就是爱的火种、不死的精灵。而且,因了苏轼的追悼,苏轼的词作,也让无数读者认识了王弗,知道她曾经“存在”过,而且她一直“存在”着,只是存在的具体形式发生了变化而已。于是,她超越了有限的生命,超越了时间的界定,走向了无限,走向了永恒。
(3)作为北宋词坛开风气之先的大才子苏轼,在思想意识上也引领潮流,在他这首悼亡词中所体现的“尊重女性”意识,具有独特的超前意识。遥想宋朝,“理学”盛行,程氏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将女性死死束缚在“夫权”统治之下,女子依附于男子生活,是男子的附属品,男子可以三妻四妾,而女子则必须恪守礼教,即使对自己共侍一夫的其他女子也不能稍有“嫉妒”之心,否则就可能遭到“被休”的严重后果。《宋刑统·斗讼律》规定“妻比夫在法律地位上低两等”。在这样极端“男尊女卑”的意识形态统治之下,大多数“妻”以屈从的姿态“存在”,以求得“夫”的垂怜换取现世安稳;而“夫”也以其特有的生杀大权任意奴役“妻”,不予“妻”以对等的人格,更谈不上爱和尊重。而苏轼对“妻”却另眼相待。苏轼在《亡妻王氏墓志铭》记载:“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9]王弗,是以一个独立的“妻”的姿态“存在”,从而赢得了丈夫由衷的爱与尊重,也获得了身为女性存在的人性的尊严和人格的独立。苏轼“尊重女性”这一先见之明,也在后世中不断得到传扬。
[1]周先慎.古诗文的艺术世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朱良志.中国美学名著导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朱良志.中国美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张世英.天人之际[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毛宣国.中国美学诗学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叶朗.说意境[J].文学研究,1998,(1).
[8]杨义.中国古典文学图志[M].上海:三联书店,2006.
[9]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