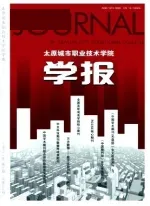“软法”非“法”——以《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为例
2013-08-15段明
段明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广东佛山 528000)
所谓软法,通常指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硬法)对称,即趋向于形成而尚未形成的规则和原则。关于软法的概念,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其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可能产生实际效果的行为规则;还有人认为,其是以文件形式确定的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却可能具有某些间接法律影响的行为规则;我国徐崇利教授则认为,(国际经济金融)软法一般表现为弹性的“标准”,而非具体“规则”,并无强制实施的效力,但其硬效果却不容忽视。虽然法理学对软法的研究方兴未艾,然而其法律性质是值得怀疑的。软法的出现容易混淆法与其他行为规范(norms)的关系,忽视对一般行为规范发生法律效力途径的研究,是多余而无益的。现有对软法的研究限于法学理论上的基本架构,不免流于泛泛,论文具体以《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下简称“《通则》”)这一合同领域著名的国际文件为例,分析其性质以及发生法律效力的途径,进而得出“软法”非“法”这一结论。
一、《通则》的基本情况
随着国际商贸活动的深入发展,跨国合同领域的当事人越发需要一套统一公正的交易规则来调整他们之间的经济往来关系,而现有的法律体系无法满足国际商事领域对同一交易规则的需求。力图通过以非立法的方式协调现有各国法律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先后三次通过了三个版本的《通则》。《通则》的适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截止到2010年底各国法院和仲裁庭已经在至少223起案件中主要或部分地适用了《通则》。以下结合官方评论(Official Comment)的内容,就 2010年《通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作简要的说明。
《通则》目标在于制定一套可以在世界范围内适用的均衡的规则体系,而不论它们被适用的国家的法律传统和政治经济条件如何。由此可知,《通则》旨在为国际商事活动提供统一的一般规则,并在序言(preamble)中将《通则》的目的具体分为六个方面:1.在当事人约定其合同受《通则》管辖时,应适用《通则》。2.在当事人约定其合同受法律的一般原则、商人习惯法(lex mercatoria)或类似规则管辖时,可适用《通则》。3.在当事人未选择任何法律管辖其合同时可适用《通则》。4.可用于解释或补充国际统一法文件。5.可用于解释或补充国内法。6.可作为国内和国际立法的范本。
考虑到现有的各国的国内法和国际公约适用范围的局限性,《通则》尽量扩展自己的适用范围。《通则》对“国际”和“商事”等词语均未明确定义。结合其官方评论的内容,一般认为《通则》中“国际”的外延十分广泛,只要合同不是根本不含国际因素或不是所有因素都和一国有关,即认为该合同具有国际性。同样,《通则》对“商事”的界定也与传统国内法不同。《通则》中的商事并非照搬某些国内法律体系尤其以大陆法系国家对“民事”和“商事”的传统分类,也并不依赖当事人是否具有商人的身份或者交易具有商事性。《通则》只是排除了消费者合同的适用,而尽可能地将各类交易合同纳入调整范围中。除了适用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外,还适用于如投资、特许协议、专业服务等其他经济交易合同。
二、《通则》不具有法律的地位
所谓“法律”,是指国家制定、认可的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体系。法律由国内法和国际法组成。国内法指一个主权国家的特定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并在该国主权所及范围内适用的法律。可见,国内法有两个特征:一是由一个主权国家的特定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二是在该国主权所及范围内适用。由《通则》的引言可知,《通则》的制定人员包括各国的高级法官、公务员都仅以个人身份参与起草活动,而并不代表任何国家制定《通则》,而且它的适用范围也不局限于任何特定国家。《通则》不符合国内法的特征,因而原则上不是国内法的一部分。
《通则》是不是国际法呢?所谓国际法,指在国际交往中形成的,主要用以调整国家间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各种原则、规则、规章和制度的总称。它的法律渊源主要有国际公约和国际习惯两种。国际公约是指国际法主体间依国际法所缔结的据以确定其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书面协议。可见,国际法最主要的特征是只有国际法主体之间才有资格缔结。协会是由它的成员国通过缔约建立的,作为国际组织的它本身也是国际法的主体,在它的设立宗旨的范围内有缔结条约的权利。但无论如何,协会单方面作出的规范性文件不是国际法,不但不能约束非成员国,亦不能规制它的成员国。所以,《通则》不是国际条约的一部,《通则》也不是国际习惯。国际习惯是指各国在反复实践中形成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被接受为法律者。因此,作为国际习惯必须具有以下两个条件:(1)通例之存在,即各国对某种事项长期重复地采取的类似行为,而且这种行为只能是各国在国际交往中采取的公法行为,也称为国际习惯的“物质因素”;(2)通例被各国确认具有法律约束力,也被称作“心理因素”或者“法律确信”。《通则》调整作为平等民事主体的国家、国际组织、自然人、法人间的跨国财产流转关系,并不仅仅调整国家间的关系。而且参与跨国财产流转关系的国家是以民事主体身份而非行使国家主权的国际公法主体身份出现的,所谓的商事交易行为也只是私法行为。因而在该情形下是不能产生国际习惯的要件之一国际通例,更遑论被各国确认具有法律约束力。正如现代意义的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原则是各国公认的国际习惯,但国家在从事国际商事交易时是不能享有豁免一样,宣示合同法一般原则的《通则》不构成国际习惯。
三、《通则》发生法律效力的各种方式
《通则》虽然不表现为法律,但不意味着它不能在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况下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实际上,正确理解《通则》序言对于《通则》目的的说明,可以发现《通则》通过多种途径发生法律效力。
(一)通过立法或司法行为为法律所吸收
如序言所言,《通则》可作为国内和国际立法的范本。《通则》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可以成为商事性国际条约或是国内法的重要参考资料,在适当的时候可能被国际条约或是国内法所吸收,成为据以调整跨国财产流转关系的法律的组成部分。此时通过立法的方式而为法律所吸收的《通则》也不是法律的渊源,而只是法律的来源。法律渊源是指法的表现形式,而非简单的法的来源,即法由何种国家机关所制定、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具有何种法律效力。此外,如序言所言,《通则》可用于解释或补充国内法,此种解释多通过司法的方式予以采用,而法官或仲裁员这种解释权限是各国民事诉讼法或仲裁法所赋予的,同样不是《通则》法律效力的当然所在。
(二)通过法律的一般授权性规定取得法律的地位
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通则》通过法律的一般授权性规定而在个案中取得法律的地位。如国内法规定在没有法律或国际条约时处理当事人之间的合同争议,可以适用《通则》。那么,法院可以在法定的条件下,援引《通则》作为该案所应适用的法律来处理当事人间的纠纷。如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规定,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适用国际惯例。如果我国法院将《通则》视为民商事领域的国际惯例,则可以在个案中补充我国法的适用。此种适用虽然在《通则》序言中没有规定,但在官方评论“《通则》的其他用途”中予以确认,即《通则》可以在国内法难以确立或证实的情况下作为国内法的替代而适用。
(三)通过当事人明确约定并入合同
《通则》可以通过当事人明确并入合同的方式而依法产生法律效力。《通则》如果被当事人并入到他们签订的合同中,出于各国私法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及在不违反强行性法律的前提下,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应当按照合同中的规定,依照当事人选择的《通则》确定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进而解决他们之间产生的争议。此时,《通则》因为当事人的选用而作为法律行为内容的一部分,能够产生、变更、消灭当事人的民事法律关系,这种效果必然是法律赋予的。对此,官方评论在“《通则》的其他用途”中认为,《通则》可以作为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指南。
(四)作为合同默示条款弥补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不足
在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的情况下,《通则》可以弥补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不足。在私法自治理念的引导下,现代合同法所包含的任意性规范的本身就具有弥补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不充分、不确定的作用。但是,与为当事人所知悉的并为该交易领域所广泛适用的《通则》相比,合同法中刚性规定的适用未必适当。因此,合同法往往规定在当事人可以自行处分的权利范围内,如果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可适用于交易的惯例。此时,《通则》扮演着合同默示条款的角色,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弥补意思表示的不足。当然,《通则》在具体案件中是否具有交易惯例的地位还是由裁判者根据法律来认定。此外,《通则》还可以作为“法律的一般原则”、“商人习惯法”或在合同中所指类似措辞的形式来适用。官方评论认为,当事人指向内容不确切的超国家或跨国性质的规则或原则的做法一直饱受批评,原因在于这种概念极其模糊。为了避免或尽量减少使用此类模糊概念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求助于《通则》此类系统、完整的规则体系以确定它们的内容是可取的。此时,《通则》同样是作为合同默示条款的一部分而适用。
(五)通过在仲裁中选用成为个案争议解决的依据
《通则》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可发挥较大的作用,因为国际商事仲裁的各种规则赋予了合同当事人在解决纠纷过程中相当大的自由空间,《通则》可以作为解决个案争议的依据。一般认为,在法律选择条款和仲裁协议结合的情况下,由于国际商事仲裁中当事人才有权选择某国的原则或规则作为解决实体争议问题的依据,故而此时《通则》作为合同准据法而适用。
对此应正确理解《通则》的规定。《通则》认为,在仲裁中当事人可以选择《通则》作为准据法,甚至在合同没有对准据法作出规定时,《通则》也可予以适用。官方解释认为,传统上当事人自由选择管辖其合同的法律限于国内法,因此当事人对《通则》的选择适用通常会被认为是仅同意将《通则》并入合同,而管辖合同的法律仍得依据法院地国际私法规则来加以确定。结果是《通则》只在不影响那些当事人不可以减损的适用法规则的范围内才能约束当事人。如果当事人同意将合同项下产生的争议提交仲裁,情况就会有所不同。仲裁员没必要受某一特定国内法的约束,如果当事人授权仲裁员作为一友好的调解员或公正行事,这一点就不言自明。但即使在没有这种授权的情况下,一般允许当事人选择“法律原则”而非国内法作为仲裁员裁决的基础,甚至允许仲裁庭适用“他们认为适当的法律规则”。正确的理解是,此时将《通则》视为合同“准据法”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仲裁不同于审判,它的自治性决定了裁决不需要援引各国实体法作为裁决理由,所谓仲裁所适用的“法律”只是说《通则》在仲裁中选用成为个案争议解决的依据,不代表它是经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律。
四、《通则》与“软法”非“法”
从《通则》的性质和发生效力的途径而言,软法并非法律,而是那些能够根据各国法律的规定发生效力的行为规范。软法的概念容易引发歧义,混淆法与非法的界限,甚至忽略《通则》之类的规范发生法律效力的具体途径,从法理上讲,是多余而无益的。
(一)“软法”非“法”的根本原因
从对《通则》性质的分析可以看出,“软法”非“法”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软法缺乏国家意志。所谓国家意志体现在法律由国家的权力机构制定并实施,而软法最大的缺陷在于将合同范本、交易习惯等不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范认为是法律,忽视了法律的国家意志性。国内法是一国意志的体现,国际法是各缔约国协调意志的体现。国内法需要由国家权力机关按照一定的程序制定和认可的,在一国范围内法律具有最高效力,并由国家机关保证强制执行。国际法是平等主权者的约定,对缔约国具有约束力。国际法的违反体现为国际责任的承担,主要表现为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报复或制裁,实施的主体同样是国家。《通则》即非由一个主权国家的特定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又非各国协调意志并确信其为法律的体现,缺乏国家意志,故而不构成法律,当然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
(二)“软法”可以在法律认可时产生法律约束力
从对《通则》发生效力的方式可以看出,软法非法律,但软法完全可以在法律认可时产生法律约束力。首先,软法通过立法或司法行为为法律所吸收,通过立法或司法机关“造法”或“释法”这一过程可以“硬法化”。其次,软法可以借助法律的一般授权性规定取得法律的地位。此时,软法通过法律预留的渠道纳入到法律体系当中,在个案中具有法律的地位和效力,成为司法裁判的依据。再次,软法可以通过当事人明示或默示的意思并入合同当中,具有合同一般条款的地位,在不违反强行法的情况下,发生意思表示而生的法定约束力。最后,就仲裁这种特殊的争端解决机制而言,软法在当事人授权或仲裁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作为本案仲裁员解决个案争议的依据,从而使得以此作出的裁定根据各国的民事诉讼法或仲裁法发生承认或执行的效力。
(三)将“软法”视为“法律”的不当之处
软法理论建立在不可靠的假定之上,只有在国家实践与司法实践中找到孱弱的支持。软法理论存在相互冲突的问题,其最复杂的理论借口摇摇欲坠。将“软法”视为“法律”,不仅容易混淆法律与其他行为规范的界限,而且容易使人忽略《通则》之类的规范发生法律效力的具体途径。如果将“软法”等同于“法律”,则不免将非法律规范当做法律,不仅为法理所不容,而且会发生一系列适用上的困难;如果认为“软法”的“法”不同于“法律”之“法”,而只是一些可能会依法发生效果的其他规范,或“软法”虽然是法但不是一般意义的法,却是非典型意义的法 (非严格的法),则何必使用此种引人误解的表述,进而可能忽视上述《通则》之类具有法律价值的行为规范发生法律效力的各种途径。总之,有必要摒弃这一不科学的概念。
[1]魏武译.冗余的软法[J].行政法学研究,2008,(2):133.
[2]姜明安.软法的兴起与软法之治[J].中国法学,2006,(2):28.
[3]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58.
[4]徐崇利.跨政府组织网络与国际经济软法[J].环球法律评论,2006,(4):416-417.
[5]罗豪才,毕洪海.通过软法的治理[J].法学家,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