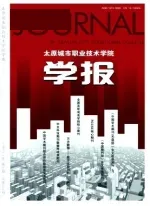论2 0世纪初期的“新史学”思潮
2013-08-15王标
王标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福建 福州 350001)
一、“新史学”思潮的主要特点
2 0世纪初期形成了“新史学”思潮,由梁启超等人倡导“新学史”。“新史学”思潮最大特点之一,就是表现出了强烈的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意识。这不仅明确反映在梁启超写的《新史学》和其他相关论著中,而且还反映在同时代其他一些人撰写的著述里面。对旧史学的批判已经成为“新史学”的标志性特征。新史学批判旧史学的真正矛头,指向的是对当时的旧制度、旧政体,批判旧史学的实际意图,是激荡起广大人民的爱国之情,保家卫国,奋发图强。因此,“新史学”的强烈批判意识,其政治意义大于学术意义,现实意义大于历史意义。
二、“新史学”思潮的形成
梁启超的《新史学》等著述对中国史学转型的首倡之功是不言而喻的,他所说的“新史学”在当时立即得到了许多人的相应。刘师培于1904年在《警钟日报》上发表题为《新史篇》的文章,陈述古代史学“魏晋以上史臣操监督政府之权,魏晋以下政府操监督史臣之权”的变化,亦指出“中国之所谓历史者,大约记一家一姓之事耳”,遂提倡撰著“新史篇”。曾鲲化的《中国历史》被称之为“新历史的旗帜”。“新史学”的倡议获得认同,并不等于人们在所有的观点上都一致。譬如,身为改良派的梁启超所坚持的是“大民族主义”,他说:“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这与主张“排满革命”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在民族观念上存在有很大差异。反映在史学中,怎样看待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的作用,尤其是如何看待满族统治者及清朝的历史地位,双方都存在着争议。与此相关的历史纪年问题,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中主张以孔子纪年,而刘师培在排满革命高涨的1903年发表《黄帝纪元论》一文则强调,“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主张黄帝纪年,既否定以历朝君主年号纪年,也否定以孔子纪年。
1902年2月,邓实、黄节在上海创办了《政艺通报》,以介绍西学和宣传国粹为主,认为“国必有学而始立,学必以粹为有用,国不学则不国,学非粹则非学,非学不国,其将何以自存矣。”1905年2月,上海国学保存会的机关刊物《国粹学报》创刊,总纂邓实、章太炎、刘师培、黄节等人是其中坚和主要撰稿人。《国粹学报》旨在保存“国粹”,避免使中国文化成为腐朽的清朝统治者“种族专制”的陪葬,以此服务于“排满革命”;又宣称“吾国之言国粹也,与争科学”,“国学,当首经史”,“国粹以历史为主”。既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又“争科学”、讲历史,这对于政治取向很不相同的学者名流来说,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够接受。
三、“新史学”思潮的学术建树
中国通史撰述在传统史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以撰写中国通史来实现“新史学”的宗旨,首先涉及的问题就是怎样看待中国的旧史学。在重订本《书·哀清史》中,章太炎对正史二十二史作了带有肯定性的评价:“唐氏以上,史官得职,若吴兢、徐坚之属,奋笔而无桡辞。宋、明虽衰,朝野私载,犹不胜便牒,故后史得因之以见得失。作者虽有优拙,其实录十犹四五也。”即使是宋以后的正史,也有可取之处。他还评论《通典》《文献通考》“是近分析法矣”,《读通鉴论》《宋论》“其法亦近演绎”,杜佑史论“简短”,马端临则“持论鄙倍”,王夫之史论“雅驯”,但“辞无组织”,钱大昕、王鸣盛等乾嘉诸老的历史考证学有“味其本干,攻其条末,岂无识大,犹愧贤者”的不足等。所论虽有可商榷之处,但大致较为客观,至少不是完全否定的态度。希望新型的《中国通史》“皆在独裁,则详略自异,欲知其所未详,旧史具在,未妨参考”,“苟谓新录既成,旧文可废,斯则拘虚笃时之见也已。”说明他仍然看重古代史学的可借鉴之处,要求《中国通史》“皆在独裁”“详略自异”,则古代史学成就“未妨参考”。
章太炎列出的《中国通史》,包括“表”5篇、“典”12篇、“记”10篇、“考纪”9篇、“别录”25篇,计61篇。诸体所出,均来自或借鉴传统史体;诸体所出,均来自或借鉴传统史体;诸篇所设,又多显时代新意。
提出撰写新中国史计划的还有陈黻宸,他在1902年《新世界学报》上发表的《独史》一文中建议:“自五帝始,下迄于今,条其纲目,为之次第,作表八、录十、传十二。”“十录十二列传,皆先详中国,而以邻国附之,与八表并列,盖庶乎亘古今统内外而无愧于史界中一作者言矣。”
从体裁体例上看,章、陈二人的通史方案有着很多的相同之处,他们更多的是继承了传统史书的体裁形式。他们都十分重视“表”,将“表”列在史书的首位;传统史学的书志部分也为他们所继承,分别称为“典”、“志”或“录”;人物传记依然是篇幅最大的部分,章太炎以“考纪”记帝王、以“别录”记其他历史人物,陈黻宸则将各类人物均置于“列传”中。主要不同处在于,章太炎加入了记事本末体,称为“记”,陈黻宸则无,显得章的体裁更丰富;章在传记部分仍然区别出“考纪”和“别录”,陈则将人物统置于“列传”中,显得陈更具平等的历史眼光。从设置的篇目上看,章、陈二人都力图体现新的历史观念、新的历史内容。如陈的“平民”诸表,章将洪秀全列入帝王“考纪”,反映了对“民史”的重视和对农民起义的不同看法。章的革命记、陆交记、海交记等,陈的邻国疆域表等,则表现出近代来新的历史内容和更为开阔的历史视野。
“新学史”思潮以指斥旧史学为帝王家谱、有君史无民史,宣传史学的爱国意义和社会功能为发端。伴随于激烈批判旧史学的言辞,“新史学”怎样去建设,这个问题到目前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讨论,稍能表现“新史学”实施步骤的主要是撰写新型中国通史的讨论和筹划,并且在三两年后即撰写出了几部教科书式的新型中国史书,而此若干建设“新史学”的实绩也未能得到后人的充分重视。平心而论,“新史学”思潮的总体走向是对旧史学的“破坏”和“新史学”的建设,相比之下,2 0世纪初期的“新史学”思潮在“破坏”方面的影响远大于建设。如上所述,正是由于“新史学”的强烈批判意识和提出建立中国“新史学”的号召,才使其成为中国史学转型的“宣言”。然而,对于2 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对以后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还应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与评价。
如从学术方面来看,“新史学”带给近现代中国史学有价值的遗产,是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努力和撰述新型中国通史的尝试。2 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关于“新史学”的很多问题的研究,包含很多方面,例如涉及历史认识论和历史观等内容,这些迥异于传统史学的理论阐述,使中国的“新史学”开始具备了现代史学的内涵和特色,也使“新史学”思潮的学术生命力得以不断延续。何兆武认为:“严格说来,中国近代的史学思想是到了梁启超的手里才正式奠定的。”难能可贵的是,梁启超一直探索这方面的问题并进行深入研究。“新史学”思潮的发展在随后几年与复古思潮的较量中暂时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在五四时期以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著述为标志,“新史学”以更为全面和成熟的理论建树再次风靡一时,其影响所及持续至今。
2 0世纪初期的“新史学”思潮的许多方面为五四时期史学所继承和拓展,五四时期史学的发展不仅在多个方面扩大、丰富、深化并改变了“新史学”,而且五四时期史学就是“新史学”发展路向的延伸和继续。
[1]姜莹.梁启超“新史学”观念生成论析[D].东北师范大学,2006.
[2]何兆武.略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A].历史理性批判论集[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603.
[3]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J].史学史研究,1982,(3):14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