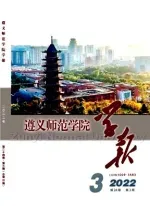戊戌变法前后慈禧太后的心态变化刍议
2013-08-15邓运山
邓运山
(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长期以来,慈禧太后在史学界一直是作为一个封建、顽固、守旧的形象代言人,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后人的心目中,慈禧一直是一位心胸狭窄、卖国求荣的皇太后,是一个抱残守缺、顽固不化的封建卫道士。但近些年来,学术界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的态度,对慈禧进行了重新评价。也就是说,尽量把慈禧放在奔腾的历史长河中进行综合考察,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剖析她内心复杂的多重心理,从而还她在历史上的本来面目。
史学界对慈禧的重新评价主要表现在她对晚清变法的态度方面。就慈禧对晚清改革的态度来说,史学界对她在洋务新政、清末新政以及她睁眼看世界等方面都基本持肯定态度,但是,对她发动戊戌政变,镇压康梁维新变法的铁案则基本上还是没有改变。对此,笔者认为,这是学术界只重结果、不看过程的表现,认为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扼杀变法,那她顽固派的标签就贴定了。其实,慈禧太后在戊戌变法前前后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她对变法都是持默许和支持态度的,甚至说在她发动戊戌政变时,也并没有反对变法本身。在此,本人不揣浅陋,略谈自己的一己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变法之前,慈禧基本默许、支持光绪帝领导的康梁维新变法
十九世纪末,堂堂大清帝国败在一个“蕞尔小国”的手上,这无疑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国人对清政府的失望情绪降到了极点,民族意识空前觉醒。“世间无物抵春秋,合向沧溟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1]p89。人们在困惑、怀疑、愤怒之余,开始把矛头对准最高统治当局,以发泄心中的不满,社会舆论也强烈地谴责部分因循守旧的朝中大员。一些思想较为激进的知识分子甚至对千百年来国人津津乐道的制度文化开始提出质疑,他们冒死向当权者请愿,要求进行制度改革。“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着,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方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阙制,变亦变,不变亦变”[2]p15。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利用人们在甲午战后表现出来的强烈民族主义情怀,竭力呼吁维新救国,从而使变法成了一种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的时代潮流。在当时那种民族危机、国事日非的情况下,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光绪皇帝深受维新派的影响,立志革新图强。同样,作为帝国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又岂会无动于衷呢?故当光绪准备重用康、梁师徒着手进行维新变法的时候,慈禧出于维护自己最高统治地位的需要,也还是持默许和支持态度的,不可能反对变法。“时帝颇流览新书,见刘瑞芬《英法政概》,宋育仁《采风记》……。遂为后言,徒练兵制械,不足以图强,治国之道,宜重根本。乃以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进后览,后亦称其剀切,第戒帝勿操之过蹙而已。帝以告同禾,同禾退告其门弟子曰:今而后法必变矣。”[3]p464《慈禧传信录》里的这段话就充分说明慈禧太后一开始还是很认可光绪皇帝的变法想法。因此,还在戊戌变法之前,慈禧就曾多次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变法启动后,她特地叮嘱光绪说:“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3]p464甚至慈禧曾明确无误地对光绪说:“你(光绪)只要留下祖宗的神位不烧,发辫不剪,别的我就不管了”[1]p26。由此看来,光绪领导的康梁维新变法在最初开始时,慈禧太后对变法基本上是持默许和支持态度的。
另外,之所以说变法之前慈禧并不反对光绪皇帝主持的维新变法,这从当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权力归属来看,也是合乎逻辑的。虽然从1887年开始,慈禧就已经归政于光绪,但是大清帝国的真正权力还是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光绪亲政伊始,醇亲王奕譞等权贵就定下了一个规矩,要求朝廷中有关军国政务的奏折,在皇帝批阅之后,要由军机处抄录“恭呈慈览”,这种做法一直延至“百日维新”期间。“德宗既亲政,以颐和园为颐养母后之所,间日往请安,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园中。”[4]p261苏维祖曾在《清廷戊戌朝变记》中指出:“皇上自四月以来所有举办新政,莫不先赴太后前禀白,而后宣示,虽假事权,并未敢自专也。”[3]p342这就意味着康梁维新派主张维新变法的奏折以及光绪皇帝所作的批示,基本上都曾给慈禧太后过目看过。光绪在颁布新政期间,曾十二次到颐和园向慈禧请示,如果得不到慈禧的认可和允许,在权力上名实不符的光绪皇帝是根本没有胆量进行改革的,更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连续颁布那么多的法令。在这一点上,著名史学家胡绳也曾指出:“对光绪皇帝在此期间所发上谕,慈禧没有表示过不同意见,有的上谕,如设商务局,还经过慈禧批示同意。有的上谕是慈禧用光绪的名义发布的”[5]p55。因此,长期以来,“光绪皇帝和慈禧个人之间的矛盾被夸大了,其实,在国家大政方针上,慈禧和光绪母子基本上是一致的,至少戊戌新政的主要措施都是她们一起决定的。”[6]p99
二、变法之中,慈禧提倡渐变,反对急变,强调政局稳定的重要性
尽管在光绪皇帝重用康梁维新派着手准备变法之时,慈禧太后基本上持默许和支持态度,但是慈禧终究是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对她来说,政局的稳定始终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可是在戊戌变法的过程中,维新派和光绪皇帝却太急于求成了,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策略错误。按康有为的想法:“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实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耳。”[7]p145在康梁的鼓动下,“皇帝下了太多的诏令,在短期内要求各局所冗员,一律裁汰净尽,引起人心惶惶,怨声载道”[8]p8。其实,像这种太过急进的任何制度改革都是很不明智的。因为改革都要牵涉一些个人利益问题,要损害一些人的既得利益,过于激进的改革,势必遭到来自被触及利益方的反对。故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管子就说过:“改变当以渐,民自顺教而风靡,久而服而习之矣。”[7]p304而这次戊戌变法就触了改革的大忌。因此,戊戌变法一开始,部分封建顽固的守旧官僚就从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极力反对变法。“人人都知道废八股,提倡实学,但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全国的读书人都觉得前功尽弃”[1]p75,他们“安肯舍吾数十年资俸奔竞,千辛万苦所得之高官,决然引退,以避贤者之路哉!故反复计较,莫如出死力以阻挠之,盖全国千万数之守旧党人,不谋而同,异嘴同辞,他事不顾,而唯阻挠新法之知。”[2]p185-186因此,他们痛恨康梁维新派,诅骂康有为是“洋奴汉奸”也不足为怪了。正如梁启超所言:“凡年之间,凡七上书,其不打也如故,其频上也如故,举国俗流非笑之,唾骂之。或谓之为热中,或斥为病狂。”[7]p11但这些事情的出现在深谙权力的慈禧眼中也还是正常的,只要不动摇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和她本人的最高统治地位,她还是可以给予光绪皇帝一些权力去继续从事改革的尝试。所以,后来即使光绪皇帝下诏罢黜阻挠变法的礼部六堂官,虽然慈禧太后认为这样的做法不妥,但也还是没有阻挠光绪的下诏。甚至当她身边一帮老臣要求她重新训政时,慈禧竟毫不含糊地加以拒绝。“旧臣惶骇,内务府人皆环跪后前,谓上妄变祖法,请训政,后不许。”[7]p160由此可见,这时的慈禧对维新派也还是持支持态度,对变法也还有足够的容忍度。
尽管慈禧太后对戊戌变法始终有足够的容忍度,但是,像御史文悌、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及侍郎坤岫、徐会澧、溥颋、曾广汉等顽固派官僚,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还是依然反对维新派激进的变法措施。同时,维新人士在实行新政的过程中,大肆排斥宫中太监,使李连英等人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很快宫中的这部分人也成了维新派的对立面。由于这些宫中太监们长期生活在太后的身边,他们深谙慈禧的内心世界和多变的心态,于是,依靠自己独特的身份,联合一些守旧的朝中大臣,搬弄是非,诬陷光绪皇帝,故意向慈禧谎报信息。“庆邸与李连英皆跪请西后训政,立山等至谓上派太监往各使馆,请去西后,西后大怒。”[7]p160至此,慈禧太后对变法的态度就开始发生了改变,这种微妙的变化就连光绪皇帝本人也觉察到了。他在给维新派的密诏中说:“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旧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臣罢黜,而登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7]p418光绪的担心随后就得到了验证,慈禧太后不久严明斥责光绪说:“汝之变法维新,本予所许,但不料汝昏昧糊涂,胆大妄为,一至于此。……朝中亲贵重臣,无一爱戴汝者,皆请予训政,汉大臣中虽一二阿顺汝者,予有法处治之”[7]p261。于是,在晚清帝后两党之间,由变法程度的分歧开始引发了矛盾冲突,随后就愈演愈烈。
戊戌变法时期,帝后两宫之争的最终结果就不用说了,反正戊戌变法最终悲壮地失败了。作为镇压变法的刽子手,一百多年来,慈禧太后至今还在被后人口诛笔伐。其实,如果站在作为政治女强人慈禧太后的立场,从改革和稳定的关系出发,我们还是能够理解她当时的做法。发生在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属于深层次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结合起来,并不是改革越激进越好。“由于传统的力量委实坚固,一旦改革真的从传统的夹缝中打开一条道路,改革本身却又犹如一条脱缰的野马,恣意驰骋,于是改革便走向自己的反面。不仅没有能从根本上为清王朝找到一条发展的坦途,反而使清政府因改革而陷入空前的危机状态中。”[1]p172维新人士太多书生意气,光绪又是一个政治上很不成熟的封建帝王,他们仅凭自己的一厢情愿和满腔热情发动维新变法,巴不得把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来要做的事情在一百天之内全部做完。由于维新派的不成熟,使得事与愿违,造成整个社会人人恐慌、谣言四起,严重地危及了封建官僚机构的稳固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别无选择,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决然中断变法。英国公使窦纳乐于政变发生20天后曾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上说过:“我认为中国正当的变法,已大大被康有为和他朋友们的不智行为搞坏了。”还有上海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转述北京外交使馆对百日维新的看法是:“维新党的计划是不合实际的。光绪皇帝可能把中国弄得不成样子,太后是宫廷中唯一头脑清晰的人,而她的及时干涉是有裨于时局的。”[9]p571
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数不清的变法运动,太多实例证明:激进的改革不一定好,保守的改良也不一定不好。就如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苏两国改革一样,中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期间,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正是邓小平的“保守”,使中国顺利地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取得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功,历史也并不因为邓小平的“保守”而否定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地位。相反,同时在苏联进行的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开始就大刀阔斧,激进有余,结果把苏联这个偌大霸权主义国家都改掉了,以新思维改革自居的戈尔巴乔夫本人也被前苏联人民永远抛弃。19世纪末的清朝也是如此,如果历史能够假设,让戊戌变法任由光绪皇帝和康梁维新派进行下去,也许清朝的灭亡用不着等到辛亥革命的爆发。慈禧太后当时正是从稳定政局和稳定社会的角度出发,来一个紧急“刹车”,发动政变完全是形势所迫。
三、政变之后,论人不论事,反维新“乱党”,不反变法本身
长期以来,史学界认为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反对变法。其实,公正地说,戊戌政变本身并不是顽固派和激进派,保守派和革新派的斗争,而是变法方式或变法程度之争。戊戌变法的关键并不是帝后两党之间要不要变法的问题,其争论的焦点在于:究竟是要推行光绪皇帝的激进式改革路线,还是要坚持慈禧太后温和式的自强新政路线问题。这一点从光绪皇帝曾赐给杨锐的密诏也可以看出,“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10]p91-92从密诏看来,光绪皇帝也明白慈禧太后并不是反对他的变法,只是不同意他推行激进变法的方式方法,即“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老臣尽罢”而已。其实,慈禧太后对变法的这种态度也不为过,康有为当初在被光绪皇帝召见时,也是这么强调的:“就皇上现有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皇上欲变法,惟有擢用小臣,其旧臣且姑听之”[7]p145-146。如此看来,慈禧太后与康有为两人的想法并没有完全冲突,慈禧并没有完全反对变法的意思。
慈禧不但在戊戌政变之前没有反对变法,即使通过戊戌政变重新掌握政权之后,她始终也算不上是一个顽固守旧派,她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百日维新”。如果硬要说否定的话,那也是因为迫于当时封建顽固守旧派的压力,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得不做出的一种姿态。事实上,她在其后颁布的一系列诏书中,议论最多的并不是对新政的否定,而是对康梁“乱党”的极力指责,是论人而不是论事。这一点我们从戊戌政变后的一份上谕(慈禧训政)可以看出:“前因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动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需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用特行申谕,嗣后内外臣工,务当清白乃心,一化新旧之见”。“嗣后大小臣工,务当以康有为为炯戒,力扶名教,共济时艰,所有一切自强新政,胥关国计民生,不特己行者亟应实力举行,即尚未兴办者亦当次第推广,以挽回积习,渐臻上理”[1]p45。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本身并不是反对革新,而是反对当时光绪皇帝和康梁维新派他们的过激做法。
同时,正是由于戊戌政变中的慈禧不是反对戊戌变法本身,我们才更能理解三年后由她亲自发动的那场“清末新政”。清末新政是由慈禧太后亲自发起和领导的,其改革力度之大,波及范围之广,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程度之深,都是三年前的戊戌变法所无法比拟的。改革的内容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国防、文化教育、法制建设、社会公益事业等各个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几乎同时对吏治官制、朝章律令、财政军制、经济民生、学校科举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系统改革,并且进一步从体制内的变革突破上升到对政治体制本身的变革。不言而喻,在整个新政改革过程中,作为清廷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起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因此说,如果慈禧完全是反对戊戌变法的话,那么三年后由她亲自发动的这次“清末新政”,我相信任何人也是难以理解的。
综上所述,在戊戌变法的前前后后,不能简单地把慈禧太后归结为封建顽固派。因为在变法之前,慈禧太后基本上是默许、支持光绪领导下的康梁维新变法的;在变法之中,慈禧提倡渐变,反对急变,强调政局稳定的重要性;在政变之后,她还是论人不论事,反维新“乱党”,而不反对变法本身。因此,笔者认为,就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来说,简单地把慈禧太后归为封建顽固派是有悖历史真相的。
[1]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M].上海:三联书店,2001.
[2]梁启超.变法通议[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3]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4]徐珂.清稗类钞(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J].近代史研究,2001,(1).
[7]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8]王晓秋,尚小明.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0]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