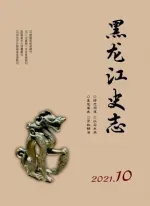明代广东书院发展轨迹初探
2013-08-15孔祥龙
孔祥龙
(云南大学历史系 云南 昆明 650091)
明代广东书院发展轨迹初探
孔祥龙
(云南大学历史系 云南 昆明 650091)
明代是广东书院发展史上一个上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其发展轨迹经历了沉寂—上升—鼎盛—回落四个时期,且与朝廷的文教政策、政治斗争、官学的盛衰和王湛之学的兴盛和有着直接的关系。
明代;广东;书院;轨迹;原因
一、明代广东书院的发展轨迹
明代广东书院的数量,早有学者做过统计,数据互有差异,且相差颇大。随着更多古籍资料被发掘和整理,笔者经过查找和整理了大量文献史料后,做了一次新的考证,得出明代广东书院有282所,各朝书院数如下[1]:洪武朝5所、建文朝0所、永乐朝6所、洪熙朝0所、宣德朝1所、正统朝3所、景泰朝1所、天顺朝5所、成化朝7所、弘治朝11所、正德朝13所、嘉靖朝95所、隆庆朝6所、万历朝66所、泰昌朝0所、天启朝4所、崇祯朝28所,另外年代不详的有31所。明代广东书院的发展轨迹,呈橄榄状,两头低,中间高,经历了沉寂—上升—鼎盛—回落四个时期。
(一)沉寂时期。从洪武至天顺年间(公元1368年~公元1464年)历八朝,共计97年,但此时广东只修建21所书院,只占明代广东书院总量的7.45%,是这四个时期中最少的。沉寂时期的书院之和,只比上升时期的正德朝多8所,但比鼎盛时期的嘉靖朝少74所,比万历朝少45所,甚至比回落时期的崇祯朝还要少7所。沉寂时期广东书院的年平均书院为0.216所,比上升、鼎盛、回落时期都要低,且远远低于明代广东书院年平均数1.018所。沉寂时期各朝书院数量排名最前的是永乐朝,但在14朝建有书院的12个排名中,只排在第7,没有一朝进入前六名。无论是总数,还是年平均数的排名,沉寂时期都要比其他三个时期要低,而且都处于最后一名。所以,洪武至天顺年间是明代广东书院发展的沉寂期,这与全国总体情况是一致的,“明初近百年的书院,基本处于沉寂而无闻的状态[2]272”。
(二)上升时期。成化到正德年间(公元1465年~公元1521年)共57年,历成化、弘治、正德三朝,共建书院31所,比沉寂时期的21所多10所,比鼎盛时期的167所少136所,比回落时期的32所少1所。上升时期广东书院的年平均数为0.544所,比沉寂时期的0.216所多0.328所,比鼎盛时期的1.687所少1.143所,比回落时期的1.333所少0.789所,比明朝广东书院年平均数1.018所少0.474所。无论从书院总量,还是本阶段年平均数,上升时期均高于沉寂时期,但低于鼎盛时期和回落时期。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的书院数量和各朝年平均数的排名,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三朝书院数量逐渐增长,排名分别为第6、第5、第4,年平均数排名分别为第9、第6、第5,名次亦依次提升。虽然正德年间的13所并没有超过明代广东各朝书院平均数16.59所,但13所已是鼎盛时期前最接近平均值的数目,这印证了成化至正德年间是明代广东书院发展的上升时期,但还远远没有达到顶峰。
(三)鼎盛时期。嘉靖至万历年间(公元1522年~公元1620年),共99年,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共建书院167所,分别比沉寂时期的21所、上升时期的31所和回落时期的32所多146所、136所和135所。鼎盛时期的书院数量占本朝书院总数的59.22%,分别比沉寂时期、上升时期和回落时期高51.77%、48.23%和47.88%,而这一时期广东书院的年平均数为1.687所,分别比沉寂时期的0.216所、上升时期的0.544所和回落时期的1.333所多1.471所、1.143所和0.354所,而且比明代广东书院年平均数1.018所还要多0.669所。明代广东书院鼎盛时期的总数、年平均数,均处于四个时期之首,沉寂时期、上升时期和回落时期都难以望其项背。嘉靖朝的书院总数和年平均数分别为95所和2.111所,均是明代各朝中最多的,而且比明代广东各朝书院平均数16.59所和年平均数1.018所,分别多出78.41所和1.093所。隆庆朝的广东书院总数和年平均数分别是6所和1.00所,相比嘉靖朝大为减少,且低于各朝平均数16.59所和年平均数1.018所。万历朝广东书院数量又开始大幅攀升,达到66所,占全省总数的23.40%,在明代各朝广东书院数排名第二,形成第二个高峰;而年平均数为1.375所,高于明代广东书院年平均数且排名第三。广东书院在鼎盛时期的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正如邓洪波评价明代全国书院发展态势一样,“嘉靖年间达到最高峰,隆庆时又跌落至各朝平均数以下,但很快就在万历朝再度攀高,形成第二个高峰[3]269”。
(四)回落时期。泰昌到崇祯年间(公元1620年~公元1644年)共24年,历泰昌、天启、崇祯三朝,共建书院32所,比沉寂时期多11所,比上升时期多1所,比鼎盛时期则少了135所。回落时期书院的总数和年平均数(1.333所),均高于沉寂时期和上升时期,而低于鼎盛时期,但年平均数则高于明代广东书院年平均数的1.018所。天启朝的广东书院数量排名第9,虽处于倒数第四,但也比沉寂时期的建文、洪熙、宣德、正统、景泰五朝排名要高;这一时期年平均数最低的是天启朝的第8名,但也比沉寂时期的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七朝年平均数排名都要高,而且比上升时期的成化朝还要高一名。崇祯朝的广东书院数量排名第3,仅次于第二个高峰万历朝,而年平均数1.647所甚至高于第二个高峰万历朝的1.375所,仅次于榜首的嘉靖朝。由此可见,回落时期的书院总数和年平均数,均超过沉寂时期和上升时期,但低于鼎盛时期。回落时期虽然从嘉靖、万历两朝的高峰期急速滑落,但同样比沉寂时期和上升时期发展要快,“回落”也只是相对于“鼎盛”来说,发展速度和规模虽在鼎盛时期之下,但还在沉寂时期和上升时期之上。
二、不同时期书院盛衰的原因分析
明代广东书院的盛衰与文教政策、政治斗争、官学的兴衰和王湛之学的兴盛有着直接的关系。
洪武到天顺年间,广东、甚至全国书院的沉寂无闻,这是明初文教政策的必然结果,明初统治者,重视官学,而禁绝书院。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令“改天下山长为训导,书院田皆令入官[4]”,把书院山长等级降低,学田入官,从经济上禁绝书院,更有甚者,“革罢训导,弟子员归于邑学,书院因以不治,而祀亦废[5]”。另一方面,明朝廷却大力扶持和倡导各级官学,以致形成“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6]1686”的盛况。朝廷还把社学列入官学,以教养童蒙子弟,这造成乡村书院的生源被社学抢占殆尽,严重制约着明初书院的发展。一般士子也因科举和功名的诱惑,更趋于学校,而不再热衷于书院。“明初书院不振的深层原因是学术不讲[7]”,明初朱学独尊,讲学未盛。从洪武至天顺这八朝,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广东与全国一样,书院废而不举,沉寂无闻,新建或重建书院仅21所,是四个时期最少的。
自成化朝开始,广东书院的发展势头有所上升。成化、弘治、正德三朝,书院开始走出低谷,上升发展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官学的日渐衰落和科举的日益腐败,“太学乃育才之地,近者直省起四十岁生员,及纳草纳马者动以万计,不胜其滥,且使天下以货为贤,士风日陋[8]1683”。官学和科举的衰落与腐败所带来的弊端,使一些人士开始转向关注书院,倡导书院教育。此时的朝廷也放松了对书院的限制,皇帝为书院赐匾、赐书时有发生,如广东南海四峰书院三次受到嘉靖帝赐书。地方官员也致力于书院的建设,如弘治朝的提学潘府,在广东清远和恩平县创设了瑞峰书院和凤凰书院,加之著名学者开始光顾书院讲学,使书院与学术再次结合,如江西的吴与弼,广东的陈白沙等学者。这些都使得明代广东书院开始渐渐走出低谷,开始上升发展。
嘉靖、万历年间,广东书院的创建达到了顶峰,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是王、湛之学的兴起及其广泛传播,王守仁、湛若水两位讲学大学,把学术与书院结合起来,将书院作为学术研究和宣传本派学术思想的主阵地,同时,学术观点上的分歧,使得两位讲学大师,各标其宗,各树其义,天下学者各依所从,各立书院。龚伯洪的《越秀名人》记载湛若水“于广东创办的知名书院有:广州的白云、天关、小禺、上塘等,增城的龙潭、独冈、莲洞等,西樵的大科、云谷、天阶,罗浮的朱明、青霞、天华,曲江的帽峰,英德的清溪、灵泉等”16所。此时在广东辟书院以讲学的理学名儒还有方献夫、霍韬、黄佐、何维柏、薛侃等学者,他们各承师说,各立书院,授徒讲业,如师从王守仁的薛侃,在中离山建中离书院,在桑浦山建宗山书院。提学魏校来粤后,又大毁淫寺改书院,以讲心性之旨,一些在任或致仕的官员也积极创建书院,一时广东书院大盛,并在此时达到鼎盛。
明代广东书院在经过鼎盛时期之后,进入了天启、崇祯朝的回落时期。嘉靖、万历两朝虽是书院发展的顶峰,但政治斗争祸及天下书院,明廷的三毁书院,断送了明代广东书院的辉煌。郭的《岭海名胜记》载:“万历中,宰忌讲学,毁及院舍,有司奉行,急若旱火,西樵独流祸烈,…若大科,若铁泉、玉泉、天阶诸舍,皆被毁拆,…名贤寤寐之地,遂为烟蔓之场”。“嘉靖初禁,抑制了书院的强劲发展势头;万历再禁,终止了书院的兴盛局面;天启三禁,书院几乎气绝[9]381”。加之明廷在内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流寇和农民起义严重;在外又有清兵的进攻和威胁,内忧外患,使士民建设书院的热情大大降低,此时的广东书院如同明朝末年,已是日薄西山。
明代以前,广东书院在全国无足轻重,到了明代,广东书院猛增到207所[10],跃居全国第二,成为全国书院最发达的省区。笔者认为,这个重大的转折与陈白沙、湛若水等广东本土的学术大师以及甘泉学派的崛起,有着重大的关系。
[1]孔祥龙.明代广东书院数量再考[J].北京:神州,2013,(21).
[2][3][9]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
[6][8]张廷玉.明史·卷二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5](雍正)宁波府志·卷九[M].乾隆六年刊本.
[7]周德昌.中国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52.
[10]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