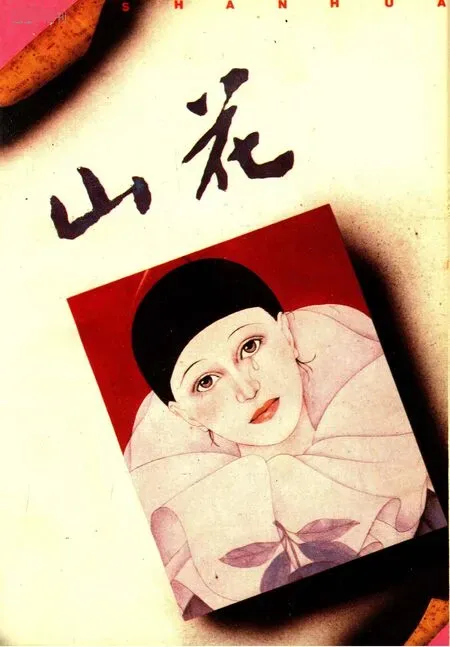论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激情”叙事
2013-08-15徐汉晖
徐汉晖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1966年这十七年间发行量巨大、社会影响深远、书写革命历史的小说。这些小说因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气势恢宏的史诗风格在当年红极一时,直至今日还有大量被改编成影视剧,依然活跃在荧屏上。这批小说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底层贫弱群众以激情如火的精神力量战胜反动统治者的革命画卷。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活动,是受压迫阶级对强势的腐朽势力的反抗。因绝大多数革命者出身寒微,而革命阶层无论在政治地位上,还是经济地位上,都不被当权阶级认可,是弱势群体。但因为对现存腐朽阶级的怨恨和不满,政治和经济地位上处于弱势的革命阶层,要与强大的反动势力作战,必然要求在精神气质上足够强大。因为经济地位等方面的贫弱,是外在的社会时代强加给革命者的。他们唯有用饱满的精神和昂扬的激情去战斗,才能以弱抗强以少胜多,去消灭黑暗的社会现实。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我们随处可看到这些富有激情的革命精神的描写。无论革命者处于顺境抑或逆境中,他们总是斗志昂扬、乐观坚强。
顺境斗志昂扬
在革命的漫长道路中,充满了挫败和牺牲,正所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革命是你死我活的拼杀,必然有腥风血雨的过程,在对敌斗争中,顺势和逆势总是更迭相生的。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为读者呈现了这样的一批革命者,他们无论处于何种境地,总是沉着冷静,尤其当斗争形势上升到暂时和相对的“顺境”时,他们更是不骄不躁、斗志昂扬,善于运用优势条件调整自我、消灭敌人。
这其实体现和蕴藏了一种进化论的历史观点。因为,在革命者的心中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即使眼前悲惨万丈,但进化论构建了一个未来的乌托邦,它有助于帮深陷困境的革命者摆脱悲观的心态,树立从危机中崛起的信心。“试看将来的环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是革命者李大钊说过的话。因此,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总能看到一种斗志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和精神。在这些作品中,作家很少涉笔战争的残暴和荒诞,也很少关注战争状态下人的生存处境和战争重压下的悲惨,更少涉笔对战争深刻的反思,而洋溢着的是积极向上的亢奋精神。小说《林海雪原》中有一段对革命前途问题的描写:“前途?”杨子荣突然愣了一下,停止了吃饭,然后他微笑道:“现在咱这不在前途上走着吗?现在我这个侦察兵就已经是我的前途了,因为我是在通往共产主义的大道上走着。”他喘了一口粗气,“以往地主骂得我不敢吭气,现在我手使双枪,动用心机,自由地瞪着眼,喘着气,打他们的老祖宗蒋介石。”他兴奋地把筷子向小炕桌上一敲,“这是多么理想的一天哪!又是多么理想的前途呀!”他略停了停,“往小一点说,昨天的战绩,是我前天的前途;今天的战绩,是我昨天的前途;明天的战绩,是我今天的前途。这样一桩桩,一件件,一天天,一月月,一步一步地就走到了穷人翻身阶级消灭的太平年。”
这段话是小分队在取得又一个胜利之后布置新战斗之前,杨子荣回答少剑波的内容,字里行间充满了乐观。而在杨子荣说完这段话不久,他们立即投入了战斗的运筹之中,“有的主张直打硬拼。有的主张调全团的人马围剿大锅盔。有的主张再来一个杨子荣献礼当团副,重演一幕百鸡宴。有的主张诱敌出洞打埋伏。有的主张虚张声势轰跑敌人打追击,因为在森林中,骑兵吃不开,树林碰马头扫马眼,步兵陷雪坑滚雪球,怎么也比不了咱们小分队的滑雪飞。有的却主张偷摸齐爆破”。
小分队成员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在每一次战斗打响之前,都表现出异常的兴奋和激动,仿佛打仗就是一场快乐的游戏,丝毫不见恐惧和紧张。其实,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这种高昂的革命精神和情绪与时代的要求有关,它是国民心态的写照。新中国成立过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全体人民都以饱满的热情与激情投入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这种全民皆欢的情绪自然也会影响到作家的创作。中国人民在面对一支胜利的英雄军队和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且深受爱戴的政权的时候,其精神是自信而豪迈的,这一时代精神的主导同时也渗入了文学创作。“对于置身于红色文化(文学)秩序中的中国作家来说,他们所必须认同的集体理想人格是明确而又单一的,即红色的‘革命英雄’人格,这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或文化规范的必然要求。”当时的文艺方针更是认为,革命和战争“在反动统治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几乎是不可能被反映到文学作品中间来的。现在我们却需要去补足文学史上这段空白,使我们人民能够历史地认识革命过程和当前现实的联系,从那些可歌可泣的斗争的感召中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信心和热情”。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就遵从了这种主导思想,以对历史的“本质”规范化叙述证明新社会的真理性和合法性,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时期的民众提供了行为准则和思想依据。
因此,在这些小说文本中,我们总能看到一群“欢乐英雄”,如周大勇、杨子荣、双枪老太婆、沈振新等,他们作为“革命暴力”的施与者,站在了主动出击的位置上,总能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胜利。对于他们而言,残酷的革命战争过程是精彩刺激的,结局是必胜的,满足了民众对于革命战争最乐观、美好的想象,构成革命文学中最具有戏剧性、欣赏性的一幕。
《红日》中有一处对大战来临之前气氛的描写,就体现了战斗必胜的信心与想象:中午十二时正,电话总机向各个部队的参谋机关、政治机关发出通知,对准表的时间。所有的钟表指针,向着下午八时的目标移动。全军指战人员的心,像钟表的摆一样,平匀而有节奏地弹动着,向着下午八时正。——这是长久渴望的时刻啊!他们紧张而满怀兴奋地迎接战斗的夜晚。一场战斗即将打响,战士们的心就像钟表一样平静、不紧不慢,他们精神饱满而又兴奋。在他们心中,战斗是轻松快乐的,他们只是渴望着时间快点过,以高昂的战斗姿态等待必胜时刻的来临。这种激情也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体现。
逆境乐观坚强
革命者在恶劣的生存环境里,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自身的力量,把个人的物质需求和欲望降到最低点,时刻激励自身的精神意志,以便迸发出最为强大的战斗力。这就客观上要求每一位革命者要有愚公式的坚忍不拔和积极乐观的斗争精神。这样的战争文化环境形成了一种群体的精神氛围,从而影响并塑造了个体的心理特征和精神面貌,使那些革命者呈现出超人的意志品质和坚强精神。因此,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所呈现的那些革命者面对困难时,总是高昂乐观、激情澎湃、毫不畏惧的。杜鹏程在谈到自己作品中的革命者时说过“在战斗生活中,……他们勇敢、坚定,工作积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在生活中是普遍的,我对这两个人物的原型,几乎没有多少加工。”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战争年代里,革命队伍往往靠激发出的强大精神力量,使个体获得有力支撑,并经受住严峻的考验,热血朝天地投身于革命洪流中。
因为革命道路是一段漫长而又充满艰险、动荡不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血腥与残酷、死亡和伤痛,参与者随时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这种外在环境的严酷容易让人产生恐惧、怀疑甚至动摇的情绪。要想获取革命的最终胜利就必须要求革命者经受住血与火的考验,坚强面对重重困难,走出潜藏着的恐惧阴影。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是一部描写战争环境的小说,周大勇领导的革命分队为了配合和掩护主力部队,以延安为中心在延安周边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他们跨高山、涉深河、徒步沙漠,备受弹尽粮绝的煎熬和敌军前后追击的危险,但无论在何种困苦环境下,这支革命队伍始终坚强不屈,积极乐观。在榆林战役中,周大勇兼任指导员,这支人数不多的连队和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浴血苦战,面临着极为艰苦的外部环境:“战士们到处找水喝。可是哪里有一点水呢?敌人经过这个村子,把水喝光,把水缸打破。找水窖吧,国民党匪军把他们死去的十多个伤兵都丢在水窖里。战士们从拂晓到现在整整战斗了九个小时,米面屑没进口,肚子饿得发烧,渴得喉咙直冒火。”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战斗是难以支撑的,但是我们的英雄们能够顶得住。在风雨、饥饿和敌人面前,战士们没有被吓倒,而是心中温藏光明,坚定地“向前向前向前”。这就是一种“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英雄豪迈和浪漫主义激情。他们“一把一把地把生面粉往口里填;嘴边、胸腔的衣服上都是白扑扑的面粉。有的人还苦中作乐:‘多擦点粉,去扭秧歌!’”战士们表现得如此英勇顽强和富有激情,这里面当然融入了作家对民间传奇英雄那种“武勇神力”的推崇,但也被赋予了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们强大而不可战胜的精神能动性。当然,也有批评者指出,《保卫延安》一类的革命战争题材小说情感过于饱满和亢奋,充斥着有点夸张的革命乐观精神,其“艺术视域极为狭小,战争生活中丰富多样的生活状态被简单地模式化,交战双方人员中变幻莫测的情感色调被抽取在黑白分明的两块调色板中,人物多元的价值取向也不容辩驳地被钉在世界的两极,精神内涵更是好则皆好,恶则皆恶,浅表单一。”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激情化叙事过浓的一种深刻洞察。的确,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语言很多都呈现出亢奋的激情表达。
小说《红日》也是描写战争场面的,军长沈振新和他领导的革命部队面对国民党装备优良的七十四师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畏惧,相反解放军战士们感到“仿佛只要是打七十四师,他们可以不吃饭,不睡觉,哪怕前面是汪洋大海也能越过,是重叠的刀山也能攀爬上去,哪怕一个钟头要赶三十里路,他们的两只脚就可以像《封神榜》上的哪吒,装上风火轮架空飞走。又仿佛只要把七十四师消灭,他们的一切仇恨皆消,他们才算得是革命英雄。”虽然在武器装备和战斗人数上,我军处于绝对的劣势,但革命战士们心态非常乐观,激情如火,对胜利的前途充满了信心。这种对比强烈的反差描写,无疑会将革命队伍的形象无限拔高和光辉化,也恰好证明了革命军队的纯良性。
革命领袖毛泽东曾高度强调艰难的逆境有利于激发人们超出一般的潜在能量,“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学问比较少的,被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在他看来,身处逆境困境之中的人是被压抑的主体,其内心必然聚集着天然而强烈的脱困欲望,从而具有蓬勃而旺盛的生命力。小说《红岩》中的革命者华子良正是如此,虽面对险恶环境,处处备受压抑和压迫,但他怀着对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念,装疯卖傻以此麻痹敌人整整十五年,一直坚持到革命胜利的前夕。表面上看起来,华子良疯疯傻傻、精神消弭,实际上他内心如火如炬,充满激情。
这其实是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惯用的一种叙事手法,写革命者、写工农兵的生活与斗争,塑造理想化的典型人物,体现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正所谓“真金不怕火炼”,越是在艰难困苦中,越能凸显英雄本色,彰显革命队伍的伟大崇高和对革命光明情景的乐观坚定。但是,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这些特征不仅仅取决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它们的形成也有着文学自身发展的渊源。与“五四”文学时期或写社会底层的辛酸,或写个人的苦闷,或揭示病态的国民不同,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都是乐观的文学,是富有朝气和激情的文学。这种文学特征的形成首先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作者其创作心理和创作手法深受毛泽东文艺思想和解放区文学传统的影响,其次20—30年代独树一帜的革命文学或左翼文学传统,以及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等都给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呈现出一种革命的亢奋精神与蓬勃之气。
[1]曲波.林海雪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429.
[2]曲波.林海雪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430.
[3]李遇春.权力·主体·话语[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36.
[4]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M].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86.
[5]吴强.红日[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137-138.
[6]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杜鹏程研究专集[C].1979:54.
[7]杜鹏程.保卫延安[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238.
[8]杜鹏程.保卫延安[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238.
[9]陈思广.17年时期英雄史诗型战争小说审美特征论[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10]吴强.红日.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324.
[11]萧延中.“身份”的倾覆与重建——毛泽东晚年政治思想的伦理基础[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5(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