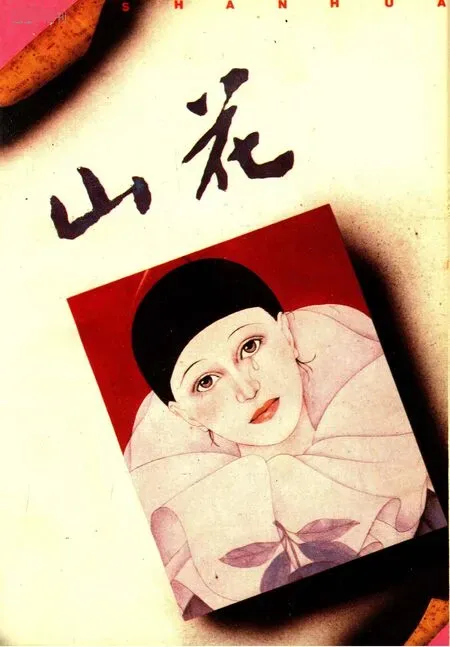嘴上有颗痣
2013-08-15拖雷
拖 雷
上了车,我发现车里还有一个女人,这让我没想到,这个女人不是陈大河的媳妇,他媳妇我见过,去年他们离婚时,我给他们办的房本,他们为什么离婚,陈大河没说,我也没问。
陈大河介绍说:“这是李红梅,是日报社的记者,和咱们一起下煤窑采访,小郭,我们处里的。”
那女人转过身,和我打了招呼,她的样子很媚,眼神里能感觉出来,她笑了一下。
车出了城市,上高速。车是陈大河在开,到目的地老牛头煤矿得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我想,最好的选择就是睡觉,出了城,楼房少了,眼前一下宽阔起来,现在是秋天,山上的植物萧瑟,光秃秃的,像被剪了毛的羊群,惊慌地往一个方向跑动着,我一点都不兴奋,甚至有点麻木,陈大河像是头一次出门,一路上他的声音就是延绵的山脉。
对了,忘介绍了,陈大河是我的副处长,我是他的兵。在单位,我俩都是负责宣传的,他是我的头儿。
陈大河在和那个李记者讲三个月前他到西藏的经历,有时像对我说,有时像对他身边那个女人在说,他的那段经历,我至少听了十回,我很少发出声音,心里猜测着眼前这个女人和陈大河是什么关系。既然是报社记者,我以前应该见过,在单位我也算是负责宣传的老人,见过的记者多如牛毛,可这个女人我确实没见过。
女人很安静,听不到她的一点声音,坐在副驾驶上一动不动,我猜想她是在听着陈大河的讲述或是把目光探向窗外,看着外面单调的景色,不管怎么,这个女人是我旅途上的一个谜。
陈大河停止了他讲述西藏,话题转向我:“小郭,你真的没来过煤窑?”
我说真的,我哪儿都没去过。
这时我感到那女人动了一下,她把头转过来,样子很吃惊地说:“什么,你哪儿都没去过吗,就在城里待着?”
我朝她笑了一下:“我这个人很闷。”
那个女记者声音很真实地说:“看你样子属于闷骚型的。”
这话没有恶意,我没说话。
陈大河似乎又兴奋起来,他一边开着车,一边手舞足蹈起来,他说:“李记者,你不知道,我们的小郭就是一个怪人,前年让他到广州开会,他说家里有事去不了,去年派他到北京学习,他说他孩子病了,他呀,除了单位就是家,眼里就认他老婆孩子,没出息呀。”
“这才叫男人呢,那些整天外面瞎跑的男人又有什么出息。”那个叫李红梅的女人像是在埋怨谁,陈大河好像找不到要说什么,止住了话头。
前面堵车了,全是大型的拉煤车,我看见从喘息的拉煤车上下来几个司机,他们鸡巴把裤裆顶得鼓鼓的,一边站在路边肆无忌惮地撒尿,一边说笑着,李记者把脸转向了一边,她说:“这些人真没素质。”
陈大河按了几下喇叭,那几个司机竟然转过身,鸡巴朝天地尿了起来,他们边尿边大笑着,仿佛在比赛谁尿得最高,陈大河一点都没恼,他被眼前翻滚的尿花,一下子逗乐了,他连声叫着好,完全已经忽略了身边的李红梅,我甚至怀疑他也要掏出鸡巴,加入眼前的这场狂欢,李红梅尖叫一声,用力捶打了陈大河几下,陈大河才止住笑声。
车阵有移动的迹象,那几个司机边系裤子边往车上爬,前面的车终于走起来,李红梅喘了口气,好像被刚才的一幕压抑了很久,她把车窗按下,但很快又升起来,外面一股尿骚味。
前面有警车,他们指挥着让大车靠左道,小车靠右道,陈大河骂了一句:“哪儿堵车,肯定哪儿有交警在检查。”
接下来,车里一下沉默了,无声无息的,我有点犯困,闭上眼总能梦到自己和一个看不清面孔的女人在暧昧,像真的,当我满头大汗地从梦中醒来,我听见陈大河说到了。
我们的目的地是老牛头煤矿,这个煤矿是这里的纳税大户,透过车窗,我看见有不少的大烟囱和像一座座山似的煤堆,老牛头煤矿到了。我是头一次来煤矿,我不太喜欢煤,黑乎乎的,觉得很脏,这几年我们这里的煤炭行业非常好,在我们原先贫瘠的土地下,突然发现出了大量的煤田,原来种地的农民一下子因为煤炭,成了亿万富翁,这样的例子不是少数,很多,他们开始不相信手里的钱是真的,当有一天他们拿着这些钱,买回宝马、奔驰,他们开始相信了,相信自己就是传说中的富人,他们的钱就是天上掉下来的,掉得太多,他们花不了,他们到最好的饭店去吃,到最贵的商店买东西,一件东西买十件。这也花不了,那就买房,本地房子不值钱,就到北京、三亚,哪儿好就去哪儿买,要买就买一个单元,这也花不完,怎么办呀,全是钱,索性开银行吧,这里遍地都是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什么的。
老牛头煤矿是国企,这次下来采访的任务是局长亲自安排的。到了这里,当地地税局的王局长和矿上的领导已经等着我们,王局长是个胖子,他的级别和陈大河一样都是副处,以前陈大河说过王局长跟他不对路,可从两人见面的亲热度来说,看不出两人有什么不愉快,陈大河介绍了李记者,说这是刚刚分管地税口的李记者,王局长满脸堆笑地说,美女记者,好好好,我就喜欢和美女记者在一起工作。
李记者一个老江湖了,她说,王局长真是富态,我也愿意和富态的男人在一起工作。
这话说得有点暧昧,大家都笑了。
王局长抓住李记者的手不放,他说,这个大河呀,身边总是有不少的美女,这个家伙,老是一个人独享,也从来不和弟兄们一起红火红火。
陈大河说,王局长就爱拿我们受苦人开玩笑,你是当局长的,身边到处是美女了,你还愁个红火?接下来,陈大河介绍我,这是我们处里的小郭。我赶紧上去握手,王局长的手很绵,像女人的手。
我不喜欢眼前这个胖子,他的脸上不时闪烁出倨傲的神态,我是个大头兵,这样的领导我见多了,当然也可能是错觉,我看人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
矿上的领导先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座老牛头煤矿的情况,矿领导口才好,人也很精明,不时地提到矿上的发展,离不开税务部门的支持,离不开王局长的关怀之类的话,我挨着李记者,我说,你不用记点什么?
她说,不用,一会儿要份材料就行。
在矿领导讲话时,陈大河一直没闲着,他爱摄影,举着照相机,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拍着,这活应该是我去干,可他是真热爱,我只能看着他,陈大河拍照时,动作很专业,也很投入,为了照矿上的领导,他的照相机几乎快要抵在人家的脸上,他拍一张后站在那里,低头看着相机里的照片,他很满意自己的成果,阳光下,他的脸红红的。李记者对矿上领导的讲话,一点都不在意,她见过世面,用她的话说,她见过的大领导多得像羊群,不管是羊群还是牛群,总之她一点不在乎矿上的领导,她用脚踢了一下拍照的陈大河,陈大河趔趄了一下,她笑着对陈大河说,你给我照几张。
陈大河很乐意,李记者整了整衣服,然后又整了下头发,李记者的眼睛好看,呼啦呼啦地很勾人,陈大河找好光线,从不同角度给李记者抓拍,在这个过程中李记者舞动自己的双手,像舞动天使的翅膀,快要飞起来了,李记者就要快飞起来的那一瞬间姿态,那一瞬间是她最妩媚的,这几张照片很累人,我看见陈大河额头汗津津的。
矿上的领导很快把情况介绍完了,他们让陈大河说几句,陈大河摆了下手,他说,干活吧,就是下矿井里,多拍点税务人员在矿上一线的照片。矿上领导说,这我们都安排好了。
出了会场,李记者去了卫生间。等她的时候,王局长笑着对陈大河说, 听说你现在已经单身了?
陈大河脸红了一下,很快他掩饰住了,他说,领导就是关心群众,连这事也知道了,咋,你有什么想法?
王局长说,想法,想法是有一点。
陈大河说,你说嘛,啥想法你快说嘛。
王局长神秘地笑了一下,他说,我看见那个李记者就不错嘛。
陈大河一听泄气了,他说,什么不错呀,人家才三十岁,太小了。
王局长说,小咋啦,现在人家都不是老夫少妻,再说你爱摄影,她耍笔杆子,这不是挺好的嘛。
楼道传来李记者的皮鞋声,陈大河对王局长说,别鸡巴瞎说了。王局长看见陈大河的窘样,就哈哈地笑了起来,李记者用纸巾边擦着湿漉漉的手边满脸带笑地说,两个老男人,一脸猥琐,又议论什么坏话呢?
王局长摆了摆手,他说,你问陈处长说什么了?
陈大河脸又红了。
我就见不惯陈大河老爱脸红的毛病,一个五十岁的男人,什么没见过,什么没经历过,为什么总要脸红呢,在单位里,陈大河属于老实人,说他老实,是说他嘴笨,和陈大河说话的人,没说几句,陈大河老实的毛病就露出来了,尤其是在饭局上,拿他开玩笑,他开始还能和人家调侃两句,可用不了多长时间,他老实的本性就显露出来,他的脸先红起来,然后舌头开始发僵,后来就是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每次看到他这样,心里真的替他难受。
也有人说陈大河不老实,他的拙嘴笨舌只是假象,他见了女人一点都不这样,不能说他口吐莲花,可也是妙语连珠,逗得女人们花枝乱颤,我和他出入这样的饭局几次,他的饭局女人总是很多,一般全是记者,有报社的、电台的、杂志社的,电视台的,当然也有这些女人领来的女人,这些女人通常都能喝酒,属于千杯不醉的,我的酒杯就是被这些女人倒满,然后再逼着我喝下去,开始我还比较谨慎,可酒精这东西,放在桌子上是平静的,像睡着的婴儿,可一放到肚子里,就变成沸腾的马群,奔腾呀,呼啸呀,长嘶呀,总之你就不会安分守己,有一次我还差一点犯了错误,那天我喝醉了,是一个电台的女记者送我回家,我俩坐进一辆出租车里,没过多久,我的手伸进了那个女人的怀里,她一点不拒绝,还有点陶醉的样子,就在我想解开她的裤带,深入地抚摸时,她用手轻轻拍了下我的手,那表情像责怪一个淘气的孩子,我酒醒了。
我干的这些糗事,我不清楚陈大河知道不,就算知道也无所谓,我想他也不会老实到哪儿。
站在下矿的通道前,王局长已经穿戴好了安全帽和矿工服,他肥头大耳的,一点都不像矿工,一看就是装样子的,他手里拿着几份宣传材料,那个矿长就站在他的身边。陈大河很投入,像个导演一样,摆弄着两个人的位置,摆弄好了让他们不要笑,尽量像是在交谈什么,王局长说,这个老陈,就会制造假新闻。他这么一笑,刚刚静下来的气场,一下子又乱了,人们憋不住了,一下子笑得前仰后合,这话又说到了陈大河的软肋。他忙说,这是人家李记者的要求,好啦好啦,很快就照完了。王局长也就不开玩笑了,他配合着陈大河的要求,边给矿长递材料,边询问着什么。
王局长刚才说的假新闻,确实是陈大河的软肋。两年前陈大河在基层采访,发现一个地税局条件很艰苦,它在山区,管辖着很多煤矿,陈大河看到后写了一篇新闻,这篇新闻原文是这里的税务干部在冬天生活非常艰苦,有时没有菜,只能吃咸菜和馒头,请注意,这里陈大河用的是有时,这稿子到了报社,编辑看后就擅自把“有时”删掉了,用了一个很扎眼的题目,就是大山里税务干部每日啃咸菜吃馒头坚持工作。这篇新闻一刊发,好家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省里的领导高度重视,亲自做了批示,要发扬这样吃苦耐劳的精神,要求广大税务干部向他们学习。这文件层层传达,据说开始时陈大河还有点忐忑不安,甚至责怪报社,你们这是干吗呢,后来他看风向变了,局领导不仅没说他写假新闻,还要责成他把这件事广泛宣扬,那个山沟沟里的税务局,一下子火了,成群结队的记者去了一拨又一拨,大大小小的领导慰问了一次又一次,这里的税务局基本无心工作,除了接待各方神仙外,就是组建宣讲团,到各个地方宣讲他们先进的事迹,这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人去多了,发现这里的条件并不艰苦,他们吃得好,住得好,这里的税务干部开的汽车都是三十多万的,又有人爆料说,这些人为什么来这里工作,事实上根本不是为了艰苦,在当地想来这里工作的人快把头都挤破了,为什么呀,这里管辖着煤矿,说都知道煤老板有钱,他们有钱,出手就大方,出手一大方,管理他们的人就会水涨船高。这么一吵吵,这么一宣传,检察院的人就来了,没过多长时间,查出这里的领导有经济问题,上面就停止了宣传,陈大河从此落下个制造假新闻的名声。
有什么办法,陈大河太爱岗敬业了,太希望人间有奇迹发生,用他的话说,这叫什么,叫正能量。
所有的人里,我是唯一没有下过矿的人,里面漆黑一片,矿上的车沿着矿道不断往大地的内部前进,越走越黑,像就要进入大地的子宫。车上的人很轻松,有说有笑的,我很紧张,身体不断地发抖,我想象着记忆中的矿难,想象着二十七个阶级弟兄,想象着没有水喝,被掩埋在地下一百米之中,叫天不应,叫地不灵,黑暗中,我的手突然被一只手抓住了,很纤细,这时我才想起来李记者就挨在我的身边,她的气息开始真实了,她说,小郭,你是不是胆子太小了?
她的声音不大,所有人都听见了,他们假装没听见,我说,我头一次。说完后我觉得不妥,接着又说,是头一次下矿里。
人们一下笑了,笑得很有内容,黑暗中又传出王局长的声音,他说,老陈,你应该不是第一次吧,一看你就是个老手。
陈大河也挨着李记者,他的声音结结巴巴的,他说,好多次了。人们又是一阵笑声。
那只小手还握在我的手里,没有抽出来的意思,反倒越握越紧,我的心一点都不紧张了,一种暖意正从黑暗的内部缓缓上升,它让我的心有了光亮,我甚至能感到李记者的身子在向我一点点地倾斜,一点点地,既能感觉到,又捉摸不定,那种感觉在那一霎那间,感觉真好,我的身体像被春天所包围。前面有了亮光,李记者轻轻把手抽出来,我有点恨眼前的亮光。
前面亮了起来,矿道很高很宽,车只能到这里。下了车,矿长开始介绍这是主井,假如发生矿难,人们都会逃到这里,这里的水和食物能维持一个月的。人们的脑子里有各种各样古怪的问题,不断问着矿长,尤其是李记者,她问完一个问题,又接着一个问题,矿长好口才,他的口才就是清泉,浇灌着众人提饥渴的问题。
陈大河跑前跑后,举着照相机不停地拍,这个时刻激发出他强烈的创作欲望,他完全忘我了,我看见他一只脚就踩在水里,自已却浑然不觉。我跟着众人的脚步走走停停,事实上,这次下矿的任务就是写稿子,写完稿子,挂上陈大河和李记者的名字发表在报纸上,当然还有陈大河的照片,写稿子对于我来说,不会有什么困难,我写了两年的领导讲话,四年的公文,六年的工作信息,写新闻我虽是新手,我想应该不会很难,我看过以前陈大河的新闻稿子,看过了我相信自己了。
煤层很清晰,一层一层的,我在上面用手抠了一下,很坚硬,这都是千年的植物形成的,我真希望在上面找到一块像化石一样的煤块,看到有一片树叶就在其中,安静地躺在上面,躺了整整千年。
前面是生产的地方,机器轰鸣,来往的矿工看不见表情,我把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想象成是自己,我看着眼前这群上面来的领导,我在想什么,我的眼前晃了一下,陈大河笑嘻嘻朝我照了一张相。前面的矿道越来越难走,不光是地上的水越来越多,还有管道,有机器,李记者停止发问,她更多的时候注意自己脚下的路,她走得歪歪斜斜,严格说,李记者的身材很不错,不错哦,也就是说她是属于我喜欢的那种女人身材,她高翘的屁股就在我的眼前晃悠,像匹骄傲的母马,我尽量想去遏制住这样的念头。
陈大河有好几次想去扶李记者,他的手伸到一半,就停止了,李记者似乎并没注意到陈大河的好意,她很专注自己脚下的路。王局长看着陈大河着急的样子,他忍不住说,甚叫个逑也干不成,这就是。说完嘿嘿地坏笑了两声,李记者就停下脚步,转过头,你们两个老男人,又使什么坏呢?
王局长说,老陈说你长得性感。
陈大河在黑暗的矿道里,紧张地差一点摔倒,我可没说。
李记者咯咯地笑了,像只快乐的母鸡。
参观完了煤矿,天也快黑了,矿上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别看这里偏僻,在吃喝上可以说应有尽有,这里的餐厅修得非常漂亮,不亚于城里的五星大酒店。尽管这样,矿上的领导说,我们这里条件艰苦,委屈了各位领导啦。我挨着李记者,记忆中的温暖还在我的体内残存,我希望灯突然灭了,这样我会用手主动地抓住她,这是想象。在酒桌上,陈大河先是示弱,他说,我得了前列腺炎,喝不了酒。
王局长不依不饶,他从服务员的手里把酒拿过来,给陈大河倒了满满的一大杯,你得了前列腺炎是半个男人,再不喝酒,就是个太监,喝,今天我喝多少你就得喝多少。
陈大河呀陈大河,关键的时候,脸又红了,嘴笨得像被冻住了一样,没办法呀,来了基层,不喝酒就是不给人家面子,就是让人家难堪,这酒能不喝吗,这烟能不抽吗?
李记者很大方一点不像陈大河那样,她不仅敢喝酒,而且会话赶话,这话赶话必须说得机智、稳妥,说得大家既高兴还要留有余地,李记者见多识广,没一会把王局长说得哑了火,王局长就把风向转向了陈大河,他说,陈领导呀,你是上面来的,来到这里你就是领导,来,咱们俩豪华上一个。他说的豪华就是把分酒器里的白酒一口干掉,这需要的不仅是酒量还有勇气,陈大河说我真不行,一半行吗?
王局长说,甚不行,男人甚都行,来,干了。说完他举起杯,一条炽热的白龙钻进了肚子,人们看得都晕,别说这酒倒进了肚子,陈大河被僵住了,王局长吃了口菜,说,干哇,看甚呢。
陈大河一脸痛苦,他举起杯喝了一半。
甚人啦。王局长说,是不是嫌我们的酒不行,快,干了。
陈大河说,我真的干不了。
我站起来说,王局长要么我替陈处长喝吧。
王局长不同意,你当处长啦,喝这酒得有级别,快,喝了。
陈大河满脸通红,现在已经看不出是憋的,还是酒精上脸,红彤彤的像个关公,在单位里陈大河的酒量也就一两,尤其他喝不了快酒,看起来他都快哭啦。
李记者说,那我敬王局长一杯吧,先让他缓一缓。说着她走到了王局长的面前。
王局长说,好,这个男人干不成,还是和美女喝吧。
说完,两人又豪华了一大杯酒。
酒席上的气氛又热烈起来,大家聊起了,最近网上刚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当领导的和女人的上床照被挂到了网上,大家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现在上面查得紧,千万不能放松警惕,也有人说拍照片的人太他妈的不是东西,也有人说这就是一个套,人家故意陷害他的,为什么陷害他呢,因为他收了钱不办事,把人家逼急了,就给他下了这么一个套。
王局长多少有点喝多了,他的舌头还算利索,他说,这个呀你们就不懂了,为甚他倒霉,你们注意到了没有,他的嘴上长了一个痣,长这样痣的男人都是花心的男人,你们看啊,咱们的陈处长嘴上也有这么一痣,这就危险啦,别人咋红火都没事,你就不行啦,一红火就容易被人家抓住。
王局长的话刚刚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人人都去看陈大河的嘴巴,果然那儿确实长了一个痣,这个痣就在他嘴角的左上方,它像一粒芝麻趴在那里。王局长的嘴一点都不留德,他这么说是故意的。
陈大河突然站起来,把桌子上那个酒杯狠狠摔在地上,他摇晃着身子,说,你妈个逼,老子不是要饭的,老子是局长派来工作的,你妈个逼,你是个什么东西,老子现在就给局长打电话。
这个意外的举动,所有人愣了,包括王局长,他想不到陈大河会摔杯子,想不到他会骂人,我和李记者都起身,安抚着陈大河。陈大河确实生气了,他把身后的椅子来回墩着,他说,姓王的,我知道你看不起我,老子若不是局长指派,才不会到你这里来,你俩别拦我,我现在就给局长打电话。
李记者把陈大河的手机抢下来,她说,不合适不合适,要打也是明天打。
这么一闹,王局长的酒有点醒了,他站起来,端着酒杯说,这么多年的弟兄,你这是干甚呢,这里还有矿上的领导,行行行,我错啦,赔个礼。
陈大河一点都不买账,他用手摆了一下,将王局长手上的酒杯打飞,他说,少寡逼,老子才不要你赔礼。
说完,陈大河穿起衣服,就往外走,我担心他出事,紧跟着他出了雅间,众人都跑出去劝陈大河,矿领导很尴尬,他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出了就出吧,他说这样吧,先安排你们回房间里冷静冷静。
宾馆就在餐厅的上面,一进屋,陈大河就号啕大哭起来,他说,姓王的不是东西,就是个小人。屋里只有我和李记者,我是个大头兵,两头都是领导,都不敢得罪,我只能说些安慰陈大河的话。陈大河哭得很伤心,这时我感觉他像个软弱的女人,这样的感觉以前没有,现在很强烈,他甚至抓住李记者的手,像一对不幸的姐妹在叙说不幸。
哭完了,陈大河吐了口气,他一下子轻松了。这时王局长进了屋,他一点都不嚣张了,一脸诚恳,陈大河不理他,他就嬉皮笑脸的,后来他示意我和李记者先出去一下。
我和李记者各自回了各自的屋里。这是九点半发生的事。十点钟,我到陈大河的房间找过他一次,房间没人,我问了下服务员,她说,她看见房间里的两个人出去了,至于去哪儿,她不知道。
我打过陈大河的手机,他关了机。没办法,我回了房间,我给李记者打了一个电话,她在房间,她的声音酥酥的,我把刚才的事对她说了一遍,她说管他们的呢,你在干吗,我说没事。她说没事就来我房间吧,我和你商量下稿子的事。
我找到了她的房间,她的门没关,屋里有一股幽香,这个时候我看见她的浴室门半掩着,里面有激动的水流声,我推开门,里面雾气沼沼的,我看见一条金黄的鱼快要被淹死。
它像是在呻吟,像是在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