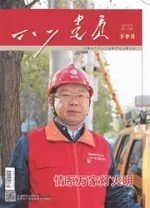足尖上的“咏叹调”——记辽宁省第二批领军人才、辽宁芭蕾舞团团长曲滋娇
2013-08-11程晓松
文/本刊记者 程晓松
衣袂飘舞间,曲滋娇踏着款款的舞步,意蕴流转于方寸舞台之间,如诗如梦,亦幻亦真。
无论是作为当年辽宁芭蕾舞台上的第一只“白天鹅”,抑或辽宁首个国际级芭蕾舞金奖获得者,直到今天的辽宁芭蕾舞团团长,舞蹈都是曲滋娇人生光谱中最亮的一抹色彩。
她注定与芭蕾不可分离。
她的名字注定与辽宁芭蕾舞团不可分离。
逐梦:“白天鹅”的倾情之舞
足尖、压腿、掰腿、下腰、转圈、大跳、腾空……空旷的练功房里,曲滋娇重复着单调而枯燥的芭蕾动作。
1980年,这是辽宁芭蕾舞团组建的第一年,曲滋娇刚满18岁。
成为辽宁芭蕾舞团的第一代演员,对于从小就梦想穿上红舞鞋、成为《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那样光辉形象的曲滋娇来说,心情无疑激动而亢奋。这意味着梦想的实现。
从小就表现出艺术天赋的曲滋娇跟着身为京剧票友的父亲学过京剧,随后,酷爱舞蹈的她进入大连少年宫学习舞蹈。半年后,曲滋娇随着前来招生的老师进入沈阳音乐学院附属舞蹈学校专业学习芭蕾舞艺术。1980年,辽宁芭蕾舞团成立,曲滋娇被招入团中,成为辽宁芭蕾舞团的“开团”演员之一。
上世纪80年代,芭蕾舞这种源于西方的高雅艺术尚处于曲高和寡之境。虽属“阳春白雪”,无奈高处不胜寒,“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对普通百姓来说,芭蕾舞还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遥远之物。选择了这条道路,对于刚刚上路的芭蕾舞演员来说,前程还是未知数。
然而,什么都阻挡不了对艺术的追求和热爱。正如诗人汪国真的一首诗中表述的:“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像云一样柔软,像风一样轻……比梦更美,比幻想更动人”,这是诗人艾青对芭蕾舞的形容。芭蕾是美的极致,也是苦的极致。对一向要强的曲滋娇来说,高强度训练是家常便饭,枯燥、乏味自不待言,摔伤、拉伤也时有发生。有一次,她10个脚指头磨破了8个,不住流血,走路都费劲,曲滋娇咬咬牙,挺了下来。
《天鹅湖》是芭蕾舞的经典剧目。在沈阳音乐学院附属舞蹈学校排演这出剧目,确定主要角色“白天鹅”的舞蹈人选时,曲滋娇从10位女演员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辽宁历史上第一位表演“白天鹅”的芭蕾舞演员。凭什么选定了身高和线条都不最具优势的曲滋娇?第一是悟性,第二就是曲滋娇特别能吃苦。
1988年,辽宁芭蕾舞团选派曲滋娇参加国际上的重大舞蹈比赛——法国国际芭蕾舞大赛。赛前,因为训练强度非常大,曲滋娇不慎尾骨骨裂,疼痛难忍,在床上一躺就是10多天,甚至连中央芭蕾舞团的专家都不忍心再为她排练,很多人劝她放弃比赛。可是,心里憋着一股劲儿的曲滋娇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参加国际大赛的机会。她忍着伤痛,打着封闭针坚持排练,最终获得国际大赛金奖。
辽宁芭蕾舞台上第一位“白天鹅”的表演者、辽宁第一个国际级芭蕾舞金奖获得者……伴随着辽宁芭蕾舞团的崛起,曲滋娇成为辽宁芭蕾舞台一颗耀眼的明星。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辽宁芭蕾舞团的主要演员,曲滋娇主演了世界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海盗》《无益的谨慎》以及辽宁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孔雀胆》《家》等作品。她亭亭玉立的身影、优雅曼妙的舞姿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赢得了芭蕾舞台前经久不息的掌声。
创新:芭蕾舞台的“中国风”
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着,洁白的纱幔,铺满了辽河两岸的人家。
广袤的黑土地,深情的黑土地。
是谁在这片沃土上播撒着种子,开垦着希望?
如诗如画的布景、飘逸的白纱裙、曼妙的舞姿、灵魂深处的激情……芭蕾无语,却完美地演绎着辽河大地建设者的风采。
羽毛、花、高高耸立的石油塔架……舞台上的元素象征着从辽宁起飞的地球上第一只鸟、在辽宁绽放的地球上第一朵花以及沈阳的飞机制造、大连的船舶制造、鞍山和本溪的钢铁冶炼、辽河油田等具有代表性的辽宁标志。
富丽堂皇的辽宁大剧院,座无虚席,观众欣赏着曲滋娇担任团长后组织创作排演的辽宁芭蕾舞团第一部具有强烈辽宁地域特色的交响芭蕾舞蹈诗《辽河·摇篮曲》,掌声不断,好评如潮。
《辽河·摇篮曲》全剧共分四场——大地之歌、生命之歌、建设者之歌、辽河母亲之歌,分别以冰雪、黑土地上的播种、建设美好生活和辽河畅想表现全剧的主题思想。
“恢弘、抒情、曼妙、优美”,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欧建平评价,《辽河·摇篮曲》的舞蹈场景壮观,音乐激昂优美,舞台效果极具震撼力。
“这是一幅东北风情的画卷,这是一部赞美生命的诗篇,这是一曲讴歌自然的乐章,这是一首美好时空的赞歌……”曲滋娇谈起《辽河·摇篮曲》的创作排演,深情地说。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年龄的原因,曲滋娇逐渐淡出舞台中心。担任辽宁芭蕾舞团副团长及接任团长职务后,她致力于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芭蕾舞艺术作品,在探索建立中国学派的芭蕾艺术道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古朴的长袍、独具中国魅力的二胡、一把红雨伞……时任主抓业务副团长的曲滋娇协助团长组织创作排演的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之后的中国第三部优秀芭蕾舞剧《二泉映月》,可以说是一部“下身芭蕾舞,上身中国古典舞”的充满创新意味的舞剧。该剧将中国经典名曲和民间音乐家“瞎子阿炳”的人物形象以芭蕾舞的形式演绎,突破了很多芭蕾舞中程式化的东西,尤其在展现人物内心方面,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和中国民间舞蹈的元素杂糅其间,在展示西方传统芭蕾舞风采的同时,表现出了浓浓的中华民族舞蹈文化的意蕴,既不失芭蕾舞的特质,又充满新意。该剧成为辽宁芭蕾舞团的“镇团之作”,先后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戏剧节金奖、全国舞剧比赛优秀剧目奖、辽宁省艺术节金奖等奖项。
创新是曲滋娇在芭蕾舞艺术上永恒的追求。以扇子、旗袍表现中国韵味的《茉莉花》,将中国武术融入芭蕾舞的《太极》,通过京剧表演《霸王别姬》,将古典舞融入芭蕾舞中……一系列“石破天惊”的创举,源于西方的芭蕾舞艺术这一“舶来品”充分融入了“中国元素”,印上了“中国符号”,使这一高高在上的“贵族艺术”走进寻常百姓的视野。《二泉映月》在全国巡演超百场,观者无不如痴如醉。中央电视台“舞蹈世界”栏目以“辽宁芭蕾舞团”为专题录制4期节目,连续播放4周,这在中国舞蹈界还是首次。
和谐:“大家庭”般的温暖
“躺在病床上的一年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老妈(指曲滋娇——编者注)、同事、朋友、亲人和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平日里习以为常,并不太在意,当我真的受伤、躺下了,我才感受到这种温暖的伟大。是老妈和亲人们的爱,让我又站立起来,重新回到了我热爱的芭蕾舞台。”这是辽宁芭蕾舞团明星级舞蹈演员、副团长吕萌伤愈复出后一段发自内心的话语。
在辽宁芭蕾舞团,许多年轻人都亲热地称呼他们的曲团长为“老妈”。“妈”这个词汇,意味着最亲密的信任。团里年轻人有工作上的问题、生活中的私事,第一个要找的人常常就是曲滋娇。
“老妈啊,我要买房子,可钱取不出来了。听说你认识人,可得给我帮帮忙啊!”正在国外访问的曲滋娇手机响了,听筒里传来团里一位年轻演员焦急的声音。
“别着急,有老妈呢,等我的信儿。”年轻人买套房子不容易,远在国外的曲滋娇比办自己的事还上心,放下身边的活儿,就开始忙碌起来。
一个个熟人地找,一个个电话地打……在曲滋娇的努力下,芭蕾舞团这位年轻演员终于解决了房贷问题。
整天忙着演出的事,不是上演的剧目,就是团里的演员,孩子都有些“嫉妒”了。上大学前,儿子和妈妈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
“妈,给你提个意见。我从小到大,你基本不管我,都是姥姥带我。妈妈的工作就是这样,这些我现在都理解了。可是,妈妈你整天就吕萌、焦洋、王韵(均为辽宁芭蕾舞团现役著名青年演员——编者注)地挂在嘴边。跟我爸谈的不是吕萌这样了,就是焦洋那样了。你在单位管他们的事就够多了,回家了,怎么就不多问问我的事呢?我怎么觉得你关心他们比关心我还多呢?”
儿子的一席话,说得曲滋娇眼圈红了。哪个父母不疼爱自己的子女?曲滋娇向儿子连连道歉,更多的话,隐藏在心底。
她的爱博大而深厚。她是小家的母亲,更是剧团大家庭里年轻人的“家长”。儿子已经长大成才,而在她的辛勤耕耘和悉心培育下,辽宁芭蕾舞团的整体人才培养工作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2012年,辽宁芭蕾舞团在国际赛场上的“大丰收”,是曲滋娇的“孩子”们对“老妈”最好的回报和礼物——在第七届赫尔辛基国际芭蕾舞比赛中,演员王韵获得了特别大奖和柴可夫斯基音乐表现大奖;在第二十五届瓦尔纳国际芭蕾舞比赛中,辽宁芭蕾舞团舞蹈学校学生何泰昱获得了特别大奖和“埃米尔·迪米特洛夫”奖两项大奖。这4项大奖均为高于金奖的特殊荣誉。
从艺30余年,曲滋娇执著于芭蕾艺术,与无数的中国艺术工作者共同构筑了充盈的人类精神家园。她是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文化部优秀专家、辽宁省“三八”红旗手、辽宁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当选为辽宁省第九届、第十届人大代表。2013年2月,她被评为辽宁省第二批领军人才。
哪怕正统艺术江河日下,哪怕低俗之风喧嚣尘上,曲滋娇追求高雅艺术,探求文化强省、强国之心始终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