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风骨
2013-08-04刘火雄
○刘火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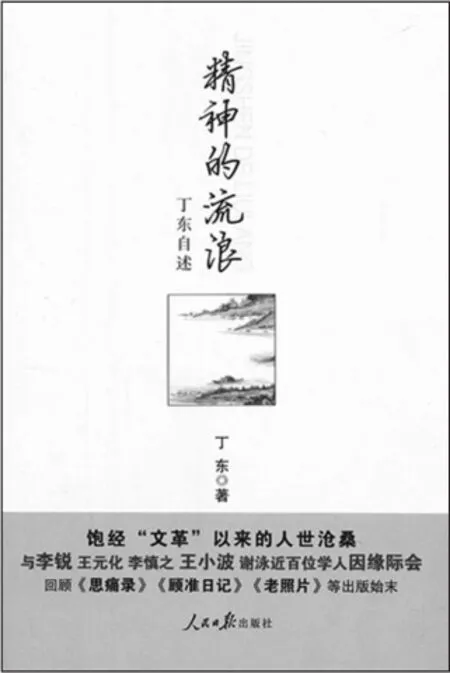
《精神的流浪:丁东自述》,丁冬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10月版。
真正的知识分子多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想起人类的未来,他们不时眼含孤独的泪水;真正的知识分子常持批判的眼光,一如北岛的回答: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中国语境中的知识分子谱系,追溯至古代往往让人联想到“士大夫”。中国士大夫矢志不渝的至高理想多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抑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民国以降,无论是胡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信条,还是梁漱溟“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担当……就其精神内核而言,他们与古代士大夫的终极追求一脉相承,与西方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也同声相应。
历经“反右”、“文革”等运动,中国知识分子一度集体沉沦,伴随着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大潮,新老知识分子再次觉醒。近些年来,许纪霖、林贤治、谢泳等学人对知识分子的议题各有研究。近年来,丁东编选出版了“背影书系”——《先生之风》《追忆双亲》《此生此前》《风雨同窗》,大多也关涉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人民日报出版社于2012年10月出版的《精神的流浪:丁东自述》一书,从传主自身经历及其与黄万里、李锐、王元化、王小波等学人的因缘际会,不难管窥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多种气度。
“文革”爆发时,丁东只是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的一名初二学生。因父亲是民主建国会的普通干部,母亲为中学实验室管理员,丁东既非“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很快被边缘化,以致常有一种不能充当学校“革命”主力的失落感。他只好在家属院里参加“革命”,跟着年龄大一点的学生发布通告,要求全楼居民主动交出“四旧”。丁东所在家属院居住的多为民主人士,100来户人家交上来的“四旧”堆满了整整一屋子,光书籍就不下万册,包括外文书、古书乃至成套的二十四史。
此后,丁东历经“知青”、“机关干部”、“大学生”、“编辑”、“学者”等身份的转换。为了重返北京,以便自主地进行学术研究,他选择了不参评研究员职称,并于1997年办理了退休手续。友人多有不解,当时他年仅46岁。
这位没有出版社的出版家,直接组织了《顾准日记》《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王申酉文集》的整理与付梓;间接促成了韦君宜《思痛录》、黄万里传《长河孤旅》、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等著作的出版;参与编辑的《老照片》文丛和三册《大学人文读本》等,都是文化含量相当高的精神食粮。
在谢泳看来,丁东的主要倾向始终是现实关怀和社会正义,他的所有学术工作,都保持着对现实的热情,他有关中国当代民间思想的研究大多是基础性的学术工作,这些工作虽然并不彰显,有时甚至是默默无闻的,其意义却极其重要。丁东曾在《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开设专栏,出版有《思想操练》《与友人对话》《反思历史不宜迟》等著作,或传播新知,或针砭时弊,在学术领域与社会现实中,他向来保持着“发声”姿态。
“没有比知道我们怎么努力也不能使情况改变这件事更使一个人的处境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的了。”哈耶克的这句断言正是黄万里人生的写照。人如其名,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水利专家,黄万里平生与万里江河紧密相连。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被提上议事日程。在70名学者、工程师参加的论证会上,众人噤若寒蝉。唯独年近半百的黄万里站了出来:“一定要修三门峡水库将来要闯祸的,历史将要证明我的观点。“一定要修,请别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便他年觉悟到需要冲刷泥沙时,也好重新在这里开洞。”寡不敌众,黄万里的意见被否决,不久后他被划为“右派”。宣布处分决定时,他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事后,有人问黄万里:明知说破会遭惨祸,为什么还要直言?黄万里坦言:“父亲(黄炎培)常对我说,‘中国有史以来,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统治阶级。’让我一辈子为农民服务我谨记着父亲的教诲,学水利,学治黄河就是想为农民服务。我不能看着要祸及农民不说话。至于为此而付出的沉重的代价,我一生无悔。”
20世纪60年代初,三门峡大坝建成并下闸蓄水,一两年之后,潼关河床淤高了4米多,淹毁良田数十万亩,渭河泥沙淤积直逼西北经济中心西安。此后多年三门峡工程沦为“鸡肋”,难逃不停被改造翻修的命运。这与马寅初“错批一人,多生三亿”的悲剧如出一辙。
与黄万里交往时,丁东对其水利思想感触深刻。在黄万里看来,正是黄河携泥沙而下冲积而成的黄河三角洲平原,养育着几亿中国人口。在此意义上,黄河非“害河”而是“好河”,“黄河清,圣人出”的想法不符合自然规律。丁东写道:“我忽然醒悟,河流也是有生命的,而黄老学说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能把河流当作活的生命来尊重。”
李锐曾任毛泽东秘书、燃料工业部水电工程局局长,无独有偶,他也曾反对三峡工程仓促上马。论证会上,李锐条分缕析,既分析当时中国还没有能力消化这样大的电量,也阐述防洪须堤防、湖泊蓄洪、干流及支流水库并重,不能用一座水库毕其功于一役,待时机成熟再考虑三峡这样的大工程。毛泽东采纳了他的建言。
李锐可以说服毛泽东放弃建设三峡工程,却不能预料自己的命运。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因同情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批评意见,李锐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打入别册20年,其中8年牢狱之灾在秦城监狱度过。复出之后,李锐写出《庐山会议实录》,其史料价值与反思深度,震动学界。
耄耋之年,李锐仍“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丁东给李锐写过口述自传,两人有过不少接触。据丁东记载,李锐每天不是阅读,就是写作,日记从不间断。这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使命感,令丁东非常感佩。
李锐曾手书条幅赠给王元化,内容为刘禹锡的《浪淘沙》:“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王元化很珍爱这幅字,将其悬挂于家中,这首诗恰恰是其跌宕人生的缩影。
作为一个“胡风反革命分子”,王元化冤案历经二十余年后才得以昭雪,长期的孤独与压抑使他一度患上心因性精神病。莎士比亚与黑格尔的经典作品,陪伴他度过了精神危机。1983年,王元化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丁东因为编辑《顾准文集》而与王元化结缘。他第一次与王元化见面,正赶上庆祝香港回归,电视台想采访他并请他发表感想。王元化说,不要采访我,这件事上我谈不出新的见解,而应景的话我是不说的。王元化还向丁东透露:他刚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时候,有人对巴金在香港报纸发表随笔反思“文革”很不高兴,于是通过上海市委让他出面做工作,想换掉巴金的上海市作协主席职务。王元化对市委书记说,你们代表市委作决定,我服从,但让我先提出报告,我不能干。最后,巴金作协主席的职务并没有被换掉。
德国学者沃尔夫·勒佩尼斯发现,“知识分子天生就是一个忧郁症患者,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无法使其理想具体化,因而陷入一种隐性的忧郁症中,或者躲藏在一个美好的想象世界的乌托邦中。”在“乌托邦”与“忧郁症”之间游走的知识分子,王小波算是一个典型。“王小波”这个名字就颇有意味,他的父亲王方名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逻辑学教授,就在王小波出生的1952年,王方名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家庭突遭变故,“小波”之名于是取意“小小风波”。
同样当过“知青”的王小波,自身也历经坎坷,特别是作品一度不为人所重的苦闷,常人自是难以体味。丁东与王小波夫妇相熟。有一次参加《湘声报》在北京举办的组稿会,丁东和王小波的座位挨着交谈中,王小波说:“银河是‘叛徒’,黄梅是好样儿的。”王小波与李银河的爱情佳话众所周知,两人情书集《爱你就像爱生命》还曾被出版。何来“叛徒”之说?原来,中国社科院评职称,一律考外语,李银河参加了考试,评上了研究员。按她的学术成就,这本理所当然。黄梅觉得让自己去考外语是一种屈辱,于是抵制了考试黄梅是英国文学专家,如此考外语,好比把成人送进幼儿园。
于平凡中发现世界的荒诞,正是王小波的深邃之处。当越来越多的人自称是“王小波门下走狗”之际,是沦为沉默的大多数,还是甘当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这种王小波式的追问越来越考量一个人的心灵。胡适当年曾感慨: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面对当今社会一系列喧哗与骚动,真正的知识分子一步步拱卒前进的精神更难能可贵。
如果说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那么很大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骨薪火相传、历久弥新,这足以让来者有理由相信未来,相信这个世界终将更加美好诚如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所言: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