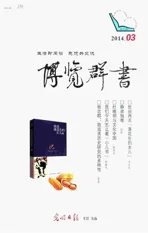我“认识”了银行家藏书家叶景葵
2013-08-04柳和城
○柳和城
面对《叶景葵年谱长编》初稿,轻轻地舒了一口气,我终于“认识”了这位银行家兼藏书家。虽则我三年前才接受年谱编著任务,但起缘得追溯到20多年以前。
由此及彼,张元济研究“副产品”
80年代中期,我有幸参加张树年任主编的《张元济年谱》的编著工作,首次接触到叶景葵的名字,并留下深刻印象。我案头小书架上就插有一本标注“叶景葵研究”的硬面抄,那是当年的“副产品”。硬面抄第一部分即《叶景葵先生年表》。一年一页,大都摘引自《叶景葵杂著》《汉冶萍公司》二书,也有采录自张元济史料的。后来陆续从《顾廷龙年谱》《上海银行家书信集》等书,又辑录得若干条目作为补充。诸如:
1898年 △春,入京春闱,援例报捐内阁中书。入通艺学堂,习英文、算学,听严复讲《天演论》。

叶景葵
1901年 △2月4日 撰《太康物产表·跋》。△本年 作报纸摘录,成《矿政杂鈔》等。
1903年 △叶去湘受委为学务处提调兼矿务局提调,“奉职勿懈”。△赵尔巽任盛京将军,叶随行,任奉天财政总局会办,“剔除积弊,未及两年,所入骤增。”
1907年 △本年 汉阳铁厂总经理李维格(一琴)见叶有志实业,以钢铁业有裨富强,邀往汉阳考察。
……
可惜很简单,有的年份尚付阙如。涉及银行的史料更少,除了几个浙江兴业银行职务头衔外,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内容。这份《年表》虽简,后来却派到了用场。我撰写《从书生到实业家——李维格其人其事》一文,就从中查到叶、李二人在汉冶萍任经理的时间及史料。硬面抄随后抄录按分类排列的几件史料,包括《郑孝胥日记》《盛宣怀传》《汉冶萍公司》《旧中国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关系史料选辑》《汪康年师友书札》等涉及叶景葵的内容。尽管并不完整,倒也脉络清晰。至于“孤岛”时期他与张元济等捐献各自藏书,创办合众图书馆问题,似乎更为详细一些。由此及彼,从张元济研究进入叶景葵研究领域,这也可谓我与这位银行家兼藏书家的一段渊源吧。因为有了这本硬面抄,20多年后我才敢接受此项编著任务。
叶景葵(1874-1949),字揆初,号卷盦,浙江杭州人,世家子弟出身。他的科举道路颇为顺利,29岁(1903年)进士及第,仕途也不算坎坷,清末先后任奉天财政总局会办、督军赵尔巽重要幕僚、天津造币厂监督以及大清银行正监督(相当于行长)等职。民国后他先任汉冶萍公司经理,1915年后出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一职长达30余年。从一名诗云子曰的书生到理财能手,再到现代实业家、银行家,叶景葵人生角色的巨大转换,正是晚清民国时期社会空前大变动的产物。正如熊月之为拙编《叶景葵年谱长编》所撰《序》所说:“任何社会大变动时代,都是社会大分化、利益大调整时代,对于身处其中的个人来说,也是适应能力大考验时代。不明大势、故步自封、抱残守缺者,或蹇滞,或落伍,或困窘;洞明大势、顺时应变、勇于进取者,则能抓住机遇,搏风击浪,勇立潮头。蔡元培、张謇、张元济等,都是属于后者,顺势明理、与时俱进。本书传主叶景葵先生,也是这样一位善于把握机遇、在多方面取得非凡业绩的成功人士。”我能为这样一位老前辈“树碑立传”三生有幸!
由表及里,从原始档案“寻宝”
按照年谱长编体例的要求,我那册硬面抄编的《年表》及摘录,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开始“寻宝”之历程。第一个目标是上海市档案馆。友人相告,上档拥有丰富的老银行档案,并均扫描成电子文本随时可以在电脑上查阅。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光浙江兴业银行的档案就达一千余卷之多!每卷少则几页,多则数百页。我对金融史本来就不熟悉,面对如此浩瀚、天书般的旧档案,不知从何着手才好,只能老老实实地一卷一卷阅读,来不得半点“走捷径”。我决定先从标有叶景葵或叶揆初字样的卷宗开始。
读几卷,我兴味盎然,彷佛进入了一个新天地,尽管对此还很陌生。我的夫人刘承陪我一起查阅。我们有分工也有合作。她分得的那部分卷宗,边阅边记下编号、内容,凡提及叶氏名字或事情的地方注明页码,随后由我复看,决定取舍。浙兴档案里关涉叶景葵先生直接、间接的史料比比皆是。翻读之余,如同亲聆謦欬,这位老银行家的身影越来越清晰可显,令人肃然起敬!简单的,我们当即抄录,制成卡片;内容重要或篇幅较长者,则记下页码,积累到一定程度打印出来,回家整理。寒来暑往,如此这般,自2010年春开始,我们俩在上海市档案馆阅览厅的电脑桌前忙碌了整整一年多,将浙兴全部档案浏览一遍,当年上海银行公会的卷宗也读了一部分,大有收获。
叶景葵与浙江兴业银行的渊源,始于清末。1908年后他曾一度“遥领”浙兴汉口分行总理之职,1915年开始担任董事长一职。他任董事长后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将浙兴总行由杭州迁至上海。这一顺应时代潮流的历史性决策,改变了浙兴的命运,也造就了叶景葵近代新式银行家的地位。档案显示当年浙江兴业银行对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扶植历程,既艰辛曲折,又相当生动。对上海恒丰纺织公司、枣庄中兴煤矿、汉口第一纱厂与郑州豫丰纱厂等当时国内重要实业,浙江兴业银行都予以大量放款,支持其生产经营。当这些企业出现危机,或发生纠葛问题时,叶景葵常常参与筹议,甚至亲自出马赶赴第一线进行谈判交涉。时值新老军阀此去彼来,向民营银行敲诈勒索,许多金融界人士不得不投身政治漩涡。而叶景葵与浙江兴业银行始终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即使遭到蒋介石辱骂也不为所动。因政府更迭,内忧外患,1914年浙江铁路公司收归国有之后应退还股东的末期股款,竟延宕达20余年之久。叶景葵担任浙路清算处主任一职,随之也达近30年。通过他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解决了问题,股东们以八折之价收回应退末期股款。其中艰辛曲折,令人感慨不已!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叶景葵作为现代企业家具有对公众的诚信意识及果敢执着的办事风格。
叶景葵作为近代著名藏书家和图书馆事业的促进者,历来受到藏书文化研究者的关注。上海图书馆继承合众图书馆的事业,收藏有叶氏生前捐赠的全部藏书。其中叶先生撰写在书上的题跋、校勘文字,早年已有顾廷龙主持整理出版,收于《卷盦书跋》《叶景葵杂著》等书之中,这次我根据原书电子文本又抄出若干篇,一一补入本谱。
叶景葵原藏文献类作品,以前知之甚少,现利用上图整理成果,从电脑库里查得一批有用的史料,编入本谱,填补了先生生平的不少空白。如叶先生早年笔记《矿政杂鈔》《卷盦政类钞》《甎屑录》等,反映了他青年时代读书求知、追求新学的众多侧面;《赵尚书(尔巽)奏议》由先生亲自辑录,他起草各篇均标有“景葵起草”字样,对于研究先生当年思想及其幕僚生涯,乃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史料;《汉行信稿》为先生1909—1910年期间任浙江兴业银行汉行总理期间通信的底稿,弥足珍贵(上档浙兴老档案里没有);《罪言之一鳞》乃是先生1911年任大清银行正监督的几个月中与各方通信存稿,显示了辛亥革命前夕中国金融业的一鳞半爪。另外,谱主精心保存的友朋书札《尺素选存》《叶揆初伉俪亲友手札》《蒋抑卮先生手札》等,本谱均加以详尽著录,使得这批原始档案重见天日,大大丰富了叶景葵思想与社会交往的研究领域,为同时代文化、实业相关历史人物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至于先生未刊书稿《卷盦藏书记》,不宜分割,于是决定作为本谱“附录”全文收录,以供藏书研究者参考。
述而有作,重在还原历史真相
编著年谱,重在史料。关于史料发掘、辑录的方法,我以为不能固步自封,而应与时俱进,充分利用新技术、新成果。《申报》数据库就是近年开发出的电子新产品,便于分类检索与稽考。我知道有这新鲜玩意儿比较晚,本谱初稿已经完成。我四处打听,方才知道数据库的大概。最后终于在友人丁小明的大力帮助下,从这里检索到100多条叶景葵相关史料。涉及谱主早年求学、科举、仕途等事迹,均可补充初稿之阙漏。即便民国后原先资料较多,现在发现的有关银行、浙路、反对内战、教育投资、捐款助赈,以及友朋交往等各种社会活动重要史料,又进一步丰富了谱主的人生,有助于对其思想及生平的全方位深入研究。一个活生生的、大写的人,透过这些史实凸显在我们面前。
有人认为,编著年谱应“述而不作”在某种意义上说,此话不错。但我以为年谱与其他学术专著一样,应当述而有作。史料的选择上就深深打上编著者的思想烙印。我在编著过程中,还有意将一些人物、事件背景材料作为注释形式,系于条目之下。值得一提的是,对少量回忆录失实问题,我则多花了许多笔墨,加以考订与辩驳。如1938年徐新六遇害后浙兴是否未给予抚恤,叶任董事长30年,是否“全权独揽”,“与蒋抑卮也因故而生矛盾”等关键性问题,我没有回避,均根据可靠史料予以澄清事实。不为尊者讳,但也不许他人在尊者脸上抹黑!
某些回忆录的失实,与长期以来历史研究中受左的思潮影响有关。近现代实业家研究,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人们不敢涉足的“雷区”。这一现象直至上世纪80年代方才有所改变。我也经历了这一转变过程。从张元济、穆藕初到叶景葵,我近20年历史研究及写作,阴错阳差,几乎都在为“资本家阶级”“树碑立传啊。通过实践,我产生一个信念——这些人物以前研究太少了,亟待加强,我能为此“大厦”添砖加瓦,深感幸运万分。这些同为民族脊梁的人物,过去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他们闪光的思想与事迹应当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今天我们从事经济建设,需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需要有模范榜样,张元济、穆藕初、叶景葵等人正是我们应该崇敬的先贤哲人,当代企业家们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无数闪光的东西。读者以为然否?
我通过读书、编著,“认识”了这位银行家兼藏书家,对其成才之路深感钦佩。叶景葵没有机会出国留学,却跳出科举窠臼,学英文,学数学,学金融,学管理。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他更注重社会实践经验的积累。正式上任大清银行正监督之前,他就先赴各地考察、调研,清末时代能有几人?浙江兴业银行股东会、董事会或重员会议,他作主持报告后,让大家发言讨论,集思广益,做出决断。上档浙兴这些会议记录,以及《兴业邮乘》(浙江兴业银行内部刊物)所载文献,就是证明。他反对内战,呼吁和平,在敌伪时期不为拉拢,保持名节,更为年轻一辈所敬仰。他还学健身养生,令人感动。他自幼体弱多病,自称“五劳七伤”,骨瘦如柴,面白如纸,然而经过不断琢磨健身养生之道,练习打坐,结果无师自通,很有成效。他曾练习米勒氏体操、太极拳和奔纳氏体操,也很有效。他60岁时自述云:“惟习奔纳氏体操后,二年余未曾伤风。向来夜间不能看铅印石印书,现在灯下以朱笔校书,作蝇头小楷,亦不觉累,跑山十余里,不至腿酸腰痛。此皆奔纳氏体操之效。”我认为,年谱编著中对于谱主生平细节的记述也不能忽视,因为这也是还原历史真相的一部分!
拙编编著过程中,得到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档案馆等各处许多朋友的热情帮助与指教,借本文刊出之际,顺以致谢。
《叶景葵年谱长编》今年上半年即将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届时望学界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阅后不吝赐教。自接受编著叶先生年谱任务以来,我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到叶先生的后人,以便获取更多信息,将书稿编得更为扎实些。无奈迄今为止,未能如愿,深感遗憾。这里我再次呼吁:知道叶先生后人的朋友请转告我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