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中国经济“双轮”赛跑
2013-07-12刘伟,朱敏
刘伟:中国经济“双轮”赛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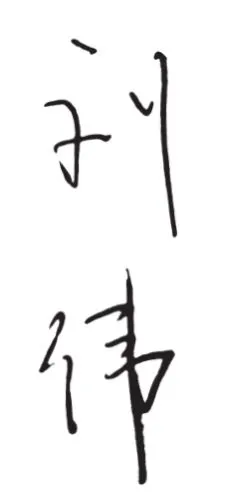
本期客座总编辑:
刘伟,著名经济学家,现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伟教授长期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当年被誉为“京城四少”(钟朋荣、魏杰、樊纲、刘伟)。如果说20多年前的刘伟教授对于自己的名利还有些许的惶恐,那么今天已经硕果累累的他依然谦逊。作为一个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享有很高声誉的经济学家,刘伟教授对中国经济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中国经济的“长短策”
《检察风云》:前些年,针对全球经济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措施。政府救市使大量资金注入国有企业,而中小企业岌岌可危。
刘伟:短期来看,当时主要是反失业和反衰退。短期内可能有困难,最突出的矛盾和威胁就是失业和衰退问题。中小企业作为中国就业的生力军,它们要出现了问题,就业保障失衡在所难免。
《检察风云》:据了解,中小企业承担了就业的四分之三,国有企业近几年非但不能提高就业率,反而在减少。在此期间,大量资金投入市场造成通胀,就业保障是否因此也开始失衡?
刘伟:中国经济实质上是“两个车轮”在赛跑,同一个举措形成“两个车轮”。经过一轮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下来,一方面拉动了需求扩张、经济增长;另外一方面,它也会推动各种成本的提高、带动通货膨胀。换句话说,在需求扩张的同时,它既有拉动增长的功效,也有推动通胀的作用。
中国当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可以考虑的策略是在一段时间里面,特别是在形成通货膨胀之前,经过经济增长的拉动,让失业问题能够短期缓解,使反衰退、抗危机取得一定的成果;等过了一两年,当通胀成为首要问题的时候,可以腾出手来集中治理通胀。所以,我们看到,之后为了缓解失业率,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未来的通胀压力。
关于中期,主要任务是反滞胀,因为有可能经济停滞,发展速度没有上来、失业率居高不下,另外一方面又通货膨胀。
《检察风云》:具体而言,之所以说中国经济中期可能出现滞涨,背后有着怎样的动态逻辑呢?
刘伟:短期政策实施之后,显示不了通胀,更多地显示拉动增长,但到中期就会表现为需求拉动物价。通常经过一两年的经济周期,带动了成本的提高,成本又在推动物价。如果一轮宏观调控举措下来,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拉动,失业率在短期内不能有效地缓解和降低,那么在过了这个时滞期之后,通胀就会表现出来。中国经济就可能出现一个非常复杂和困难的局面。
《检察风云》:要处理好通胀与滞胀的关系,在结构性政策上,应该怎样处理近期和中期的衔接问题?
刘伟:以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案例来看,刚才说了,当时的策略是:近期主要反衰退、中期主要反滞胀。意思是任务要先明确,近期就反衰退,为此即使加重通胀也值得——凯恩斯主义的菲利普斯曲线正是如此;中期就反滞胀,那只是一个和近期衔接的事情。衔接不外乎两条:一是先采取的措施一定要尽快地显示出扩张效应,假使对经济增长和反失业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那就麻烦了;二是如果取得预期效果,失业率很低,经济增长上去了,过两年有通货膨胀就不再恐惧,届时宁愿牺牲失业率换取通货膨胀的降低也可以。
《检察风云》:试图把两个矛盾打散么?还是在政策抉择上,在不同的时段,二者相权取其重?
刘伟:要看二者能不能置换得动。凯恩斯主义当时即是如此,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有个选择和替换:如果一个时段内,威胁最大的、首要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失业率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就要先解决通胀,为此所有的目标都要服从这个目标,宁愿降低需求、减少通胀,宁愿让市场疲软、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也要换取通货膨胀率的降低。政策就是要有重点。
假如在另外一个时段,中国宏观经济的目标不是通货膨胀,而是失业率,是经济停滞萧条,那么所有的问题都要为解决失业让步。到了这种情况,就要刺激需求,付出的代价是物价要上升,即意味这个时候政策重点的选择是要降低失业率,而不惜提高通货膨胀率。
为解决当前的主要矛盾可以牺牲次要矛盾,这就是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但也有人认为,为什么到上世纪70年代出现问题了呢?特别是当时中东战争、石油危机,石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涨到12美元(上涨了4倍),整个国民经济的成本在全球范围内提高,此时就出现了滞胀。这种局面实际上意味着,凯恩斯那一套已经失灵了。
从总供给角度调结构
《检察风云》:从总供给角度看,应该怎样调整宏观政策结构,降低就业率,来提高经济效率呢?
刘伟:宏观地看,物价总水平和失业率的提高并行就是滞胀。物价总水平、宏观问题讲的不是股市或楼市等某一个产品。
因为滞胀的局面很复杂,宏观政策选择起来也很困难,所以必须就要考虑:第一,这一轮拉动增长的效应能否尽快显现出来,增加就业,如果显现得越快,就恢复得越好(即使出现通胀),我们政策掉头时候的“本钱”就越大,就可以把宏观政策搞得很紧来治理通胀了,“弹药”充分;第二,如果通过一轮政策下去带来的增长不大,失业率不低,通胀一来就不敢大手笔地治理通胀,因为失业的压力太大了。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拉动增长的效应,对未来经济效率的提高至关重要。
《检察风云》:控制滞胀必须提高经济效率,那么未来滞胀的关键因素有哪些?怎样才能有效控制滞胀?
刘伟:的确,此时要特别考虑这一轮刺激经济增长的效率情况。因为未来出现滞胀的关键是成本提高,包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本品的价格、生产数据投入品(煤电运油、上游投入品)的价格。特别是在这儿,一方面资本品、稀缺品的价格在提高,另一方面,关键是人们掌控和使用的效率能否提高。滞胀的要害是成本推动的,那就是成本在提高,产出没有压住它,所以要特别突出刺激经济增长的效率情况,技术含量、投入产出比越好,未来滞胀的可能性就越小。
《检察风云》:调结构与提效率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刘伟:结构变化是效率提高的函数,即由于效率的改善,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效率改善的速度和程度不一样,使其在国民经济中成长的竞争力不同,然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就有了结构性的变化,包括地区结构、行业结构、企业结构。所以,结构变化是效率改善的结果。
这两者是中长期的事情,而不像刺激总需求那样,措施一下去就见效。
《检察风云》:结构的调整,是为了提高效率。此间,必要的衔接点有哪些?
刘伟:从总供给角度调整结构,提高效率,就需要技术和制度的改变。所以,要把近期和中期的任务衔接好,把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总量扩张和结构调整、速度提升和效率改善,统统衔接好。这才是在能够有效地保增长、扩就业的同时,避免未来中期出现滞胀的根本办法。
当时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意识到,近期威胁主要是衰退,中期主要是滞胀。治理衰退就是刺激总量需求,但是治理滞胀就不是总量的问题了,而是供给问题,就要有结构的变化、有效率,这样才能把成本降下来。
市场化方向不容逆转
《检察风云》:通过这些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考验,中国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还有哪些不足?一旦危机到来时,我们使用金融工具时可能出现哪些问题?怎样改进?
刘伟: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了。因为中国的货币政策肯定有问题,各个国家的货币问题都在通过这次危机自我检讨。有人认为货币政策根本就没有用,甚至认为危机是货币政策惹的祸,然后让财政政策来买单。
但在中国,说句老实话,不是货币政策不够松,而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有问题。整个社会制度,使得整个货币的扩张传递不出去,实现不了,这个是很要紧的问题,比如心脏需要供血,但是血管这儿被堵塞。这恐怕是未来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检察风云》:此外,对中国与世界的一体化问题您怎么看?
刘伟: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和发达国家一体化?我们有自己独立的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和西方的基督文明怎么一体化?我们有自己的社会制度的经济、社会、法律、行政制度,你和西方的制度怎么一体化?
中国要是真正进入西方的一体化,弄不好自己要蒙受更大的灾难,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一般我们不要撇开自己和国际的现实,去盲目简单讲一体化,像历史上东欧的一体化实践都证明是失败的。
但是要知道,不能由此而反对全球化。全球化一定是趋势,是遏制不住的历史潮流。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一定是全球当中的一部分,中国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一定是全球化的一个内容。这是对中国体制影响非常关键的问题。
采写:朱敏
编辑:程新友 jcfycxy@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