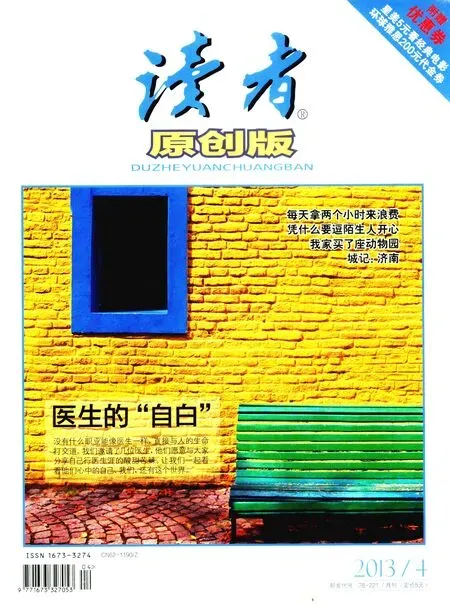今天,我们好好相见—专访蒋雯丽
2013-05-02王莹莹
文 _ 本刊特约记者 王莹莹
今天,我们好好相见—专访蒋雯丽
文 _ 本刊特约记者 王莹莹

只为记录一段岁月
有些女人的生命,如同一处深深掩埋的宝藏,你以为已经窥得华丽锦绣,其实万千光彩还在后面。蒋雯丽便是这样的女人。
北京的冬天,坐在温暖明亮的咖啡馆里,蒋雯丽和一帮好友相谈甚欢。她刚刚从片场赶来,马上还要奔赴下一个片场。时间对于这样的一线明星而言,确实是挤海绵。但在她身上,你看不到一丁点儿被时间追着跑的急躁,而是从容温婉,一如她在荧屏上的形象,无论是知性、极致、疯狂还是焦灼,都有一个共同的内核,那就是追求美,追求心的安宁。
此刻的她,素面,黑衣,短发被帽子压得略略变形。哪怕是在这家小小的咖啡馆,她也算不上闪闪发光的超级美女,却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令你无法移开目光。而这种力量,令岁月在她身上变成了营养。
你能想象吗?今天的蒋雯丽,除了是影视明星,还是一名导演,并且开始写书。2010年,她取材于自己的成长往事,首部自编自导的电影《我们天上见》摘得韩国釜山电影节“最受观众喜爱影片奖”;不久前,她将电影剧本改编成散文集《姥爷》,不过是童年记忆中的点滴小事,细细读来,却如同看到《城南旧事》中的英子,穿着红棉袄,扎着麻花辫,在“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淡淡忧伤中雀跃而来。
这样一场转身,谈不上华丽,却优雅温暖,因为它无关野心,只为完成一段岁月的记录。“以前每次听到妈妈说,哪个大大不在了,哪个伯伯走了,我心里都很难过,仿佛岁月也随着他们的消失而消失了。那些我童年熟悉的面孔、那些记忆的碎片,让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把它们定格在某一瞬间。”
从2005年开始写剧本,2008年开拍,3年之内30次易稿。写好之后当然首先给老公顾长卫看。“他觉得很好,超出他的想象,因为纯属成长记忆,没有那些花哨的东西,很有画面感。”
没有依靠老公,而是亲自操刀拍电影。为了如实还原故乡安徽蚌埠的画面,她对摄影师说:“能下雨的地方尽量下雨,画面要像中国的水墨画。”结果,一共120场戏,需要下80多场雨。这可难坏了所有的部门,因为雨戏是最难拍的。她请来的特效师刚刚从一个大制作影片中下来,带来了拍摄那部电影的全部设备,却沮丧地说:“那部影片才一场雨戏,你们这部80多场,设备不够。”
如果说当导演纯属完成个人心愿,写书则是“被逼的”。为了把电影作品推广开来,朋友们建议蒋雯丽把剧本变成散文集。“都是挤时间写,写得最多的时候是去年春节带老人孩子去三亚度假。安顿好他们,我就找安静的地方写,或者他们睡了,我抱着电脑赶紧写,有时写着写着他们喊了,还得停笔。”
虽说都是处女作,口碑却甚好,但她仍然是谦逊的,甚至略带羞涩。“真的吗?”她微笑着反问别人发出的种种赞美,如同一个没有自信的小女孩。不足之处当然有,情感仍是最重要的。“技术有不足的地方,但打动人心并不取决于这些,而是作品中有没有爱。”她说。
爱,令一个人变得特别
在影视圈,牢牢占据一线地位的蒋雯丽总有一些特别的味道。温婉、知性、优雅、淡定、从容……从《我们天上见》到《姥爷》,所有的形容词恍然有了根基—爱。
蒋雯丽的爱来自童年。父亲支援新疆建设,母亲工作忙碌,无暇看管她,因此从两岁开始,她便跟随姥爷长大。“姥爷和我,一个90岁,一个七八岁,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他扶持我长大,我陪他走完人生的路。一个生命像小树长高、长壮实,另一个生命却像一棵老树,慢慢地倒下,无声无息。我想把这种爱、这种生命的传承写出来。”蒋雯丽说。
这是一种怎样的爱?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不是可歌可泣的传奇,不是口香糖般廉价的花言巧语,而是渗透于时光,缓缓流淌于一箪食、一瓢饮、一缕丝的小事,琐碎到你几乎看不见。
比如姥爷给她补胶鞋:“他先用锉子,把破损处的周边锉平,再从报废的自行车轮胎上剪下一小块胶皮,也用锉子把周边锉平,然后,用烤热的火剪把胶皮粘在胶鞋上,把鼓起来的部位锉下去。”
比如她不小心把新棉袄弄上了泥渍,伤心欲绝中看到:“阳光中,烟囱炉子旁,姥爷戴着老花镜,托着我的棉袄,在炉火上烤,边烤边用小刷子一点一点地把泥刷掉。”
比如吃饭:“姥爷盛菜的碟子,永远是纯白色的,不带任何花色图案,因为白色的碟子才能衬托出菜的色彩和美。姥爷把菜盛进碟子之后,还会用抹布把白碟子的四边擦干净,让菜美美地待在中间。”
其实又何止姥爷,还有那些清贫却良善的街坊四邻,如同一首优美的田园诗:“张奶奶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看到小鸡下蛋。随着‘咯嗒咯嗒’的叫声,张奶奶晃动着她细长的身躯,准确无误地从鸡窝里取出一个热乎乎的鸡蛋,笑眯眯地让我摸摸,小心翼翼放进坛子里。”

童年照片

幼年的蒋雯丽和姥爷
……
没有戏剧冲突,没有生离死别,没有跌宕起伏,只有生活中的小事,娓娓道来。真的可以这么普通,这么渺小,这么平淡?曾经,蒋雯丽也有过怀疑,甚至无数次将剧本改编成扣人心弦的情节剧,但她最终选择了放弃,忠实于生活。而这种放弃,却无意中营造出另一种回归。
在豆瓣电影上,有这么一段影评:“最近跟着家人看了一部电影《我们天上见》。本来不抱希望,随便看看,但荧屏上的暖暖亲情感动了我。想着家里瘫痪的老人,我突然想让老人也感受到我年幼时他曾经给予我的温暖。我要我们在人间时尽心尽力,不要等到天上时见。”
在拍摄电影《让子弹飞》的间隙,葛优看到了这部电影。当看到由朱旭扮演的姥爷给10岁的外孙女小兰扎头绳时,他承认自己流泪了。“本来这应该是由妈妈完成的画面,没想到却由近90岁高龄的姥爷来完成。”
或许,我们每个人的童年记忆中都有这样一些温暖的画面,都有一个“姥爷”。我们也都以孩子的心打量过这个世界,听到风吹动树叶婆娑的声响,看到雨水从屋檐上倾泻如注,还有阳光的影子,从屋子的这边走到那边……
或许,我们所有的野心,所有的困惑,所有的不安,都能在这些画面中获得片刻安宁。
不要等到天上见
姥爷离开已经30年了。年复一年,每每回老家,蒋雯丽都会给姥爷上坟。
“每次扫墓我都会跟姥爷聊聊,说说委屈,有时还把自己说哭了。”蒋雯丽说,“其实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成功与否,姥爷都会很欣慰,都会无条件接受。这就是爱,爱自己的孩子,不管他有多丑。”
幼年时,蒋雯丽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体操世界冠军,长大后却成为一名自来水厂女工。正如电影《立春》中的王彩玲,她一直试图“走出去,改变命运”。考电影学院时,考官出了一道题:“讲一件你最难忘的事情”。“我想都没怎么想就上台了,讲的就是在医院里和姥爷的最后一面。讲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人都不存在了,像灵魂出窍一样,姥爷就在我眼前。大家安静极了,全都听我讲。后来听说郑洞天老师当时就说,这个学生我将来一定要用。”
如果说,每一个生命都有上帝派来的守望天使,那么这个天使对蒋雯丽来说便是姥爷。“姥爷一直在帮我,从小时候带我到考电影学院,再到今天拍姥爷的故事,我的每一步都跟姥爷有关,每一步都是爱。也因为这份爱,让我看世界的眼光没有那么功利、浮躁,而是相对单纯、平静。”
五光十色的演艺圈里,蒋雯丽人淡如菊。“我其实是个封闭的人,和演艺圈接触很少。在电影学院上学时,我就不会外出参加舞会等活动。刚一毕业我就结婚了,又走进了家庭这个封闭的世界。”
蒋雯丽与顾长卫的婚姻是中国影视圈的一段佳话。拍摄电影《孔雀》时,顾长卫曾骄傲地说:“老婆养了我5年。”一个儿子、一个领养的女儿,读的都是普通公立学校,坐校车上下学,穿的多是朋友送的旧衣服。儿子说没事儿,做母亲的她也觉得挺好。
电影拍完了,书写完了,她感觉自己对爱的理解更深了一层。“更珍惜了。父母一天天老了,不知道哪一天就走了,所以会更珍惜。孩子们一天天大了,很快就会离开你,所以会更珍惜。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每一天,买菜、做饭、陪孩子写作业,周末一起郊游、看电影,看起来平淡无奇,但这就是生活。”
在《离别钩》中,古龙写下:“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地相见。”
“不要等到天上见。”蒋雯丽说,“我们的爱,要在今天,要和身边每一个人好好相见。”

电影《我们天上见》剧照

电影《我们天上见》剧照
老公鼓励我当导演
《读者·原创版》:昨天我连夜看了电影《我们天上见》。若不是这次的采访任务,我肯定会错过一部美好的电影。这部反映你和姥爷的亲情之作、你头一次自编自导的电影、朱旭老人的封镜之作,知名度却不高,有没有感到遗憾?
蒋雯丽:我觉得投资公司给我这个机会,完成一部很个人化的电影作品,已经很幸运了。至于遗憾,当然会有,但这是我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因为市场完全是另外一个门类系统,作为创作者,我的精力只能顾及拍摄。国内的电影院是不分类的,文艺片、商业片都在一起放,所以我们这种片子的空间很小,放映时间要么是早上9点,要么是夜里11点,能放10来天就不错了。其实这类亲情片,我觉得应该模仿日本的那种院线慢慢放,像《那山那人那狗》,一放一年,靠的是长线,口口相传。但我们没有这样的影院,毕竟不是像《泰囧》那样的片子,大家一窝蜂去看,喜欢娱乐的人多。我也不是没有商业头脑,只是无能为力。
《读者·原创版》:为什么没有让老公顾长卫帮你拍摄,而是选择自己做导演?
蒋雯丽:就是他鼓励我自己导的。他建议我,既然剧本都是亲身经历,自己导会特别有感受。起初我还想着让他给我当摄影,他说如果他当摄影,人家会认为这是他的电影作品,不完全是我的,于是就给我推荐了一个台湾摄影师林朗中。他仅在剪片时给我提意见。
《读者·原创版》:他怎么评价这部电影呢?
蒋雯丽:这部电影是用胶片拍的,我很庆幸做了这个选择,因为胶片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进入历史了。电影的调光、配色完成之后,我让他去洗映场帮我对第一个电影拷贝进行技术把关。当时他邀请了另外一个摄影师一块儿去的。我很忐忑,因为那也是我第一次在大屏幕上看成片。他看完后很感动,特别由衷地祝贺了我,我当时真的很激动。
我希望带给大家一种暂时的回归
《读者·原创版》:从2005年到现在,似乎追忆姥爷、追忆童年时光占据了你生活中很大一部分比重。
蒋雯丽:这是我的一块心病。没做演员以前我就想写姥爷,但功力不够,难以实现。2003年,我拍了《中国式离婚》《好想好想谈恋爱》《爱过我放过我》,还有一部电影《台湾往事》,整个人都要崩溃了,于是2004年基本没有拍戏,完全调整自己。就在那一年,我想,身边的人包括自己都像蚂蚁一样,都在忙什么?活着是为了什么?要是明天真的死了,今天我们会为什么而感到遗憾?我告诉自己,首先,我喜欢西方艺术,于是就去了欧洲,一个博物馆一个博物馆去看,感觉真是太棒了!其次便是这个心病—表现姥爷,表现童年岁月。没有什么得失的考虑,哪怕做完以后得不到任何人的认可,却是我最想做的。于是,2005年我就开始写剧本了。
《读者·原创版》:当追忆变成剧本,感觉是否又有不同?
蒋雯丽:是的。除了怀念姥爷,我惊讶地发现中国30年的变化太大了。你看我们小时候房檐下接的雨水都可以淘米,现在自来水的污染却令人害怕;小时候我们吃的都是有机食物,虽然生活条件差,但姥爷还活到90多岁,很少有人得癌症,现在身边却动不动就有人得癌症走了。现在我们的物质丰富了,可人们的心态、幸福指数却在下降。那时候理想主义还没有消失,但现在的年轻人却不谈理想。所以我特别希望这部电影能带给人们一种关注,哪怕只是片刻的宁静、一种暂时的回归,回到我们曾经的生活。
《读者·原创版》:曾经的生活、那个时代的人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蒋雯丽:我的价值观是在那个年代确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这些都是很传统的价值观,现在我们却不这样了,这是很遗憾的。姥爷对人一视同仁、乐善好施,不管你是什么阶级类型,到我家都用很贵的茉莉花茶招待。记得有一个瘸子马爷爷,差不多每个星期三中午都要来我家要饭,每次姥爷都让我拿5分钱的钢镚儿放到他的破碗里。有一段时间他没有来,我们还担心他是不是生病了。直到现在,我在路上碰到要饭的一定会给,但大家总认为是假的,唯恐上当。对比姥爷那个时代,今天我们富裕了很多,但同时也丢失了很多。
我们的爱要往上走
《读者·原创版》:顾长卫导演曾经说:“拍《孔雀》之前,我被老婆养了5年。”这是真的吗?
蒋雯丽:他只是这样说,其实也在工作。当导演是很不容易的,我拍《我们天上见》就花了5年,如果不演电影,真是没法生存。我对他很理解,我们俩在精神追求上很多都是一致的,所以他去做导演,我就全力支持他。两个人在一起都这么久了,就像两棵树,树根都长在一块儿了。拍《最爱》的时候,一个朋友说,特别理解雯丽为什么这样支持顾导,因为他们俩的追求是一致的。当我做导演之后,更感觉到导演不易,尤其一些不完全去拍商业片的导演,想对社会有一些责任感,表达一些看法。今天我们却绝少有人表达对社会的看法,一切都是商业娱乐的,这是很可怕的。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我们要把这个变迁的时代记录下来,不管是给现在的人看,还是给后人看,都是非常宝贵的。这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所担负的责任。


蒋雯丽与丈夫顾长卫
《读者·原创版》:“我们天上见”,其实就是不要等到天上见。但是今天,我们却很难和身边的人尤其是父母好好相见。忙,算不算一个借口?
蒋雯丽:这部电影在深圳上映时,一位观众说,我们的爱都是往下的,爱自己的孩子,孩子再爱他们的孩子,而你却在回忆追溯,报答姥爷,是往上的爱。爱孩子是本能,爱父母却是责任,需要被激发。孩子也是从我身上看到如何对待父母老人的。我们每年春节都陪着两边老人一起过,平时尽可能和家人在一起。我拍戏时爸爸都会跟着,也算借机去各个地方旅行。他很快乐。
《读者·原创版》:不久前我看到一个数据:中国买房者全球年龄最低,平均27岁。可以说,“啃老”在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天经地义。
蒋雯丽:我跟孩子讲,我第一次拍戏是大学一年级,把挣的钱一半寄给爸妈,剩下一半留着做学费。大学4年我没有要父母的钱,自己寒暑假拍戏、勤工俭学,每次挣的钱都会把一半给父母。那个时候父母过的什么生活自己是知道的,所以很心疼父母,不想让父母再辛苦。现在大家条件好了,孩子看不到父母的辛苦,觉得父母挣钱容易,就不会有这样的感受了。现在中国的父母应该向西方富豪学习,给孩子留下最多的不是金钱,而是道德、精神、爱这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