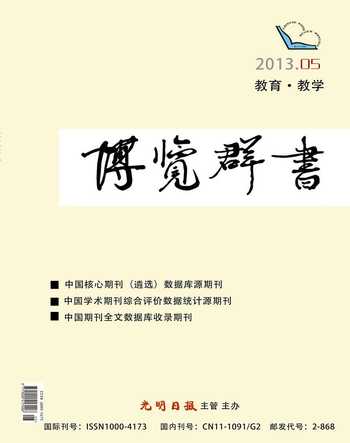刘庆邦《神木》的“审丑”艺术探微
2013-04-29冯琦
冯琦
摘 要:刘庆邦《神木》将形式丑和内容丑完美结合,在美与丑的辩证关系中巧妙地实现美丑转化,作品闪烁着神性指引和人性希冀的火光。从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四个方面观之,刘庆邦《神木》表现出的审丑艺术,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刘庆邦;神木;审丑特质;审美转化;审美价值
“短篇小说之王”刘庆邦被亲切地称为“民间代言人”,他是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煤矿题材小说钟情于“审丑”,最具代表性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中篇小说《神木》。这部作品曾获得“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多项殊荣。而“丑”作为与“优美”、“崇高”并列的审美范畴,并非一种客观的物理存在,而是一个“情景交融的意象世界,它有一种‘意义的丰满,是在审美活动中生成的”。正如葛洪在《抱朴子·博喻》所言,“贵珠出于贱蚌,美玉出于丑璞”,丑给人带来意义的丰满之感,在一定程度上比美更富有表现力。
一、《神木》中丑的审美特质
(一)形式丑:底层的符号
张法和王旭晓在《美学原理》中提到:“形式是对正常事物的偏离或者变形。”形式丑往往会与外形丑相联系,这种丑不涉及精神丑,是感性的认识。《神木》中人物形象来自底层,他们衣衫褴褛,灰头土脸。宋金明的道具,“一个用塑料蛇皮袋子装着的铺盖卷儿,一只式样过时的、坏了拉链的人造革提兜。提兜的上口露出一条毛巾,毛巾赃物得有些发黑,半截在提兜里,半截在提兜外耷拉着。”这一段描写,让读者在脏污的行李中感受到了形式丑。作品中这样的描写不胜枚举,作者通过感性材料形成形式丑,这个层面的丑是底层人民的符号。
(二)内容丑:人性恶的咒语
波德莱尔《恶之花》对社会的丑恶极尽描写之能,从恶中提取美,毫不留情地揭露社会的阴暗,诗中充斥着腐尸、蛆虫、毒蛇等令人作呕的意象,他曾说:“我的灵魂,像没有桅杆的破船,在丑恶天涯的海上飘荡颠簸!”[2]波德莱尔可谓是西方现代丑学、丑艺术的先声。《神木》中作者将丑的事物无所避讳地一一呈示出来,尽其所能地对传统的审美理想进行颠覆和破坏,内容丑与形式丑的结合。两个谋财害命的恶人本是普通挖煤民工,偶然间发现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谜底。作者详细写了两次办“点子”的经过,尤其是第一次,二人杀死元清平干净利落的血腥场面让读者触目惊心,在内容丑、精神丑的表现形式中吟诵出一段人性恶的咒语。
(三)丑的审美转化
《神木》中的丑的表现并非单一的,而是把丑作为一种逐渐转化的动态过程,丑与美在辨证统一的关系中逐渐契合。小说的题目“神木”是神性的审美符号,对“煤炭”的审美化转化。也正是由于神性的缘故,黑暗肮脏的煤窑被附着上了一层神性的是色彩,使得原本的丑在冥冥之中增添了一种宿命的味道。树叶到化石再到煤炭,这是自然界“死亡——再生”的转化模式,这其中蕴含了“死得丑恶”到“生得唯美”的审美转化,在生死转化中暗含着神性的指引。刘庆邦曾写道:“我给小说起名《神木》,也是强调任何物质都有神性的一面,忽略了物质的神性,我们的生命是不健全的,生活就会陷入盲目状态。有了神性的指引,生命才会走出自然的泥淖,逐步得到升华。”[3]《神木》就属于这里所言的酷烈小说,刘庆邦毫无避讳地书写着底层人民的生命状态。
二、《神木》中丑的审美价值
在大众媒体的大肆渲染和推波助澜之下,出现“审丑泛滥”的局面,有些作家作品打着“文学审丑”的幌子,殊不知早已进入了“恶俗审丑”的误区。然而,“文学审丑”的背后蕴涵的是对复杂人性的深刻思索,对底层小人物的亲切关怀及对个体生命精神的痛彻反思。《神木》中丑的所具有审美价值可从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活动的四要素进行阐述。
(一)世界:现实世界的反映
文学来源于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直观反映。“‘丑由于发掘和显现实际生活中某些人的丑恶的人性而生成的意象(即成为美),从而具有一种意义的丰满。”[4]此处所言的“丑”的意蕴是通过发掘和解剖人性的丑恶,来深刻反思某个群体或者整个社会的黑暗、腐朽和混乱。刘庆邦在报纸上看到矿工在煤矿上打死同伴讹诈抚恤金的报道,震惊不已,他萌生了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的想法。原本被苦难淹没的受难者自身成为制造苦难的刽子手,现实世界的苦难成为异化人性的罪恶道具。
(二)作者:个人价值观的表达
作者力图展示冷静客观的笔调来书写故事,可是在作品中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作者个人价值观的表达。《神木》作者在讲述这个罪恶故事时,流露出对社会价值观的失衡现象的深重担忧,以及人类对金钱的崇拜和渴求泯灭了良知的丑陋行径的控诉。故事结尾处王明君(原名赵上河)与张敦厚(原名李西民)同归于尽,并且让王风(原名元凤鸣)向窑主索赔两万块,嘱托王风要他“回家好好上学,哪儿也不要去了”。王风事后并没有向窑主讹诈金钱,作者在黑暗的故事中保留着人性救赎的期待。
(三)作品:艺术空间的延拓
“把美和丑都摆在美学的范围里并论时,就是承认美和丑同样是一种美感的价值”“美、丑一样是美感范围以内的价值,他们的不同只是程度的而不是绝对的。”[5]正如前文所说,美的事物的表现力是有限的,丑的事物具有更为广阔的表现力。《神木》表现了底层民工挣扎于前现代与现代、后现代社会的夹缝之间,遭受资本残酷盘剥,人成鬼、人变兽的人伦惨剧。
(四)读者:复杂人性的反思
丑的意象被读者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接受即是“审丑作品”的最大功效。尼采说:“艺术使我们想起了兽性生命力的状态:艺术一下子成了形象和意志世界中旺盛的生命肉体,性的涌流和漫溢;另一方面,通过拔高了的生命形象和意愿,也刺激了兽性的功能——增强了生命感,成了兴奋感的兴奋剂。”[6]在个体生命意识不断强化的当今社会,《神木》使读者重新审视人类兽性生命力的原始状态,充分认识到人性的复杂性,并对复杂的人性作出深刻的反思。
丑是最富审美现代性的范畴,刘庆邦的《神木》深入挖掘丑恶的否定性价值,以丑来发掘人性中非理性的力量,以酷烈的逾越来打破美的常态梦幻,让人类在原始生命本能的丑恶行径下无处遁形,在无处遁形的羞愧中睿智地颖悟和深刻地反思。
参考文献:
[1][4]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58.367.
[2]朱立元.西方美学范畴史·第三卷[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363.
[3]刘庆邦.给人一点希望[J].北京:十月,2004(05).
[5]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158.
[6][德]尼采.权力意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