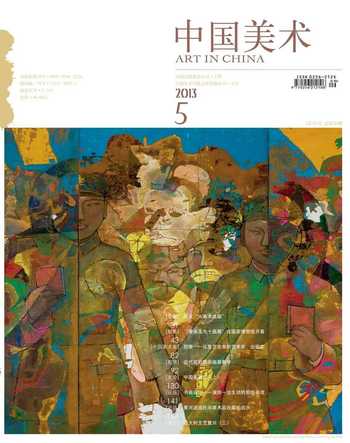新博物馆理论与后博物馆学
2013-04-29黄丹麾
一、博物馆与博物馆学
(一)博物馆
博物馆源自西欧,在英语中,Museum这个词是指“缪斯的崇拜地”(缪斯在古希腊神话中主司智慧,传说是由九位掌管不同艺术门类的女神组成),意指博物馆是一个向公众展示智慧、展示知识的地方[1]。1974年的哥本哈根博物馆年会为博物馆下的定义是:博物馆是一个不追求营利且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公开的永久性机构;它为研究、教育和欣赏的目的,对人类和人类环境的见证物进行收集、保护、研究、传播和展示。长期以来,这个定义成为国际上相对公认的定义[2]。
在当今文化中,博物馆的概念还包含着许多相互对立的意义。来自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艺术史学、历史学、哲学、语言学、文学批评以及性别研究领域的理论家们把博物馆视为各种伪装,但他们对这些伪装究竟是什么又持有不同意见。最常听见的是将博物馆比喻为圣地、市场主导产业、殖民化空间以及后博物馆。下面拟分而述之:
1. 圣地
人们想象博物馆的最持久、最传统的方式之一是将它作为一个神圣的空间。这是许多博物馆至今仍然追求的偶像意向。在圣地范式中,博物馆具有治疗的潜能。那是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离的神圣之处。博物馆藏品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作为圣地的博物馆声称它的展品为人们提供了精神启迪,使人们树立了柏拉图式的对美和道德的价值观。博物馆作为圣地范式取决于机构宣称的权威性的程度。作为圣地,博物馆时刻保护着它的珍宝。作为圣地的博物馆是仪式化之所,深受教堂、宫殿以及古代庙宇建筑的影响。大部分博物馆理论家相信将博物馆作为圣地是一种经营主义范式,并不满足当代文化的需求。
2. 市场主导产业
过去,博物馆一般认为它们的机构为藏品提供“纯洁”的环境,不受商业运营的玷污。但是,所有的博物馆都需要筹集资金来维持运转。博物馆主任、理事、发展部官员甚至馆长的职责都包括主要的资金决策。博物馆的运转资金主要有四个来源:政府(市政、州/地区以及国家)、公司、慈善基金以及私人慈善家。美国艺术博物馆的首创者出自19世纪富有的工业家,他们将艺术收藏看作他们自身的同时也是新美国成功、财富及力量的象征。美国艺术博物馆的建造很大一部分得益于个人捐助,这些个人的财产来自他们庞大的企业。第一批博物馆的创办者和开发者是J·P·摩根和亨利·克莱·弗里克这样的人,他们将自己看作工业巨头,并且视艺术收藏和赞助艺术为另一种建立他们历史地位的方式,此举在当时也的确为他们争得了地位和带来了愉悦。他们创立了建立在公司结构上、由私人当地董事会管理且由私人投资的艺术机构[3]。美国以外的博物馆过去能依靠政府资金来满足自身的需求,但是近期的政府财政紧缩迫使它们开始采取美国的模式来自救;这样一来,所有的资金来源都需要获得回报。企业通常要求将它们的商标标注在博物馆广告、横幅和标志牌的显著位置。慈善基金会要求他们资助的博物馆项目来补足他们自身的目标。私人慈善家则要求在他们过世后拥有一个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边房,博物馆会为他们的收藏品举行名誉展览,他们能在精英人物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捐赠的藏品会以特别方式进行展出。在当今经济形势下,许多博物馆对它们的经济现状变得更为开放,而且采纳了商业模式来获取充足的收入。为了给游客提供便利和增加额外收入,博物馆开始设定接待区域:餐馆、咖啡店、商店、书店、自动取款机、衣帽间、休息室、校园社团区、儿童区、教育中心以及剧院。
3. 殖民化空间
许多评论家将博物馆视为殖民化空间,从事着定义人群的分类过程。他们根据于后殖民理论,该理论研究了帝国主义和父权结构是如何形成以及继续形成文化,还确认了变革的策略,该理论认为:“展览是有特权的舞台,展示着自我与‘他者的意象。”博物馆理论家认为,博物馆构建了“他者”,从而来构建“自我”以及使其合理化。在展览来自非西方文化的展品时,博物馆展示更多的是宗主国的价值体系而非殖民地的价值观。因为博物馆强加了有关种族、种族划分以及性别的等级制度,将它们编码成机构,有效地将具有帝国主义强权的白人(男性)公民(自我)对抗被征服者(他者)的状态统一起来。作为殖民化空间,博物馆自然将非西方文化处于拘禁的发展状态,并冰冻在时间的洪流里。作为通过博物馆的帮助而建立起来的历史霸权,欧洲中心主义成为考古学、艺术史、博物馆学的遗产的同时,也成为批判的对象:“尽管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被视为西方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但是没有欧洲人挺身而出,声称欧洲之外的文化也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相反,殖民地的考古常常被用来展示所谓主流文明的优越性,这一传统在欧洲白人社会和北美社会达到顶峰。在其他地方,古老的遗迹被看作是土著文化随后退化或是更早的欧洲文明被野蛮的当代人所淹没的证据。”[4]
4. 后博物馆
后博物馆立足于后现代背景下博物馆的新变,对传统博物馆予以了颠覆性的质疑。比如,后博物馆理论家否认视觉艺术品能够还原历史及其情境,认为“博物馆将艺术从其语境中脱离出来,就毁了艺术”[5],艺术只有保持在原初的背景上才有完整的存在,对艺术品的保护不只是要求挽救这一对象,而且还要维护其原初的语境。批评家常常说,博物馆屠杀了艺术,“只要艺术健全,创造力蒸蒸日上,那么博物馆就永远不会出现。博物馆不过是艺术的坟墓,是把曾经为活物的东西的残余乱埋一气的茔窟”[6]。博物馆怀疑论者常常认为,没有生命的艺术品只有在观者的凝视之中才能获得生命。当然,也有观点指出,博物馆怀疑论者为传统提供了一种可怕的、非历史性的画面。有时,博物馆解放了艺术,让我们得以目睹那些原本隐藏或未被充分欣赏的绘画与雕塑的各个方面。正如汉斯—乔治·伽德默尔所说:“一旦艺术的概念具有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特征时,艺术品就开始独立,与其原来的生命语境相分离了。只有这个时候,艺术才确确实实地变成了马尔罗的‘无墙的博物馆中的‘艺术了。”[7] 也就是说,后博物馆在质疑传统博物馆的同时,其自身也同样受到新的质疑。
(二)博物馆学
19世纪中叶,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博物馆的历史和现状、博物馆传播知识、普及教育、娱乐公众的功能等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
20世纪30年代,博物馆学研究进一步发展。1934年,国际博物馆事务局出版了两卷本《博物馆学》,并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它促进了各国博物馆学的研究。博物馆在普及教育、传播文化方面的作用,日益得到普遍重视。至此,一门专门研究博物馆的学科——博物馆学应运而生。
所谓博物馆学就是指研究博物馆的性质、特征、社会功能、实现方法、组织管理和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律的科学。博物馆学的研究对象是保存、研究和利用自然标本与人类文化遗存以进行社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包括博物馆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也包括博物馆社会功能的演进、内部机制的运营和相互作用的规律。
博物馆学属于社会科学。它涉及并吸取了许多学科的相关内容,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都同博物馆学相关。这门学科与博物馆的实践结合得十分紧密。博物馆是一种社会文化教育设施,它的发生、发展和所从事的各种活动受社会需要的支配,并为社会条件所制约。因此,从整体上看,博物馆学属于社会科学。
博物馆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具有很多分支学科。它的分支学科包括理论博物馆学(主要探讨博物馆的基本性质、社会功能、特点以及博物馆与社会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历史博物馆学(探讨博物馆事业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以及博物馆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性质、作用和特点)、博物馆技术学(研究博物馆藏品的征集、鉴定、分类编目、保管、修复、陈列展览的设计、组织以及对观众的服务、教育等工作的原则和方法。它们分别发展为藏品管理学、陈列学、博物馆教育学)、博物馆管理学(从宏观上研究博物馆事业的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规划和管理制度,从微观上研究博物馆内部职能、机构组织、人员配备、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普通博物馆学(综合上述各个分支学科进行研究的学科)、专门博物馆学(是把一般博物馆学的理论与技术应用于某些专门博物馆领域的学科)等。
二、新博物馆理论
新博物馆理论,有时亦称批评性博物馆理论或新博物馆学,宣称尽管工作人员将政策和程序作为一种专业实践予以采纳,但是他们做出的种种决定实际上反映了根植于社会制度叙事中潜在的价值体系。理论家提倡将博物馆从崇拜与敬畏的角度转变为对话与批评反映的立场,他们展望着一种新的博物馆,在决策制定上透明,而且甘愿分享权利。新博物馆理论提倡的是非殖民化,使之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文化遗产,它同时还关注真正的跨文化差异。
伴随着彼得·弗格(Peter Vergo)于1989年发表的文选《新博物馆学》,新博物馆理论作为一个新兴领域正式进入学术领域。弗格与其后的又一代博物馆理论家深受20世纪60年代初期艺术家们的影响,这些人宣称所有的呈现都具有政治性,而且通过他们的作品明确地阐述了博物馆批评。在动荡的60年代,社会被贴上了不信任的标签,艺术家们开始寻求一种声音能够使他们的作品得到合理的展览、诠释和保藏。受到民权运动的激励,他们挑战原有的博物馆,使其变得更具包容性,接纳女性和有色人种艺术家的作品。他们寄希望于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展览来改变艺术的形式,这同时表明他们需要改变展览的空间。他们还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的文章,因为他认为氛围和权威都是社会结构部分,与21世纪的文化不相适应,也毫不相关[8]。
三、后博物馆理论
艾琳·胡珀—格林希尔(Eilean Hooper- Greenhill)利用“后博物馆”这一术语来显示机构已经彻底改造了自己,不再是一个“博物馆”,而是一个全新的东西,但是又和“博物馆”密切相关。后博物馆理论清晰地阐述了议程、策略和决策制定过程,而且以承认再现政策的方式来不断地重新评价他们:博物馆员工的工作不再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而是被看作对议程的一种贡献。后博物馆活跃地寻找着与它服务的机构——包括来源机构在内——分享权力的机会。它认识到参观者不再是被动的消费者,而是开始理解它的赞助者。后博物馆理论敏锐地聆听和对此做出反应,鼓励不同的部族成为博物馆对话中的活跃参与者,而不像过去那样灌输给大众参观者。但是,在后博物馆建设中,馆长不再是推动者,而且对展览负责,因为她或他从事着评论调查的工作。后博物馆的主张不会回避棘手的问题,相反会暴露对立和矛盾。它宣称机构必须展示含混性,承认其多样的、变幻莫测的特性。最重要的是,后博物馆的主张是矫正社会不平等的一片领域,后博物馆的支持者们认识到孤立的博物馆参观不会激起变革,他们不希望这平等的舞台最终变为博物馆宣称社会控制的另一种方式。他们仍然幻想着后博物馆理论能促进社会理解。希望博物馆成为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共同空间,它们在参观者的注视和记忆中相互抵触,同时展现它们的异质性,甚至是不协调性,像网络一样联系,相互杂交和共同存活[9]。
四、新博物馆理论和后博物馆理论对传统博物馆的质疑
新博物馆理论和后博物馆理论并非一家之言,而是包含了各种观点的方方面面。其中最富争论性的是博物馆的改变问题。究竟是博物馆在变化还是对诡异的变化做出附和之声?博物馆能够改变吗?它们是否陷入时代的洪流,受到精英文化的限制?或者它们一直处在变化的过程中?新博物馆理论和后博物馆理论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学界的争论。
怀疑者的立场是:博物馆不会(不能)改变。米克·巴尔(Mieke Bal)和卡罗尔·邓肯(Carol Duncan)等一些理论家相信博物馆仍然遵循着福柯式的现代或训练模式。许多人都引用由社会学家皮埃尔·不迪厄与阿兰·达尔贝在1969年的经验主义来做有远见的分析:博物馆可能正在为消费介绍新的空间、展览、教育计划和机会,但是,它们内在的依然是精英主义机构。它们使决策过程变得晦涩,避免审视自己的历史,它们立志将“公众”统一起来,而不是承认多样的和善变的身份。它们设计了一个参观者理应符合的游客形象。它们继续吸引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上层阶级观众,对边缘人群依然采取不闻不问,甚至是胁迫的态度。詹姆斯·库诺(James Cuno)坦率地声明,艺术博物馆只对少数相关的人(约占人口的20%)感兴趣。根据怀疑者的观点,尽管对主题和审美的实验悬而未决,大多数展览根据宣扬进化性改变的经典执行着传统的组织工作。展品与原来的语境的关系被切断,被当作偶像供奉起来。人们依旧是通过西方文化价值的镜头来诠释来自非西方文化的人造物品。保护的主体性很少得到承认,新科技并非创造真正的互动经历,而只是将参观者转移开,防止他们提更多的关于博物馆权威性和真实性的问题。当新的开创性活动真正发生之时,它们常常会出现在短期展览领域,通常不会对博物馆本身产生实质性的改变。有少数理论家认为,博物馆从其定义上来看就是不能改变的,而且它们很快就会过时。展览行动仅仅是将等级制度强加于人的一个政治过程。
乐观者的立场是:博物馆会(能改变)。他们认为博物馆是个有争议的地点,并对博物馆的理想化提出了警告,因为解构传统价值体系才刚刚开始而已。许多理论家将逐渐涌现的“私人”博物馆空间对公众开放视为一种健康的迹象,它至少能让博物馆占据一个更为民主、更为开放的“第三空间”,超越了精英主义和消费至上。这些成型的后博物馆通过这种开放式能够形成新的合作关系,来表达他们与他人分享权利的迫切愿望。这些理论家深受众多机构的鼓舞,从临近的博物馆到社团中心,再到大学美术馆,他们都是新近才建立起来并被赋予新生命,以多样性的视角来反映种族、阶级和性别。这些机构很可能采用后博物馆的理念,因为与其他已确立的百科全书式的收藏品相比,它们能够承担更多的风险,能够与其他机构开展创造性的合作,以此来满足它们的财政、学术、收藏以及展览的需要。有时他们会引进顾问,这不仅是为了节约全日制员工的薪水,而且是为了从无矛盾的局外人那里获取关于它们机构的更多洞察力与建议。
博物馆作为“伟大”收藏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多数西方艺术中的经典藏品已经成为公众收藏。大多数博物馆在获取展品或者是接受赠送之前,对该藏品的出处都会做详细的研究,因为这涉及一件展品的所有权历史。如果中间存在非法活动的问题,大多数馆长为了避免潜在的诉讼问题或遣返要求,他们都不会办理这项手续。作为该趋势的一个结局,这个观念在许多博物馆中已经比展品本身更重要。当馆长将这个观念看得优于展品本身时,他们就解构了这个过程中的经典。装置设计以及文本制造了联系并引发了评论性调查。照片、图形以及视频为人们提供了机会,同时支持了多样化的观点。一些博物馆正在纠正以前被忽视的一些问题,如家务、家庭及性。新兴的后博物馆理论正在以文化敏感方式来对待非西方展品。
许多博物馆理论家相信后博物馆中最为重要的上升趋势是机构与观众之间关系不断发生变化的特性。理论家引用了教育学家的新理念,即使是在一些比较保守的博物馆如大都会博物馆,也对观众采取一种新的尊重态度,将机构和参观者放置在一个更为平等的地位。一些博物馆正在采取协调性的努力,通过评价参观者的经历来理解它们的观众。它们采用“前—后”评价观来反馈参观者提出的建议,不仅在展览之后还包括展览之前,因此展览变得更加完整。它们支持教育研究,因为它使博物馆经验理论化。它们承认多样化的学习风格,同时提供用来实践的多种方式,如讲座、表演、在线展览、视频、艺术辅导班、工作间以及一些现存的历史剧院。现在达成了一种共识:参观者通过他们自己的经历和价值体系的视角来改变博物馆。因此,一些博物馆正优先考虑交流,并将其作为一个目标来看待。
在新兴的后博物馆主张下,教育家与其他员工(包括馆长和展览设计者)成为一个通力合作的团队,来制作展览和调整计划以满足观众的多样化需求。博物馆员工避免了将支持者在项目的初始阶段就拖入辩论的危机。员工还产生了构成主义学习机会,能使参观者在开放式教育经历中成为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如今,教育家使用科技手段,采用革新的方式来展现展品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他们设计恰当的新式媒体帮助参观者提出问题,挑战他们的偏见并刺激对话的产生。博物馆网页尤其能提供新的方式来和博物馆之间互动,为参观者提供了进入博物馆内部和了解其工作方式的机会;在博物馆提供的讨论版中,参观者能在此与博物馆员工直接交流,甚至对展览本身产生影响[10]。艾伦·瓦拉赫(Allen Wallach)在对美国博物馆和展览的研究著作《展示矛盾》中,十分关注艺术机构在更广泛的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包括这些机构如何具体地表述、再现某些社会的冲突与矛盾,他的兴趣在于这些机构作为意识形态的制造者和传递者的作用,其中包括对艺术史和作为民族历史和国家历史的美国历史的不同解释。同时,他注意到尽管博物馆“是非常保守的机构”,意图生产“历史的永恒不变的形象”,但有些博物馆“做出了妥协,甚至鼓励对艺术史和美国史采取修正性质的方法”。瓦拉赫指出,艺术馆“将其藏品神圣化”,“在恰当合乎形式要求的环境中展示的艺术品成了高级艺术和社会至高无上的理想”[11]。瓦拉赫宣称对现代博物馆的认知理解上存在两个相互关联的恶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博物馆在观众和展品之间建立起的各种关系(历史的,意识形态的),“设计展品的摆放位置”。第二个层面是建筑本身是如何从历史发展演变而来的现代性的表征。现代艺术馆内在组织和现代艺术展览“制造出证实这一美学的现代主义历史”[12]。瓦拉赫的文章表明,艺术馆的任何展览同样也是一种阐释,这种阐释部分源于展览自身的环境背景:“这不是纯粹的视觉问题——如何成为视觉——而是视觉意识形态的问题。周围的办公楼,特别是公寓大楼,本身就是艺术馆的组成部分,它强化了过去和现在的对比,强化了封存于历史的乌托邦希望和晚期资本主义当下的无特定指向的活力(unfocused dynamics)之间的对比。”[13] 新的艺术实践、新的展览方式、新的策展机制、新的文化思潮、新的美学原则必然会对传统博物馆予以挑战和颠覆,因此由传统博物馆、博物馆学走向后博物馆、后博物馆学是历史的必然。
伴随着博物馆学的发展,美术馆学的建构也势必提上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在《美术馆工作暂行条例》的总则中对美术馆的概念这样界定:“美术馆是造型艺术的博物馆,是具有收藏、研究、陈列展览美术精品及相关资料,向公众进行审美教育,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等多项职能的国家美术事业机构。”[14] 由此可见,美术馆作为博物馆的一个专门机构和美术事业机构,已经无需质疑,那么美术馆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呢?尽管界内对此还有争论,但是卢先生的专著《中国美术馆学概论》的问世则标志着中国的美术馆学研究已经启动,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门学科必能日益走向成熟。
(黄丹麾/博士、《中国美术馆》编辑、《艺术视野》执行主编、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客座教授)
注 释
[1] 张子康、罗怡《美术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10。
[2] 卢炘《中国美术馆学概论》,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20。
[3] 滕守尧主编《全球化的美学与艺术》,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97。
[4] [美]南希·艾因瑞恩胡弗著,金眉译《美国艺术博物馆》,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3。
[5] [美]大卫·卡里尔著,丁宁译《博物馆怀疑论》,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66。
[6] 同上,第72页。
[7] 同,第82—83页。
[8] [美]珍妮特·马斯汀编著,钱春霞、陈颖隽、华建辉、苗杨译《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导论》,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7-8。
[9] 同上,第23-24页。
[10] 同上,第37页。
[11] [英]乔纳森·哈里斯著,徐建译《新艺术史》,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48。
[12] 同上,第50页。
[13] 同上,第51—52页。
[14] 卢炘《中国美术馆学概论》,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