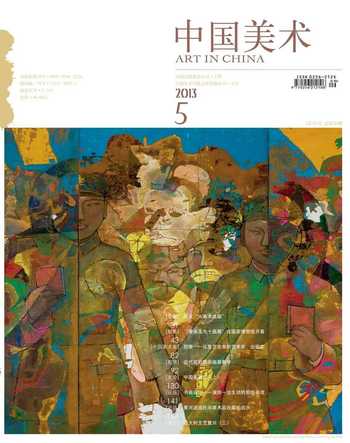市场机制下职业画家的历史地位及影响力
2013-04-29燕敦俭
燕敦俭
提起职业画家,很多人会想起那游走于江湖的卖艺人士,甚至有人会给职业画家冠以不好的名称。有些学者也在著作里提到职业画家如何为糊口而作画,并且和那些以模仿某人名迹的行画作者混为一谈。由于历史的原因,职业画家已经离我们有了一段距离;但在国家改革开放后,中国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许许多多的人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走出来,投入市场机制之中,这其中也包括一些艺术家。自20世纪80年代迄今的30年来,职业艺术家们走过了风风雨雨却没有真正走出自己的阴霾,这里有自身的某种弱点,更多的却是因为体制结构还没有真正破冰,致使职业画家始终处在一种无奈的状态。职业画家在历史上是如何生存的,它具有怎样的影响力,如何给职业画家定位,反观今天,我们又应该怎样看待职业画家,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
所谓职业者,必须是以所从事的行业来谋生方可称职业。在人类私有制产生以后,生产就有了分工,百工的概念大约来自周朝。周朝以前,行迹难考,虽有分工,也大多不够稳定。周王朝建立以后,王都固定,建制分明,所以分工明确,承接有绪,许多姓氏来自百工,就是证明。因此周朝职业人,一如今天的政府的上班族;唯一不同的是,今天的画家们大都是工作之外才成为画家,或者可以说业余才从事艺术研究。即使在画院、美协、美院之类的单位上班,也首先是完成展览或教学任务,才可以自由地去画画。所以,若从专业角度讲,这些人的专业并不是画画而是工作,是为官方的文艺宣传和文化教育事业而奋斗。若从体制外和体制内讲,那时是大政府,而几乎没有社会,因为只有绝对权力和绝对无权利两个阶层,有权利的人可以绝对享有无权利人的生产成果,很显然,中间的流通环节几乎不存在。百工是职业人,也是奴隶,朝廷设有管理百工的官吏,平民则有自己的奴隶生产生活用品,若有交易,那也是地主与地主之间互通有无,生产者无权交易。
职业人能用自己的产品进行交易,那是奴隶权利身份提高、平民阶层逐步扩大、社会需求逐步增加的结果。这时的百工后代们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但很辛苦,因为不拥有田产,他们只能用产品交换衣食。和诸多从事务农的专业生产者一样,种田的没饭吃,织帛的没衣穿,卖履的没鞋穿,因此百工的职业通常被人瞧不起,他们仍然在贱民的行列,自然画家也在其中。虽然他们的用武之地有限,那时尚没有独立的画种,但是他们创造了绘画史是极有可能的。这样看来,这些职业画家的先辈们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不高的,因为他们极有可能会归类到匠人行列,或者工艺美术师之类的工作者队伍里去。
产生真正的职业画家是在汉朝以后,这仰赖于文字文明的普及,官佐对文字的研究、掌握不仅出于工作的考虑,而且源于对美的追求。如汉代的张芝,为了创造出更美的书法作品,他甚至放弃了做官。这时绘画也成了官佐们的兴趣爱好,书画同源之说也就应势产生了。有了官佐们的带动,职业画家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甚至可以进身到官佐的行列。当然若从传说的角度上讲,真画者产生的时间还要提前,例如《韩非·外储上》提到的为宋元君画画的“解衣盘礴”者,这些人都是民间的职业画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叙画之兴废》记载:“汉武创置秘阁,以聚图书,汉明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立鸿都学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正象汉乐府采集民间音乐一样,皇家对图画的收藏也会引发民间艺人的创作热情。但历史记载的缺失,使我们无法知道那些作者的姓名。汉代的大量墓室壁画及记载中的宫室壁画作品恐怕多数还是来自民间的职业画工。
魏晋时期,艺术走向自觉。我们可以看到顾恺之这样的艺术大家的出现,同时还有卫协、史道硕等人。南朝时期的画家见于记载的更多,如陆探微、张僧繇、宗炳、王微等,这些人的身份都很特殊。如顾凯之,虽然做过参军,但他的身份还应是画家;而像史道硕、陆探微、张僧繇等人更像是职业画家。而宗炳、王微则不仕,却于绘画有其卓越贡献。因此我们虽不能断定他们是职业画家,但那时的生活较为安定和富足,不会以画画谋生,但在绘画研究方面有极大的建树。以上这些人均见于历代画论的评述,是绘画艺术的先驱和开拓者。
唐代的职业画家很悠闲,因为有达官贵人争相延聘,画家往往因一技之长,获得丰厚的报酬。唐代的文艺事业非常开明,画家活跃在寺庙,或者宫廷,或达官贵人之家。这在画史的记载里有很高的出彩率,没有歧视,没有成见,谁画得好,彩头就给谁。就连皇帝和王子都参与到画画的事务中去,因此反而推动了画画事业的发展。只是后来画史的编纂者,碍于公权力太过强硬,才往往把些地位显赫的人排到头位,但评价却很笼统,远不及提到职业画家那么兴奋。
宋代对待职业家的态度是,只要你画得好,我就收编,就像对梁山泊的好汉招安一样。如《图画见闻志》载:“燕贵,本隶尺籍。工画山水,不专师法,自立一家规范。大中祥符初建玉清照应宫,贵预役焉。偶暇日画山水一幅,人有告董役刘都知者,固奏补图画院抵候,实精品也。”每每画院的大门向民间打开,采用考试的办法收编人才。当然,画院也会培养自己的专业人才,采用师徒相授的办法,如《千里江山图》的作者王希孟就是画院自己培养的高材生,他曾得到宋徽宗的亲授,可见宋朝的画坛也很开明。开明带来文化事业的繁荣是自然而然的事。除了像苏轼和米芾这样的业余画家之外,宋代的大部分专业画家都很敬业,所以整个宋代,好作品、大作品不断,名家辈出。但要指出的是,画院收编终归是有限的,翻看宋代画史,职业画家的数量是惊人的,他们借助正规的画史被记录下来,可见我们的文化传统是公平的,并没有因为当时许多画家无编制而受到歧视。在此之后,朝野的界线分明,职业画家的业绩达到鼎盛时期,这就是元明时代。
二
“元四家”都是职业画家,四人中只有王蒙晚年短暂出仕;黄公望也是做了一段时间的“临时工”,却因上司犯罪被诛,吓出个神经失常来;倪瓒和吴镇都是以画画为职业。和明代职业画家不同的是,元四家的职业生涯以寄寓为主。但当时职业画家确实有做得很好的,与王蒙比邻而居的盛,就是个比较成功的画家。王蒙的老婆有“红眼病”,她见邻居的生意好,就对王蒙发泄不满。王蒙说,别看他现在得意,将来我比他强多了。王蒙说这话时,有多少自信不知道,大约他的职业生涯也不怎么样;所以当明朝建立后,他以高龄出仕,却落了个下狱屈死的下场。这一段,后人很少有述及,大约还是出于界定他是职业画家的立场。
很显然,做职业画家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但那时是异族统治,文人的地位是很低的。更何况,作为南方人,属于第四等人,受不了窝囊气的就放弃身份,过着流寓生活。郑所南是,王冕是,倪瓒也是,黄公望49岁那年始学画,也不过十来年光景,却创出惊人业绩,一幅《富春山居图》掀翻画史,这幅画的优点在于疏淡静朗,完全去掉了火气,比之于倪瓒又胜一筹。
与国家画院和朝廷中的士人阶层相对,这些在野的职业画家以逸民著称,提出了画中“逸气”说。例如倪瓒说“聊写胸中逸气耳”,王冕也说“吾家洗砚池边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又说“冰花个个圆如玉,羌笛吹它不下来”,与元廷不合作的态度跃然纸上。赵孟虽然老道精熟,堪称元代画坛领袖,然就其气节来说,已输一筹,不得入“元四家”之列。
元代的职业画家具有逸民的特点,而明代的职业画家则是明确地打着旗号,公开收钱,而且是居所稳定,鬻画自食。这一点,与洪武皇帝滥杀大臣、加强专制有关。明代的许多文化人,宁可放弃做官,穷理致性,因此形成了在野派与当朝派的激烈党争,以致出现了大规模杀戮士人的事件,如明朝后期的东林党人被杀的事。不过明朝是尊重读书人的,一个人如果能考取秀才,已是不一般的待遇;如果中了举人,那更是风光无限,县太爷都要尊重他,因为举人也可以选官。一些人选择做职业画家,也会受到尊重,因会这些人都是大才子,都是颇有学问的人,如文徵明,他不仅有学问,而且人品相当好,曾被荐入朝廷,做了翰林。这可不是一般的待遇,虽然他的翰林并没有实权,亦如李太白当年,写写文章,做做画,陪皇上消遣而已。想必文徵明还是有抱负的,但是朝廷内的党争使他无法展现自己的抱负,所以干了一年多,他又跑了回来,做回原来的自己,他的学生陈白阳对此很有看法。
洪武初年,太祖以不称职为由杀了几个画家,这使得画家们战战兢兢。所以选择不入画院可能更好。戴进能全身而退很是幸运;就连吴伟这样的宫廷画家,后来也到社会上去混生活。万历皇帝祖孙都有多年不上朝的经历,致使朝纲废滞,政府懈怠,于是吴伟以狭妓为乐,饮酒作画,以致索画者常备美酒佳妇待之,若要以金钱相邀,定然不理。
苏州、杭州、扬州都是富庶之地,商贾云集,许多画家以鬻画为食,称为利字画,如戴进、蓝瑛、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沈士充、张宏等人,都是收入稳定的职业画家。沈周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沈周一生不治仕业,他的祖父也是如此,但是学问是要做的,这是典型的文人而不是仕人。他一生卖画为业,生活很富有,这与明代发达的商品经济有关。比如徐渭,他的职业是幕僚,但却干着职业画家这一行,由于身份的原因,他卖画所值甚巨。胡宗宪又为他在武林买了宅院,于是他整日以卖画为业,胡宗宪也不过问,后来胡宗宪被害,他吓得扔掉了宅院,跑回家乡,精神失常,曾以铁钉贯耳,后又因杀妻入狱,幸得朋友救助出狱。
朱棣迁都北京,南京仍是以都城的建制存在着,这大约是朱棣迁都亦有二心,固而保留了南京。但此后南京的建制一直存在,朝廷的格局也一直存在。比如海瑞做礼部侍郎就是去南京上班,而不是在北京,南方的经济繁荣也许与此有关。南京居住着大批职业书画家,直到清朝,民间书画交易都很火爆。有趣的是,像吴伟这样被公家饭养着的宫廷画家,却能在青楼酒肆如鱼得水。
唐寅可谓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人生经历自不待说,他作职业画家很显然却不怎么样,那狂傲的性格,既毁了他的前途,也毁了他的职业生涯。他自视才高八斗,却又作玩世不恭状,写诗曰:“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蘖钱。”他的咏《桃花庵》的诗不胫而走。和沈、文不同的是,他的山水画走的南宋路数,而人物亦工亦写,真可谓画中才子。
明朝的画家都叫着价卖自己的画,也带动了江湖画的市场,这种画现在叫“行画”,是一些江湖艺人混饭吃的手艺,传说沈周的画好卖,模仿者甚多。据画史记载,沈周白天画的画,晚上就会有仿品出来。沈周也不在意,有人拿着假画来请他添款,他也不拒绝,因此沈周的影响越来越大。假如说,之前的临仿是为妥善保存原作或出于某种需要,皇帝会指明画家进行模仿;而明清以后,这种模仿已变得很低级,并且出现了专造假画的市场。有人也为这些人取名曰职业画家,这是糟蹋了职业画家的名头。
三
清代的画坛基本上为职业画家所占据着。“清初四王”中的王时敏和王其实也算职业画家,虽然王时敏曾在明朝做过奉常,王也曾被召进宫里画《康熙南巡图》,但总归还是靠职业生涯过活,他们由于和宫廷的联系,所以身价很高。而恽寿平更是标准的职业画家。但这一时期真正的大腕是石涛、朱耷和扬州八怪等人,石涛和朱耷都是明宗室,朱耷一生经历简单,却以耿介著称,以致于被索画者折磨成神精失常。而石涛经历却很复杂,多游历,作画也非常勤奋,晚年定居扬州,标着价卖自己的作品,和“扬州八怪”中的其他画家一样,过着鬻画自食的生活,郑板桥曾中进士在山东做过10年的县令,失官后到扬州卖画,和石涛一样,他也为自己定了润格,靠卖画过得还可以。八怪中还有罗聘和李方膺也做过短暂的官,但都因不同原因,最终选择了职业画家这一行,可见职业画家并非人人都能做。做得好,必先为仕,有学问有影响力。恽寿平虽然名气很高,在画史上和“清初四王”排在一起,创立新安画派,但在影响力上还是要逊石涛、“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一筹。同样还有金陵画派中的龚贤。龚贤端居清凉山,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有田可耕,自号“半千居士”,衣食无愁,因为画卖得好,一生很平顺。
但是,可以看到,当时将画坛风光占尽的还是“清初四王”。因为当时的藏家主要是王公大臣,他们有着相同的审美趣好。比如皇帝喜欢董其昌的字,臣僚也都喜欢董的字,一时董字成了官场的硬通货,大家无不争相购置。石涛曾去京师奔前程,交好了一些王公大臣,但终没有大的发展,最终折回扬州,卖起画来。根据后世记载,石涛的订货也多是些民间的订单。清末,吴昌硕、任伯年都是当画坛大佬的角色,特别是在现今的画史上更是占尽风光;但在当时,他们也仅是上海滩上职业卖画者而已。朋友为吴昌硕捐了一个县令的角色,也许那地方太穷,也可能真的不能适应腐败透顶的官场,他干了一年有余就不干了。他也曾参与抗倭做了幕僚,但也很快就返回,继续做他的职业书画家;也许有了这等经历,自然不同于其他职业画家。吴昌硕的职业生涯过得还可以,在上海买了房,安居下来。
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从清末向民国过渡并进入到新中国的老书画家,大多都做过职业画家;并且和职业画家有着师承关系,如潘天寿就是吴昌硕的学生,而吴昌硕曾跟任伯年学过画,齐白石曾就学于曾髯农。而张大千则就学于李瑞卿,在师承关系上几乎见不到“清初四王”的影响。特别是民国以后“清初四王”受到了批判,只是稍近时间才有了一些中肯的评价。
四
反观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对当前的画坛做出理性的评价,若论美术教育的发达,莫过于当今社会。自1901年前后李瑞卿在南京开办两江师范学堂并成立绘画手工科、聘请日本人担当教授以来,中国的美术教育就掀开了新的一页。但它带来的问题也很明显,美术教育的普及,几乎让人忘记了美术的本身,特别是美院的考试方式及课程设置,生硬地将美术基本功落实在素描、色彩、速写等一类的课程上,甚至有人要取消文化课的考试和学习。对民族传统艺术的研究也很不到位,边缘化、皮毛化的现象很严重。所谓边缘化、皮毛化,是指对传统的艺术精神缺少考量,一知半解。特别是近年来,美协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越来越大,底层书画爱好者的话语权得不到伸张,艺术标准被少数人制订,加之高研班一类的衍生品,艺术创作有被阉割的倾向。虽然国家已开始了市场机制的运作,由于政府的权力过大,致使市场经济被压缩,这使职业人很难做下去,尤其是画坛上的职业人。
如何看待职业画家这一行,是个历史问题。比如元代的钱舜举创“隶家画”说;明董其昌又倡“南北宗”说;都是在强调官僚和文人的艺术观,没有做官,至少也得是个文人,这是基本的要求,同时也要有画技。钱选和董其昌都有画技,两人都做官,并且董的官也做得足够大,这并不等同于加入美协之类的组织。钱画的工稳就不用说了,而董其昌则是踏踏实实在做画的学问,靠学古人而走出古人的窠臼,这样的人历史上也不多见。不做画的学问而能成名者,历史上一个都不会有。
而现在的画坛实在让人看不懂了:讲出身,讲来历,古已有之,而现今仅仅顶一个会员的名头就能行走江湖,被藏家所认可,也只有现今的体制能做到。会员不是官,也不是资历,只是一个标签而已,要打破这种行规,才能真正让学术回到艺术中来,让收藏回到理性上来。
因此,重述职业画家的影响力,可能会使我们重新思考艺术的定位问题。画家不同于演艺家,有点像作家,当然不是韩寒一类的写给未成年人看的作家。沉下去几十年,玩的就是真功夫、真学问。一部经典出来,有足够的影响力,那也不过是一个浪花而已。踏踏实实做下去,不只是为名气、为钱,也是为了民族的艺术繁荣。
我并没有否定体制内的艺术家的意思。绘画毕竟最终还是欣赏为上,不仅仅是展览的艺术,也不是仅供收藏家放在箱底等待升值的法宝。一旦走出欣赏范畴,画的优劣,也就可想而知了。画家要不要资历、文化,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一个不作文化探讨的艺术家,充其量只不过是画工而已;而一个连中学都可能没上好的艺术家,也很难说他的艺术有多高深莫测。过去说,一个中国画家不过50年是很难成功的,所谓人、艺俱老。中国画不同于西画的涂抹,她是要多方面的修养,受视网膜的影响,西画家在眼睛老化之后,就很难正确描绘色彩;而国画家恰恰要到老了才炉火纯青。刚刚获得一个头衔就认为某个人的作品值得收藏,会贻笑大方。这并非我个人的看法,老前辈们多有教导,历代的画评也早有定论,因此聊作评述。不当之处,望方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