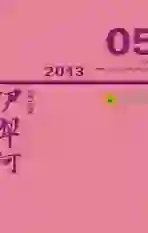乌宗岛与恰巴恰
2013-04-29姜付炬
姜付炬
一.音讹乌孙山
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的一段南山称为“乌孙山”,《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地名图志》第145页这样叙述乌孙山一名的由来:“据传,准噶尔时期,一年发山洪而得名‘乌森,‘乌森是蒙古语水译音。乌宗岛者,盖‘乌森的异译。解放前后,察布查尔县的锡伯文人始著文称乌孙山,其含义为古乌孙国之山,以示察布查尔的历史悠久。”这个后起的地名,以讹传讹,竟然成为论证汉代乌孙国的证据。苏北海先生在《西域历史地理》第一卷中说:“伊犁昭苏盆地以北,察布查尔以南的一条天山支脉至今被称为乌孙山,这些都是古代乌孙族在此活动的有力佐证。”乌孙山在清代及至民国文献中称其为“乌宗岛”,只是解放前后才始称乌孙山,为证“乌孙山”的讹传,有必要简要考证一下“乌孙”原始的音义。
1.乌孙音义考
乌孙山或乌孙国的“乌孙”一词的音义和语源历来有争议。对“乌孙”音义的考察有助于理解乌孙山地名的演变。“乌孙”音义主要有以下几说。
A团结说
有学者认为乌孙可拟音为uysun,突厥语uy为凝固、凝结,引申为团结,后缀sun义为“使”,所以乌孙—uysun义为团结。有意思的是学界有人将uighur—维吾尔同样解为“团结”或“联合”之义,不知为什么没有学者把乌孙作为维吾尔的主要族源。从音韵学角度考察,“乌”字的上古汉语的读音并不是u而是a,乌孙只能拟音asun不能拟音为uysun,所以不可能是突厥语uysun—团结之义。此为一说。
B允姓说
学者余太山认为乌孙为战国时期秦国西北的允姓之戎,在其著作《古族新考》和《塞种史研究》考证甚详。简言之:“乌孙”即为“允姓—Asii”的音转,乌孙部落从战国时代至汉代一直由东向西迁徙(笔者注:Asii即为塞人)。此为二说。
C有熊说
学者朱学渊认为中国北方诸族有着共同的族源,乌孙与有熊(黄帝姓)—虞舜—阿史那(古突厥王族姓)—爱新(清皇族姓)无论语言或种族均同出一源。详见其著作《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朱先生的颠覆性假说令人耳目一新,但是乌孙与爱新觉罗同出一源恐与史实不符。郑天挺先生1943年6月撰就的《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专章“爱新觉罗得姓稽疑”,对满清皇族爱新觉罗得姓史实论述甚详。郑天挺先生文中说:“私臆清代先世以童佟为汉姓,由于同字之转。同姓之来由于夹谷,清太祖重定姓氏,微易其字而为觉罗,复加爱新于其上,以示尊异。”努尔哈赤重定姓氏将本姓夹谷,改为觉罗,并在前面冠以爱新(笔者注:意为金),“以示尊异”。爱新觉罗本姓夹谷(觉罗)非姓爱新,所以爱新与乌孙无关。但是,乌孙与有熊、虞舜、阿史那是否有关尚待新论。此为三说。
D尚黑说
民族史学者何光岳认为焉耆及乌孙曾经在中国山东孝义县漹水一带居住,当地有一种鸟名叫焉鸟,两族共以焉鸟为图腾。焉鸟一身羽毛有红黑之分,焉耆尚红,乌孙尚黑。此为四说。
E马族说
美国学者梅维恒(Victor H. Mair)认为“乌孙”的原音与梵语的“asvin—马”有关,提出“乌孙”可能是“马的民族”(horse people)之义。此为五说。
F跳跃说
日本学者白乌库吉说乌孙可以解为突厥语“跳跃”,源自萨满教跳神仪式。此为六说。
G乌孙说
笔者认为,这个“乌孙”是汉语音义的乌孙。乌孙者,乌之子孙也。乌孙的始祖传说与乌有关。传说乌孙亡国后,襁褓中的猎骄靡有乌鸦衔肉喂养,人以为神。乌为三足金乌,为三足乌,为金乌,为青鸟。三足乌是代表太阳的神鸟,表明乌孙族的太阳崇拜,故自称太阳的子孙:“乌孙”。乌孙赤谷城之赤谷即为阳谷、暘谷,义为太阳谷。羲和为太阳神之母,羲和之子出暘谷,即为赤谷。有人认为乌孙官号“翖候”(读为xihou)为“羲和”的异译。乌孙王称为昆弥或昆靡—kunmi,乌孙王的王号后大多带一个“靡”,这个“靡”或“弥”读作mi,辅音m和b相通所以也可读作bi,义为“王”;昆—kun义为太阳或日,昆弥或昆靡义为太阳王或日王。此为七说。
如果笔者此说成立,和乌孙同在河西立国的“月氏”也应当是汉语音义,以“月”为氏。乌孙是太阳族,而月氏是月亮族。
由是可以认为乌宗岛与乌孙山并没有任何历史联系,“乌孙山”实为以讹传讹。
2.乌宗岛音义考
学界一般都认同《察布查尔县地名图志》对乌孙山的音义解释,认为“乌孙山”由“乌宗岛”讹变而来,“乌宗岛”可译为“水山”。
笔者认为“乌宗岛”解为“水山”尚有商榷的余地。
一.蒙古语“水”读作usu或usun,一般音译作“乌苏”和“乌逊”。乌宗uzun与usun发音相去甚远。如若《察布查尔县地名图志》所言是因为曾经的山洪而得名,那就更不应当是usu而应当是蒙古语delebe或hookiji,意为汪洋的大水或洪水状,后一蒙古语中的hoo可能是汉语“洪”的音变。
二.如果认定乌宗uzun为蒙古语乌森usun,那么岛taw不可能是蒙古语的“山”,只能是突厥语的tag—taw—套—岛。也就是说乌宗岛应当是一个蒙古和突厥语的复合地名,蒙古语乌宗usun为特名,岛taw为通名,意为“水山”,当然亦无不可。但是如果是蒙古人为此山命名为“水山”,为何不直接使用蒙古语“山”的能名,读作usun agula或usun dabaga,反而要舍近求远使用“岛taw”这个突厥语“山”的通名?
三.乌宗岛之“乌宗”作为地名在其它地方并不译作蒙古语“水”。
如吐鲁番的乌宗布拉克;哈密的乌尊吞盖、乌尊塔格乔喀、乌尊巴斯陶,哈密有三处乌宗布拉克,更有意思的是哈密还有三处“乌尊苏”,如果这个“乌尊苏”也和“乌宗岛”一样是蒙古和突厥语的复合地名,“乌尊”是蒙古语的“水”,“苏”为突厥语还是“水”,所以在这里“乌尊—uzun”不可能是蒙古语“usu—水”,只能是突厥语的形容词“长”,可译作“长流水”。新疆南疆以“乌宗”或“乌尊”为地名更是比比皆是,如库车的乌宗乡,《阿克苏地区地名图志》这样解释:“乌尊乡人民政府驻乌尊村。以驻地村名乡。”乌尊“系维吾尔语,意为长。因乌尊村沿渠而建,南北拉的很长而得名。”
乌孙山南坡的昭苏县有一组以“乌宗”或“乌尊”命名的地名,《昭苏县地名图志》全部将其译为哈萨克语的形容词长短的“长”。如昭苏县城东面的乌尊布拉克乡,夏特乡南部的乌尊布拉克。昭苏有三处乌尊萨尔。昭苏县还有一处地名乌尊萨依,如果照上述翻译乌宗或乌尊为蒙古语“水”,萨依为突厥语“山谷”,“乌尊萨依”应当译为“水山谷”,但是《昭苏县地名图志》“乌尊萨依—Uzun say”条下说这条山沟长7.5公里,无水、无林,是一条干沟,如此只能译作长沟,不能译作“水沟”。昭苏阿克牙孜河谷陡坡上有一条牧道名叫“乌尊乔尔玛”,意为长长的小道。由于牧道又陡又长,转场的牲畜只能鱼贯而行。“乌尊乔尔玛”当然不能又是复合词:“水小道”。所以上述的“乌尊”均应与“水”无关。这个乌尊或乌宗,作为水或泉的定语,表示水长流不断;作为山的定语,表示山绵延不断;作为路的定语,表示小路漫长。
察布查尔和昭苏是一山之隔的邻县,但对一些地名的族属和音义分歧很大。除本节主述的“乌宗”(乌尊)外,还有如察布查尔的霍诺海和昭苏的洪纳海出于同一分水岭的南北两条河的名字,实际上是同名的河流。《察布查尔地名图志》将霍诺海记作Honohai,认为是准噶尔蒙古语“霍诺哈”的音译,意为褐色的狗,起因不详。《昭苏地名图志》将洪纳海记作Honohoi,认为是突厥语的音译,意为驿站。哈萨克语里khonalkha,意为住宿、过夜的地方,与Honohoi—洪纳海的音义相近。察布查尔的“霍诺海”曾经也写作“洪纳海”,至今霍诺海沟口的“洪纳海麻札”国家文物部门仍然延用原来的称谓。蒙古语“棕色”或“褐色”当为ulabur,乌鲁木齐的乌拉泊应当读这个音,作这个解。上述霍诺海的“霍”就是解作“褐”,笔者也认为应当是汉语“褐”字西北方言的音转。
乌宗岛之“乌宗”在突厥碑铭的古突厥语中读作Uzun,义为“长”,另外一个近义词Uzaq,义为“远”。在维吾尔语中的Uzun,同样义为“长”;在哈萨克语中的Uzen,有两义,一为长的,二为高的。所以乌宗岛可以解为绵延不断的山或高耸入云的山,突厥在伊犁居留的时间早于蒙古,乌宗岛这个地名也许是西突厥的遗存,这个地名当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3.乌宗岛地望考
“乌宗岛”为史地学界所关注是因为1881年签定的《中俄伊犁条约》。中俄伊犁条约第七条:伊犁西边地方应归俄国管属,以便因入俄籍而弃田地之民在彼安置。中国伊犁地方与俄国地方交界,自别珍岛山,顺霍尔果斯河,至该河入伊犁河汇流处,再过伊犁河,往南至乌宗岛山廓里扎特村东边。 自此处往南,顺同治三年塔城界约所定旧界。
乌宗岛山成为中俄划界的标志,由默默无闻而声名远播。乌宗岛只是察布查尔县南山中的一段。解放前后当地的锡伯族文人循“乌宗岛”之音,称其南山的中段为“乌孙山”。
现在察布查尔县的南山一并被统称“乌孙山”,当代地图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测绘局编制,中国地图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集》中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地图,将其南山标为“乌孙山”。《昭苏县地名图志》将其从国界到特克斯的北山统称“乌孙山”,并且以讹传讹地说:“乌孙系哈萨克语,公元前200多年前哈萨克族的乌孙部落定居于伊犁河流域此山周围故名。”《特克斯县地名图志》亦将其北山统称“乌孙山”,并说为“古地名,沿用至今”。唯有《新疆察布查尔自治县地名图志》所载的地图将该县南山由西向东分别称为帖木里克山、乌孙山和察布查尔山。明确标示乌孙山从国界以东的霍诺海沟口至切吉山隘。切吉山隘以东标示为察布查尔山。霍诺海沟口以南标示为帖木里克山。
帖木里克山在《平定准噶尔方略》和《清史稿》中记为推墨尔里克岭,乾隆二十年春清年北路军从固尔札渡口渡伊犁河,向南翻越推墨尔里克岭发动平定准噶尔部的格登山之役。推墨尔里克岭亦写作特穆尔里克山。特穆尔里克山由多座山组成,由国界依次向东排列:沙拉套山(黄山)、喀拉套山(黑山)等。
据《新疆图志·山脉五》载自西向东有:
沙拉套山,《新疆图说》:在绥定城南二百四十里,谨案此山为中俄分界,第九号牌博。
喀拉套山,洪海水出焉,北流七十里分溉庄田。《新疆图说》:此山在绥定城南一百八十里。
乌宗岛,有水出焉,北流分溉庄田。《新疆图说》:在绥定城南一百八十里,冲布庄水、大博罗庄水、小博罗庄水、霍落海庄水均出其麓。
色格三岭,有水焉,北流溉田入于地。
华诺辉岭,水出焉,入于特克斯河……谨案此岭《新疆图说》作霍洛海,今皆谓之铜山。
索果尔岭,索果尔水出焉。其阴产铁……谨案此岭即莎岭。(笔者:莎音suō)《新疆图说》作索达坂,索果尔水源出于此,北流二十里至索果尔军台,折而西北流六十里至坎庄。
察布查尔山,有水焉,北流溉民田……谨案此山《新疆图说》作恰布恰伦在伊犁河南。
雅玛图岭,有水焉,北流遇沙而伏。《西域水道记》:哈什河西南流,经雅玛图岭北。
《新疆图志·山脉五》没有专门记述特穆尔里克山,是因为将以上诸全部归于其名下。沙拉套突厥语意为黄山;喀拉套突厥语意为黑山;色格三突厥语意为八十,色格三岭为八十座山;华诺辉岭即为洪纳海山,突厥语意为驿站;索果尔岭的“索果尔”为蒙古语腋窝,详论见下段;察布查尔山音义见下一章;雅玛图岭音义见拙作《那拉提与雅玛图》。所以在《新疆图志·山脉五》中乌宗岛只是特穆尔里克山中的一座前山。在清末民初的地图上,乌宗岛是绥定县与宁远县的南部界山。
索果尔岭,莎岭。《西域同文志》莎达巴:“准语莎,臂胯也,岭形如之故名。”索果尔,即索郭勒—莎郭勒,莎河。《西域同文志》所谓“臂胯”不知何指,臂在上半身,胯在下半身,不可能是“腰胯”之误,腰胯的蒙古语为sheguji,与“莎”音相去甚远。应当是腋窝或胳肢窝之误,腋窝的蒙古语为suo,正与“莎”的发音同。从莎岭流出的河称作索果尔—索郭勒—莎郭勒。现在蒙古语的莎岭—莎达巴—索果尔演变成为哈萨克语的苏阿苏suwasew,suw为水,asew为山口、山隘,苏阿苏—水山口成为索果尔或索郭勒现在的地名。莎郭勒的东面是察布查尔沟,西面是乌尔坦沟,均为蒙古语的地名。乌尔坦ortege蒙古语意为台站、驿站。
赖洪波先生在其论文《伊犁地名历史沿革考》中,论述过“乌宗岛”向“乌孙山”的讹变过程后,委婉地提出他对“乌孙山”地名乱象的忧虑,他说:“综上,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应注意此一历史地名规范,废除乌孙山这一讹传地名,以免自乱藩蓠也。”
从历史角度看,“乌宗岛”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沉痛教训。1871年沙俄乘伊犁之乱军事占领伊犁,十年后中国索还伊犁,在条约签订和划界过程中,沙俄就是以地名的模糊概念对中国领土巧取豪夺,在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进一步圈占中国领土。如上所述的伊犁河谷段,故意以两座东西走向的山脉划界,北起别珍岛,南至乌宗岛,以期浑水摸鱼。当时清廷谈判的大员崇厚手中没有自己的精确地图,当然更没有精确的地理概念,竟然私自签约将特克斯流域全部割让给了俄国,全国舆情哗然愤然。清廷再派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重开谈判重订条约,曾纪泽当时用的还是俄国绘制的地图。曾纪泽比崇厚聪明许多,要重订的伊犁条约中在乌宗岛后面加上“廓里扎特村东边”的定位限制。这个定位限制也没有阻止沙俄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在《中俄伊犁界约》中违约将第十八界牌东移至噶尔札特村(笔者:即廓里扎特村)以东7公里,距现在我国的麻札村仅1公里。
再则,乌宗岛是一个中性的地名,而讹传的“乌孙山”则是一个承载历史和政治的地名,随意命名,有可能“自乱藩蓠”,带来难预见的后果。
从现实的角度说,对“乌宗山”或“乌孙山”的四至,至今国家没有统一规划和管控,地方和部门各自为政,自话自说,各吹各调,乱象叠出。察布查尔一套,昭苏和特克斯各自一套,伊犁自治州和新疆自治区又是各自一套。各县的“地名办”所定的地名读音、意义、语源以及地望四至不统一,给行政管理、经济开发和史志撰写带来负面影响。所以对“乌孙山”这样影响深远的地名要重新考量,纠正以讹传讹的现状。县以上的地名管理机构要对各县地名的管理、审核和统一起到职能作用。
4.山银哈达的锡伯诗意
乌宗岛意为“长山”,长山的主峰名为“山银哈达”,海拔3480米。山银shanyan,满语、锡伯语:白色。哈达hada,满语、锡伯语、蒙古语:山峰。Shanyan hada白峰,白石峰。
我国东北的长白山是满族等通古斯人的圣山,伊犁的“山银哈达—白石峰”则是锡伯、蒙古、哈萨克等民族的圣山。长白山的主峰名为白云峰,乌宗岛的主峰名为白石峰。
白石峰—山银哈达三峰相连写出一个“山”字,白石裸峰,在碧空白云下熠熠生辉。春天百花漫山,映衬着白云白雪白石,美轮美奂,天外仙境。
“山银哈达”不仅仅读起来朗朗上口,韵律回旋,令人联想翩翩,而且文字内涵深厚悠远,具有浓浓的锡伯诗意。山崇拜、石崇拜是中华各民族的原始文化源头,对大山的敬畏崇拜已经融入民族血脉,成为民族文化的基色。
所以,用“山银哈达”代替“乌孙山”也可能是一个诗意的选择。
二.义歧恰巴恰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所在地名,明代称海努克,清代称锡伯营,民国时期建县称河南县,后改称宁西县,三区时期改称苏木尔县,解放后改回宁西县,1954年建立锡伯自治县始称察布查尔。官方将“察布查尔”解释为锡伯语“粮仓”。
县名“察布查尔”源于锡伯族开凿的察布查尔大渠,而察布查尔渠的源头在察布查尔山。察布查尔山由蒙古语恰巴恰音变而来,这是公认的察布查尔地名的演变链。由于官方的武断解读,造成对“察布查尔”一词的翻译,地名来源和语言族属的分歧。因此有必要对其语源、音义和演变过程再一次劙清考证。
1.恰巴恰音义考
卡巴卡或恰巴恰在蒙古语和突厥语里都是一个常见的地名。
蒙古语Цавцил(chabchil)有两个意思,一是陡峭,二是林间小路。而Цавцаал(chabchal)为陡峭、险峻、关隘之意。
《俄国 蒙古 中国》一书中所载的雷纳特一号地图,编号100的Цабцаль译作察布查尔,注为外伊犁阿拉套山的察布查尔隘口Chapchal。这个译音与蒙古语词典所载几近相同。相传雷纳特一号地图是准噶尔汗王噶尔丹策凌亲手绘制,送给雷纳特带回欧洲。这个地名存世至少有500年以上的历史。
直至清末民初,恰巴恰或察布查尔依然只是一座山、一条河、一个隘口和一个村庄的名字。瑞典人马达汉1907年5月曾经过察布查尔山口,他在日记里是这样记述的:“5月7日 ……从坎尼村(笔者:今察布查尔县坎乡)出来,道路朝东沿着一座突出的山嘴根部进入察布查尔村。道路在这里向南拐了一个急转弯,我们骑马穿过这些高低不平的山嘴,一条相当宽阔的山沟在这里把道路与主干道分隔开,这种情况跟索达坂—坎尼路上的情况一样。一条很小的河道,察布查尔苏河,蜿蜒曲折地沿着山谷流淌。在河的左岸,与河同名的村子南端,一些孤单单的房屋,隐没在绿草茵茵的山丘后面。景色如画,草木青翠欲滴,在远方生长云杉的群山雪岭衬映下,显得格外迷人。从这里往南,道路带我们沿着一个狭窄的山谷,走向主体山脉……在山口以南1-2俄里的地方,我们停下来宿夜。为了躲避已经开始下起来的雨,瞬息之间支起了帐篷,以保护行李等物品。
“5月8日……下了一夜雨,今天当我们应该走的时候,雨还在下。由于我的卡拉喀什人向导坚持认为,不能在这样泥泞的道路上过山口,我决定等天气好一点再走……直到12点半,一切都准备就绪,于是就出发。离开营地后,马上就爬坡,沿着坡路直达察布查尔山口。上坡路不太陡,但石子很多,雨后许多地方非常滑溜。下午3点半我们经过了许多道相互连接的山冈之后,来到了最后一座山冈……山口顶上,有两座石堆和布条之类的东西(蒙古人祭祀的敖包—译注),表明离卡尔梅克人(笔者:蒙古人)祈祷的地方不远了。山口的南坡比较平缓,不像北坡那样累人。这里的路在现在这种状态下都可以通马车。我们骑马下坡走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道路进入了苏尔尕苏峡谷(笔者:今苏阿苏),然后与索达坂的路合在一起。雨后苏尔尕苏河涨水了,今天约有2庹宽,水量充沛,但不深。道路在离开苏尔尕苏的地方,就开始往连续不断的三个山口爬行。其中最高的山口叫吉里达坂,今天这段路非常滑,我们的驮马上下山口十分困难……”
从马达汉日记的记述可知一百年前察布查尔山一带蒙古人的遗迹还有很多,坎村和察布查尔村一带的居民多为塔兰其人(笔者注:指伊犁维吾尔人)。
2.《拉失德史》中所记的“卡巴卡”地望考
伊犁“恰巴恰”这一地名历史久远,但在历史典籍中很少出现。《拉失德史》中所记的“卡巴卡”是仅见的伊犁河畔“恰巴恰”。
600年前,东察合台汗国的歪思汗Awais khan在伊犁立国,称之为“亦里巴里”(笔者注:伊犁城)。歪思汗以圣战之名,与敌手交战61次,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后在伊塞克湖畔,与兔沙克汗争夺汗位,中箭战死。
《中亚蒙兀儿史-拉施德史》一编247页记载其中的一次战役:“另一次,歪思汗又在蒙兀斯坦边境的卡巴卡地方,同也先大石(笔者注:瓦剌首领。瓦剌即今天的西蒙古)作战,也被战败。他的坐骑中了一箭,因而不得不徒步往前走。当他快要被俘的时候,异密·赛义德·阿里跃下马来让汗骑上,自己却伏在地上。异教徒以为他死了,于是就在他头上射了一箭。当他们走到跟前时,这位异密一下子抓住一个(碰巧是一个比较有地位的人),连衣襟提起来把他当盾牌,四面挡箭,一直跑在汗的缰绳旁边。就这样,一支箭也射不到他身上。他如此且战且走,连衣襟抓住这个人,足足走了一程,来到亦刺河边(笔者:即伊犁河)。他便把这个喀尔木人(笔者注:卡尔梅克人,亦即西蒙古人)扔到水里,带住汗的缰绳跳入水齐胸深的河中。有几个人被淹死了。而异密则托起马头,就这样引导着骑马披挂的汗过了河。”
《拉失德史》英文译者罗斯对“卡巴卡”的注这样说:“这次战役发生在什么地方,著者并未提出任何线索。蒙兀儿斯坦的‘东境和‘北境都有喀尔木人,但在这两面我却没找到卡巴卡,这个地方很可能在亦剌河上游,现代这条河叫作伊犁河。”
罗斯不知道“卡巴卡”在什么地方,但他推测应当在伊犁河的上游。罗斯的推测非常正确。原来笔者将“伊犁河的上游”理解为伊犁河支流,例如巩乃斯河的支流恰巴河。实际上伊犁河的上游在喀什河、巩乃斯河和特克斯河汇流段,所以这个“卡巴卡”应当是察布查尔县和巩留县交界的察布查尔河谷。此河谷自古以来一直是南下翻越察布查尔达坂,进入特克斯河谷,再翻越木札特冰达坂通往南疆;北渡伊犁河,进而北上翻越登努勒台到达天山北麓。为兵家必争之地,歪思汗和也先大石在此争战势所必然。
赛义德·阿里将战败的歪思汗救下,牵引着他的坐骑渡过伊犁河。由此溯喀什河北上,在喀什河支流博尔博松河畔就是歪思汗的归宿地,他的陵墓所在。东察合台汗国的歪思汗战死于1428年,距今近600年,所以”卡巴卡“这个蒙古地名的出现时间不会少于这个成数。
3.“恰巴恰”向“察布查尔”的演变
有意思的是,峭壁的“恰巴恰”向粮仓的“察布查尔”的演变,和“乌宗岛”向“乌孙山”演变一样,是地名的讹变。
由峭壁的“恰巴恰”向粮仓的“察布查尔”的演变引出一件公案。对“察布查尔”这一地名的语言族属和地名起源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对立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察布查尔”来源于蒙古语“恰巴恰”,意为“峭壁”,地名起源于恰巴恰山(即现在的察布查尔县与特克斯县交界的察布查尔山)。另一种观点认为“察布查尔”与蒙古语无关,为锡伯语“粮仓”之意。
第一种观点以管兴才和舒慕同先生为代表。
纪大椿的《新疆察布查尔调查散记》记叙1958年他到察布查尔县社会历史调查的经历,其中有一段关于“察布查尔”地名来历的叙述:“我们向管老(笔者按:管兴才)请教了‘察布查尔一名的来历。他认为这并非锡伯语,也不是人们所说的‘粮仓之意。这使我们很惊讶,因为书上报纸上都是这么说的。他告诉我们,这是蒙古语,察布查尔渠在嘉庆年间开挖时就叫锡伯渠,龙口在察布查尔山,后来才叫察布查尔渠。此后我倒留心这个问题,不少锡伯族知识分子赞同他的看法。我也请教过几位蒙古族同志,他们说察布查尔是峭壁的意思,以此作地名的地方不少。地名学是一门很不简单的学问。”
舒慕同·乌扎拉《新疆地名趣谈》一文中说:“目前许多报刊、杂志甚至正式文件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察布查尔一词在锡伯语中具有粮仓的含义。听过之后,确有令人啼笑皆非之感,因为这个名词在锡语中根本不存在这一概念。”(载《新疆日报》1987年10月10日)。
第二种观点以英林和舒慕尔先生为代表。
英林编纂的《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地名图志》的开篇“察看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概况”说:“‘察布查尔一名,原为清嘉庆年间锡伯人凿通之一大渠名,为纪念此渠哺育之恩,故名,锡伯语有粮仓之意。”该图志山脉章察布查尔山条下:“准噶尔时期,称‘恰布恰,蒙古语意为悬崖谷地。至清,因开铜矿,得名铜山。后受察布查尔大渠之名影响,逐渐演变为察布查尔山,锡伯语意为粮仓山。”
英林专门撰写《“察布查尔”一词考辨》一文论证“察布查尔”的锡伯语“粮仓”之意。
文中说:“察布查尔一词在蒙古语中不含有任何意义,”蒙古语的恰巴恰山和恰巴恰河演变为察布查尔山和察布查查尔河是受到锡伯语“察布查尔布哈”的影响。
英林解释“察布查尔”为锡伯语“粮仓”之意的论证很有意思。他说:“察布查尔”一词,是口语化的锡伯语,是由“察布”和“查鲁”二词简化粘合而成的。其中的“察布”,是锡伯语化的梵语借词,即为喇嘛教通用经语,蒙古语称“萨普”(sap)。“察布”(chabu)一词,在锡伯语中含有两种意思:一是指供品,即在供桌上摆的食品或敬献喇嘛的食物,从前锡伯人请喇嘛用餐叫“chabu gaiki”,二是指肴馔,即丰盛的饭菜或盛宴。“查尔”一词是锡伯语“查鲁”的口语,兼含仓或粮仓之意。
在英林之前苏慕尔·德善撰写过《“察布查尔”考辨》,虽然坚持“粮仓”说,但是解释了“察布查尔”由“恰巴恰”演变而来的过程。苏慕尔·德善在文中最后总结说:“我们就‘察布查尔这个名称来说,因‘察布查尔这个山名,命名大渠为‘察布查尔布哈(大渠),同时‘察布查尔一词是从原蒙语的‘恰布齐一词演变来的,之所以成为锡伯语的‘粮仓之意,这是因为‘察布查尔的‘察布正与喇嘛教经语供品—‘察布相同;‘查尔正好与锡伯口语‘查尔—仓,粮仓相同,因此就将‘察布查尔汉译为‘粮仓了。”
“为什么在锡伯族中至今也还存在对‘察布查尔一词不解其意的情况呢?是因懂‘察布查尔一词前半部‘察布一语的人目前为数不多,一般只有当过喇嘛的人和70岁以上的人才懂得。目前新疆锡伯族中,当喇嘛的人数,已寥寥无几,加之,有些写文章的人调查研究不够,就产生了对‘察布查尔一词在理解、解释、翻译上的混乱情况。”
英林和苏慕尔·德善先生这样解释锡伯语“察布查尔”的音义:“‘察布查尔一词,有两个音节,含有两个意思,‘察布为喇嘛教经语,意为‘供品(指庙内供桌上的食物或献给喇嘛的食物)。供品即食物,食物引申为粮;‘查尔为锡伯口语(书面语为查鲁)兼含仓、粮仓之两种意义。就是说察布查尔一词的后一语,‘查尔也含有‘粮仓之意。”
英林先生说锡伯语“察布查尔”地名与蒙古语无关,恐与史实不符。察布查尔地名源自恰巴恰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是意为“粮仓”的“察布查尔”亦可用蒙古语解释。
“察布”可解为蒙古语цав,这个词有两个意思,一是裂缝,二是蒙古语旧词汇的“斋”,即为喇嘛准备的斋饭,或赠献给喇嘛的布施,亦或是用饭之意。“查尔”可以读作蒙古语的sang,意思为“仓”。正好合乎英林和苏慕尔·德善先生对察布查尔为“粮仓”之意的解释,只是用的是蒙古语。
如果说“察布”为喇嘛教经语,意为“供品”,是指“庙内供桌上的食物”。古代敬神的供品主要分五大类:1.酒茶类。2.香烛类。3.果盘类。4.五谷杂粮肉食类。5.动物类。食物只是供品的一个部分,所以“供品”引申为“食物”,再引申为“粮”,在逻辑上很难讲得通。“查尔”可以解为“仓”或“粮仓”之意。calu为满语“仓”,sang为蒙古语“仓”,全部为借用汉语“cang—仓”的音义,苏慕尔·德善先生说的锡伯语口语“查尔—car”为“仓”同样是借用汉语“仓”。如果以“查尔”为“仓”,那么很难在前面冠以“察布—供品”,“察布查尔”就成了“供品仓库”了。
既然如英林先生所言“‘查尔也含有‘粮仓之意”,那么察布查尔县直接命名为“查尔”县,何苦要在前面加上“察布”这个久已过时,且大多数锡伯族人不懂的喇嘛教词语呢?
笔者认为,如果说“察布”是指蒙古语цав,即“献给喇嘛的食物”,即为“布施”。“布施”满语为shelembi,蒙古语为uklig ukgumui,发音都与“察布”相去甚远。在语义上与“布施”有关,且在语音上与цав—chabu—察布有关的只有汉语“茶布”。
“茶布”亦可读为“茶布施”,在藏传佛教或喇嘛教中全称“熬茶布施”,意为向喇嘛庙和喇嘛布施钱财。清魏源《圣武记》卷五:“东西数万里,熬茶膜拜,视若天神。”清俞正燮《癸巳类稿·驻札大臣原始》:“阿睦尔撒纳又寄信藏中熬茶,言已总四部时,善待达赖喇嘛,振兴黄教。”以“熬茶”代称“熬茶布施”。自明代、清代以至民国为维系笼络西藏宗教上层,均实施过“熬茶布施”政策。“熬茶布施”也就成了喇嘛教的宗教用语。
“布施”译自佛教梵语Dana,音译为檀那。Danapat意为施主,音译为檀越。佛教用语“茶布施”取义为“布施如茶、清净无私”,其中寓意是一片茶叶的布施虽然微薄,但是以清净无私的心去布施,不求名誉,不求功德、不求福报,只是尽心尽意地奉献自己的芳香。由此可知,无论“茶布施”、“茶布”还是“察布”,和“查尔—仓”一样都是汉语或者汉语的译音。
4.察布查尔的锡伯丰碑
前述《新疆图志·卷六十三·山脉五》察布查尔山条下专门记载了锡伯族先贤图默特带领锡伯民众开挖察布查尔大渠的故事:“图默特创议于察布查尔山口引水,自崖上凿渠,东西长二百余里,数年功成,闢田千顷,遂大丰殖,雄视诸部,郑白之沃不足云矣!”
《新疆图志》的作者将察布查尔大渠比作秦代中原的“郑国渠”和汉代的“白渠”。“郑白之沃”典出东汉班固《西都赋》:“下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新疆图志》的作者认为和察布查尔大渠相比,“郑白之沃”无足道也。
察布查尔就是恰巴恰,根本无须硬行解释为“粮仓”。察布查尔大渠本身就是一座和察布查尔山一样的锡伯族丰碑,镌刻着锡伯族二百多年屯垦戍边将荒原改造成“粮仓”的不世功绩。
参考文献
1.赖洪波.伊犁史地文集.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9月一版
2.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中亚蒙兀儿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一版
3.弗·约·巴德利(英).俄国 蒙古 中国.商务印书馆,1981年一版
4.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地名图志.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地名委员会编,1987年12月第1版
5.昭苏县地名图志.昭苏县地名委员会编,1995年12月第1版
6.特克斯县地名图志.特克斯县地名委员会编,1986年7月
7.旧刊新疆舆图.清光绪三十二年版.台湾成文出版社民国五十七年三月影印
8.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1月版
9.冯瑞(热依曼).哈萨克族民族过程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5月一版
10.哈萨克族简史.《哈萨克族简史》编写组.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一版
11.英林.“察布查尔”一词考辩.《锡伯族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一版
12.苏慕尔·德善.“察布查尔”考辩.《锡伯族文化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一版
13.纪大椿.新疆察布查尔调查散记.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网,2010年9月8日
14.朱学渊.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中华书局,2002年5月一版
15.余太山.古族新考.中华书局,2000年6月一版
16.吕一燃(主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论集(1990).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8月一版
17.新疆图志.袁大化修,王树楠纂.东方学会重校增补.天津博学印刷局,1923年印行
18.王树楠.新疆山脉图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3月版
19.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一版
20.阿克苏地区地名图志.阿克苏地区民政局,200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