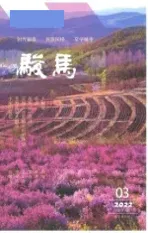去听风声
2013-04-29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蒙古族)
那是更北的北方。
那里有尚还保留着最后荒野气息的北方森林。
北方的森林,对于我有不同的意义。
我的鄂温克朋友,就常年生活在这片无边的林地之中。
每年,我都会上山去看望他们。我喜欢五月和九月。
五月是春季,冰雪消融,小驯鹿也在这个季节降生。
那些刚刚降生不久的小鹿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到母鹿的腹下寻找乳头。它们生着像天鹅绒一样细软的皮毛,而它们的蹄子,竟然像煮得过久的栗子一样,是柔软的。
小鹿的出生,总是带给营地前所未有的希望。
五月,也是候鸟迁徙的季节,我曾经有幸目睹成千上万的雁阵如乌云般从山林上空呼啸而过的恢宏场面。很快,夜鹰也会到来,在每个晴朗的夜晚像不倦的铁匠一样发出敲打铁砧般急切的鸣叫声。一起到来的还有众多的候鸟,森林就此开始热闹起来了。
而九月,是秋天,也是一年中山地最美的季节。
一座山上的林木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呈现出不同的丰富色彩,金黄、火红、红棕、明黄……有些颜色,是我的语言所无法描述的。
在林地间行走时,我常常无意中闯进一片林间空地,在耀眼的阳光下那些上下翻飞的红色蜻蜓仿佛遗落人间的璀璨宝石;而正在河湾中进食水草的犴听到我靠近的脚步声,像挨了大炮一样发出巨大的溅水声跳上岸,轰然作响地撞开身前的灌木丛,一头林中巨兽眨眼之间就消失在丛林之中;一头羞涩的狍子在白桦林中只是稍稍地展露了一下俊俏的头颈,就悄然隐没不见了;三头肥硕的熊若无其事端坐在青翠的平缓山坡上,王者般俯视着整片谷地;随着如同地雷爆炸般的一声巨响,脚边平地升起一个巨硕的斑斓毛团,那是一只受惊的松鸡……
九月的森林,是一个繁忙的世界。
其它的季节,我很少上山。
除了令人谈虎色变的草爬子(蜱虫),夏天山上有太多穷凶极恶的蚊虫,即使是生着厚厚毛皮的驯鹿,也要在人们用湿木头烧起的烟雾中,终日苦苦撑捱。
而营地的冬天则过于寒冷了。
真的太冷了,十月上山时,我已经不得不在结冰的河中洗澡。在隆冬季节,山上最冷的时候甚至达到-50℃。
其实,从现实意义上讲,山上几乎没有什么美妙的季节。春天驯鹿产崽,刚刚结束冬眠不久的熊在饥饿的驱使下常常会袭击母鹿和小鹿,营地的人们不得不时时提防;而秋天也正是山火肆虐的危险时段。
对于山上的鄂温克朋友,他们长久地生活于丛林之中,感受这种四季的轮回,他们的时间只存在于太阳升起又落下、小鹿降生又长大这些具体的事情上。所有的季节,无论山外人视为仙域的风景还是炼狱般的酷寒,对于他们来说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承载这种生活方式的,正是一个民族在北方广袤的林地中黯然消逝的背影吧。
寻求现实发展和固有文化保留与传承的和平共处,这几乎是世界上所有少数民族在这个时代必须面对的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的规划,地方的协调,不断地尝试,也许还要耗时多年。但正如美国自然生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所说:“每一个国家都应该维持部分的自然资产不受破坏,这点非常重要,这样未来才有参考的记录,衡量环境改变才有一个基准,大家也才能看到土地遭破坏前人类所拥有的光辉过去。有朝一天要重建栖地时,我们也需要知道过去的模样。”
这也正提醒我们保留古老驯鹿文化的重要性与迫切性,驯鹿鄂温克部族数代以来带着自己的鹿群在森林中迁徙,与万物和谐共生,我们必须尝试让这种文化在森林中代代传承。不仅可以作为我们在未来到来时参考的记录,也可以作为衡量环境改变的一个基准,将来的人们可以通过它看到森林退化之前那广袤无边的辉煌过去。有一天,当我们试图重建北方森林的辉煌时,至少森林中的驯鹿文化,还能让我们有一个比对的标本。
但眼前的现实是,在北方的驯鹿营地中,有些东西已经永远地消失了。想起这次在山上与维加聊天时谈到的一件事。他和我有同样的感叹,曾经的猎熊部族正成为被传说的丛林传奇,现在,即使真的可能猎到熊,也没有人学乌鸦叫了。在失去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失去曾经伟大的传统。在北方的森林中,有些东西就永远地消失了。
我希望永远保留自己在北方森林中的营地,那里是我的家。
我希望在北方无边的丛林中,驯鹿鄂温克部族敲打缀有巨犴蹄甲兽皮盐袋召唤驯鹿的声音永远不会消逝;我希望背着背包穿越丛林之后,擦汗时透过白桦林看到帐篷上升起的炊烟,被驯鹿群簇拥着的营地;希望看到迎我进帐篷的芭拉杰依、维加和柳霞,希望看到我送给营地的礼物,那头已经剽悍如熊的蒙古草地牧羊犬齐姆且(鄂温克语:六趾之意)。
我每年都会上山,过一段驯鹿营地的生活。
最近的这个冬天,我就在那里。
白天,我拎着斧子放枯树、锯柈子,用斧头敲开冰河取水;夜晚要经常从温暖的睡袋中爬出来,给炉子添柈子,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在凌晨时不被冻醒;噢,还要上山寻找走远的驯鹿,尽管今年雪小,但也不得不经常在没膝甚至齐腰的积雪中跋涉五六个小时,以至于我现在看到雪就恶心,还有点轻微的雪盲。
这次上山的第三天,为了抄近路赶回营地,我迷路了。
确实有些大意了,我早晨出去时既没有带食物和水,也没有带火种。
我独自在山谷中根据自己的直觉向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走,并不时地用手表上的罗盘校正方位,但随着太阳慢慢沉下山脊,天色发暗,温度陡然降低,我开始紧张了。在雪地里冻死或冻伤也许有点夸张,但要让营地上的朋友出来找我,我的面子上也有些过不去。
终于,天快黑时,我意外地发现了狗的爪印,很好辨认,是狗而不是狼。
我知道这是营地的狗。
循着狗的爪印,我找到了营地。噢!森林中温暖的家。
尽管又渴又饿,回到帐篷里,我做的第一件事,还是拿起一块肉,切开了,分给营地上的狗。能够平安地回到营地,我得感谢它们。
不过,每次上山总能看到或者听说一些人,以文明人的姿态进入,但猥琐地在未经主人允许的情况下拿走营地上的东西——桦皮盒、盐袋子、猎刀,连插针用的兽骨制成的线棒都不放过,当然也许这些东西在他们回到文明世界之后都能够成为到北方森林一游的炫耀资本。
对于这样的人,芭拉杰依总是淡然地称他们是要饭的。
想起前几年一件事。当时我去根河的敖鲁古雅乡看望正在山下的芭拉杰依,遇到了自称是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一帮人,好像刚刚拍完一部电影,将作为道具租用的一头驯鹿送回敖乡。但是,他们在使用了驯鹿之后,并未按原来的口头承诺兑现租金,芭拉杰依尽管生气,却也没有办法,毕竟当时没有订立合同。为了获得良好的银幕效果,这头驯鹿没有锯茸,保留着一副漂亮的鹿角,所以说,每次将驯鹿租出之后,不但得不到租金,还要损失出售鹿茸的钱。而且,驯鹿因为在外面饮食不习惯或者过度使役,往往回来不久就会生病甚至死亡。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止发生了一次。芭拉杰依并不愿意出租驯鹿,但这些电影厂的人每次都是经芭拉杰依的朋友介绍来的。
那头刚刚充当了道具的驯鹿因为不能适应那段颠沛流离的生活,饮食也不太习惯,积食胀气,回到敖乡之后就开始绝食绝水。它不喝自来水,我和芭拉杰依只好牵着它上山找山泉。看到石下涌出的泉水,已经两天滴水不进的驯鹿竟然立刻低头痛饮。这丛林中的生灵,只喝山上的泉水。回敖乡怎么办,总不能天天爬山领它来喝山泉水吧。后来芭拉杰依想出一个好办法,我找了四个空矿泉水瓶子,装满了山上的泉水,带到山下,每次饮它时,都在自来水中掺进一些。
还好,那头驯鹿最终安然无恙。
也许我做不了更多的事,不过,至少我将这件事,写进了我的小说《驯鹿牛仔裤》中。
我真正要学习的,恐怕应该是鄂温克人那种面对一切的坦然,就让一切随风而去吧。
就在不久之前,一位鄂温克族朋友额日泰先生提到一件往事。他去蒙古国旅游,一天,一位当地的朋友对他说:“朋友,领你去听听风的声音。”就这样,他们开车一路前行,到了山边,坐在巨石之上,喝奶茶,吃羊肉,听风吹过松林的声响,听在林中潜行的野鹿的低鸣。就那样。整整一天。
说的多好啊,去听风声。
我在呼伦贝尔的营地很快建成,我的一群猛犬终有安置之地。
另外,最近也托新巴尔虎右旗的朋友帮助寻找一些品种不错的蒙古牧羊犬种犬,以我的营地为基地,繁殖一些蒙古牧羊犬的幼犬,将它们无偿送给草原上的牧民和山林里的鄂温克朋友。这也是我多年在呼伦贝尔搜集素材写作并出版多部作品之后,终于能够对这片土地所做的实质性的回报吧。
现在终于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生活在呼伦贝尔,而且,能够经常去看望芭拉杰依,也能够经常进入丛林深处的驯鹿营地,去听听风吹过的声音。
责任编辑 王冬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