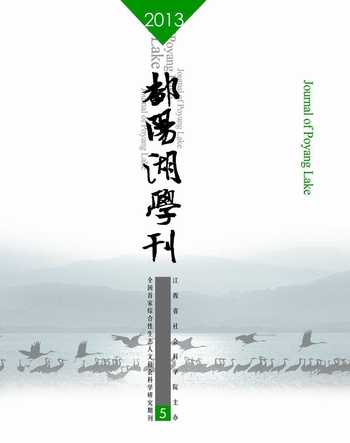论贵州苗族诗意栖居的生态文化内涵
2013-04-29蔡熙
蔡熙
[摘 要]几千年来生活在贵州山区的苗族人民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文化。万物有灵的自然观、绿色的生态法制、绿色的生态禁忌和绿色的生态习俗等构成了苗族诗意栖居的生态文化。这种生态文化既反映了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和膜拜,也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智慧和生态伦理。故而,苗族基于独特的山地环境而形成的诗意栖居的生态文化,对于新时期构建绿色的生态文明理念和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关键词]贵州苗族;诗意栖居;生态文化
[中图分类号]Q9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5-0111-08
[作者简介]蔡 熙(1968—),男,湖南永州人,文学博士,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贵州文化研究。(贵州贵阳 550002)
[基金项目]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亚鲁王》的文学人类学研究”(13XZW024)的阶段性成果。
英国文化学者艾哈迈德指出:“今天,全球危机的范围几乎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和心理等人类活动的全部领域。”①他在《文明的危机》一书中重点探讨了气候变化、资源短缺、粮食问题、经济危机、国际恐怖主义和军事化倾向六种危机,其中生态和资源危机被他视为最主要的危机。当前,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已出现“生态赤字”。我国所面临的生态形势更是十分严峻,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而且每年仍然以1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递增;全国酸雨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2.6%;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27%;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全国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①由于人口膨胀、盲目开垦、过度砍伐森林,自然灾害频繁出现,人与自然之间原本和谐共融的关系变得日渐疏离甚至截然对立。
几千年来生活在贵州山区的苗族人民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文化,这些独具特色的地方生态知识具有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意义。整理和挖掘其生态文化内涵,让苗族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文化参与构建当代中国的生态理念,对于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参照意义。
一、诗意栖居的生态环境
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曾言:“诗意地栖居意味着置身于诸神的当前之中,受到物之本质切近的震颤……存在之创建维系于诸神的暗示。而同时,诗意的词语只是对‘族之音的解释。”②用“诗意地栖居”来描述苗族的人居环境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苗族是众所周知的森林化的生态民族:吃森林绿色食品、森林蔬菜、森林食油(茶油),喝森林饮料(茶和树汁),穿森林衣服(麻织品、蜡和树脂染品),住森林建筑(全木结构的干栏式住宅),甚至娱乐也森林化(爱鸟、斗鸟、斗牛),医学也以草木本中药为主,连苗族的鼓社也无一不是森林化的产物。因此,到过贵州的旅游者都称苗族为“生态民族”。③
苗族大多聚族而居,一个寨子少则几户,多则几百户甚至上千户不等,单家独户居住的很少。苗族人依山就势,把房屋建在山腰或山顶,田地则在山麓,因此,一个完整的村落空间往往包括住房、田地、水井、风景林、土地庙等,它们共同构成诗意栖居的生态环境。
(一)绿色建筑:吊脚楼民居
迁徙到贵州的山区苗民,为了适应南方温湿的气候,防止洪水和猛兽的袭击,就地取材创造了一种防湿防潮的干栏式吊脚楼建筑。苗族是干栏式建筑的发明者。苗族的吊脚楼民居,往往沿着山势走向进行布局,顺应地形,减少开挖土方对地表的破坏,将建筑融合到山地环境之中。这种建造在斜坡山地之上的吊脚楼,以木架空作屋悬居,既不占用苗族赖以生存的极为少量的坝子和谷地,又可增加建筑的使用面积,还可以充分利用自产的竹木材料。由于吊脚脱离了山体本身,因而可以起到防潮和保暖的作用。吊脚楼是一种纯木结构建筑,采用穿斗式结构,不用一钉一铆,梁、柱、板、椽都是由木材加工而成,顶面盖小青瓦或杉皮;建筑用材,除了木材之外,还因地制宜地运用竹、石、泥、茅草、秸杆及牛粪等。在黔南州长顺县敦操乡,苗族吊脚楼的围护体及隔断层均用篾笆折构成,原因是该地区盛产楠竹,人们就地取材,将原生楠竹劈成约2公分宽的竹条,再按所需的尺度编织成席,然后将其固定在木构架上,这种竹壁既经久耐用又色泽古朴。贵阳市的花溪、青岩、石板哨,龙里县谷脚区的千家卡、羊大凯等苗族建筑,除构架及门窗用木材外,垒砌堡坎和基脚用的是石头,板壁、隔壁、瓦等也以石板代之。这些取之于大自然的天然材料决定了整幢房屋的天然色彩,使这种以原质素色为基调的绿色建筑与大自然浑融为一体,是顺应自然的“天人合一”生态观的反映。
(二)水井
在苗乡,水井是一个村寨赖以生存的基础,没有水井的地方就没有村寨。生活在苗岭深处的短裙苗,每一个苗寨都流传一个共同的传说:猎狗披一身白浮萍回来见主人,然后主人随狗找到定居的地方。白浮萍给苗族先祖传递了水源丰富、可以发展生产、适宜人类居住的信息。白浮萍蓬勃葳蕤之地就是生命繁衍之地,就是文明的源头。在贵州山区,苗寨一般建在山坡向阳处,距河谷较远,虽可饮用溪流水,但易干涸,因此,人、畜用水多依赖地下水源,村寨往往建在水井边,村寨规模的大小也要受到水井的限制。水井的出水量(特别是冬季干枯时)能供多少人畜饮用,村寨的规模必定控制在这个范围内。
苗寨的水井多是露天泉眼,水井的位置多在村寨的旁边,四周为参天的古树所笼罩。由于没有人敢砍水井边的古树,甚至连枯枝枯叶也没人敢攀折,因此,苗区的水井一年四季如荫,清泉汩汩流淌。水井的管理方式有两种,一靠制度,二靠神灵的力量。制度的管理主要是通过村规民约来实施水源的使用原则和环保措施。规定都要在村民大会上通过,然后杀鸡喝血,诅咒盟誓,或者写成条款,刻碑于井侧。神灵的管理范围包括水井的卫生、水井边的古树和饮水的礼仪等,管理方式主要是通过诅咒、故事传说和禁忌来约束人们的行动。
(三)保寨树与风景林
在苗乡,每个苗寨附近都无一例外地种植有保寨树与风景林。枫树是苗家的神树,被当地人称为祖母树,其主权属于村寨的神灵,它对村寨有庇佑功能,保佑寨泰民安。据传说,迁徙而来的祖先要想在一个地方定居,必先种下一棵枫树,枫树成活,表示祖先喜欢,人们就可以安家落户,如果不活,则意味着祖宗不同意,那就迁徙他处。村民们除对它进行保护之外,逢年过节还要烧香纸祭祀,不少人甚至将儿女拜寄给古树,希望儿女能得到古树的庇佑而顺利成长。另外,每个村寨的房前屋后都种有树和竹。因此,在山地苗寨,一年四季草木蓊郁,绿荫婆娑。
(四)土地庙
生活在喀斯特石山中的苗族,生活环境较之平原地区要艰难得多,这里石多土少,山坡上的田没有自然水源的浇灌,全靠上天下雨,这些田叫“望天田”。坡地的稻谷单产始终不如平坝地区高,而且劳动强度大。在苗族人看来,作为他们赖以生存基础的土地十分珍贵,也是他们感恩的对象。苗寨的村边有很多土地庙,有的村寨简直遍地是土地庙。土地庙是护卫和照管村寨的地神,有多种形式,如当方土地、坳塘土地、青苗土地、衙前土地、街坊土地、天门土地、桥梁土地、梁山土地等,另外还有河源土地、桃园土地、山神土地等。各地神互不管辖,各司其职。其中当方土地,苗语叫jud denb,每个村寨都有,其功能是保护每个村寨的平安。土地庙的旁边都有古树。苗族人对土地庙持一种敬畏的心态。人们为了祈福,或为了谢恩,或为了诅咒,要在土地庙前摆几个碗,烧一叠纸,点三炷香。
在贵州,苗族的绿色建筑往往是房屋与树木错落相间,一片建筑群的山地下方有河流淌,村寨附近有水井和土地庙,山麓低谷缓坡地带被开垦为良田,水井、土地庙和风景林是公共空间,聚居的人群集体抵御野兽的袭击,树木是与人类相依为命的生存伙伴,每一个苗寨都成了一个诗意栖居的生态空间。
二、诗意栖居的生态观念
林木蓊郁的生态环境与苗族人千百年来“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分不开,它表征了苗族人民的生态智慧和生态自觉。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包括万物同根同源、万物有灵的自然观,以及在自然观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对生态伦理、生态法制、生态禁忌、生态习俗的绿色忧思。
(一)万物同根同源、万物有灵的自然观
古代苗族人认为,凡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自然物与自然现象都是有灵魂的生命存在,如天上的日月星辰、风云雷电、雨雪霜露等,地上的土地、山川、巨石、古木、五谷、六畜、水井、道路、家门、炉灶等。不唯人有灵魂,动物、植物甚至无生物都是有灵之物。苗歌中说“山上的石头是大地之主,人只是梦境中的过客”,这就是说,苗族人并不觉得人类可以完全主宰世界,人类和其他生物物种的生命一样,是自然环境中各种自然物互动运行的产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些灵魂能够影响并控制客观世界中的事件、人的现世生活和来世生活。这就是古代苗族人万物有灵的信仰,它是一切原始宗教发生的基础。
黔东南的《枫木歌》这样记载说:“枫树心心生妹留/妹榜生从树心来/妹榜长大要谈情/她和水泡沫谈情/谈情谈了十二夜/妹榜生下十二蛋/宝蛋得来十二个/一十二个远古宝。”在苗族神话中,枫树蒙冤被砍伐后,从枫树心粉化出蝴蝶,请鸟孵出的十二个古宝即姜央、雷公、龙、虎、蛇、象、牛等12个兄弟。这个神话故事表明,枫树不是神造的,蝴蝶妈妈从枫树中出生,不仅是有生命的蝴蝶能够游方谈恋爱,而且没有生命的水泡也参与了生命创造的过程,因而无机物被看成是有生命的存在形式。由此,创世万物的生命之源蝴蝶妈妈——妹榜妹留成了生命之母。妹榜妹留,是苗族原始神话中创造人类的伟大母神。根据苗语的音译,妹是母亲,榜留是蝴蝶,因此,妹榜妹留即是蝴蝶妈妈的意思。在古老的苗族神话中,妹榜妹留被视为人、兽和神的共同母亲,这就是天地万物起源同“枫木”的渊源关系。古代苗族万物同根同源、万物有灵的生命神话清晰地昭示了山地民族朴素的绿色生态思想。
(二)绿色的生态伦理
古代苗族源于“万物有灵”观念之上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宗崇拜演绎成了绿色的生态伦理。绿色的生态伦理强化了人神兽同根同源的生态观念,将地球上的生命及其生活来源都视为自然的恩赐。每个苗寨的护寨枫树林,就是苗族关于万物生命同源、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文化象征符号。这种“万物有灵”观念使得人们把人生的幸与不幸都归之于自然神灵的恩赐和狂怒,因此,人们对山林、巨石、岩洞、古树等要祈祷和祭祀,由此产生了“雷神”、“风神”、“古树神”、“神山”、“神石”等神灵。夫妇多年不生育要拜巨石、岩洞、古树,小孩身体虚弱也要找岩妈或树爹拜祭。在自然崇拜中,苗族人特别崇拜枫树,牯藏节宰牛时,要用枫树压杠,祖先神灵的木鼓架也要用枫树。以苗族的支系短裙苗为例,短裙苗生活在苗岭深处,其道德观念来自对天地万物的认识以及对祖先神灵的崇拜,在他们看来,天地有眼,万物有灵,祖先有知,而且祖先的灵魂无时无刻不在活着的人的生活中。短裙苗人遵循具有朴素原始宗教观念的道德规范,提倡族人多行善不作恶,因此,在短裙苗社会里,村寨和谐,邻里和睦。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短裙苗崇拜自然,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他们相信山有山的神灵,树有树的生命,在他们向山林索取生产生活资料之前,先要征得山林的同意,如果是采伐,先请巫师作仪式,通过巫师与山林之神对话,征得他们同意方能进山砍树,如果是捕鱼,也要请巫师作拜山拜河仪式,获得同意之后才能行事。故而,在短裙苗生活的地域,处处是青山绿水,是人类疲惫的心灵得以栖息的家园。
(三)绿色的生态制度
千百年来,栖居在贵州高原的苗族人基于万物同源的自然观形成了一整套独特而完整的社会组织制度——鼓社制、议榔制,以及严厉的护林法规——习惯法。
苗族鼓社是由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后代结合起来的群体,同一鼓社的成员,都是同一血缘的亲属关系。鼓社除具有军事、调整婚姻关系和内外关系,以及相互援助和保护等基本职能之外,还组织和发展生产(包括农业、林业狩猎和饲养牲畜等),而领导共同保护鼓山林及村寨环境、管理耕种公田,修建鼓社庙和组织祭鼓节等也是其最基本的几项功能。鼓头由每届鼓社节的本鼓社男性成年成员选举产生,总理全鼓社的共公事务,一般不连任。
议榔,苗语称Gheud Hangb(构榔),是由不同宗族家庭组成的、完全以村寨和地域为基础的地域性组织,它突破了血缘关系的纽带。议榔的最高权力机关是议榔大会,由榔头或德高望重的理老主持,其任务是讨论有关大事,制定榔规榔约。
榔规榔约是一种民间法律。苗族社区主要通过榔规榔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议榔制定的榔规榔约,俗称民族习惯法,它是苗疆社区内的准法律。习惯法由各村寨的理老、寨老制订,并凿石埋岩为证。由于苗族在历史上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所以议榔款约多以口头形式流传,一代代传递和完善。苗族的各级社会组织以信仰为中心形成了一整套生态维护管理的制度,如咸丰五年(1855)兴义县绿荫村的乡规民约记载:“窃思天地之钟灵,诞生贤哲山川之毓秀,代产英豪,是以维岳降神,赖此林域之气所郁结而成也。然山深必因乎水茂,而人杰必赖乎地灵。以此之故,众寨公议,近来因屋后丙山牧放牲畜,苗木因之濯濯,掀开石厂,巍石遂成嶙峋,举目四顾,不甚叹惜。于是,齐集与岑姓面议,办钱十千榀,与众人记为世代×后培植树木。禁止开挖,庶几龙脉丰满人物咸×。倘有不遵,开山破石,罚钱一千二百文;牧牛割草,罚钱六百文,勿谓言之不先矣。”①
自苗族村民中出现掌握汉文化的文人之后,历史上就有了不少用汉文记录榔规榔约的木牌和石碑。特别是自明清以来,贵州天柱苗族民间社会有许多约定俗成的榔规榔约,人们将其刻诸石碑上,以此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行为。天柱民间禁碑的内容十分丰富,大体包括农牧渔业生产禁碑、生态环境禁碑、维护商贸活动与航运秩序禁碑、调解纠纷与维护村寨治安禁碑、保护公共财产禁碑和风水坟山禁碑六个方面。如《永世恩功》碑载:“故栽者培之,郁乎苍苍,而千峰叠嶂罗列于前,不使斧斤伐于其后,永为保护。”许多山林正是在村民的共同保护之下才得以荫蔽成林的。
各村寨利用传统的习惯法有效地维护了民众植树造林的社会环境和积极性。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苗族的巫文化发达,因此,与其他民族相比,苗族村寨在制定榔规榔约的时候多了一道巫文化程序,神性的生态文化通过各种规约和仪式来表达。规约制订出来之后,鼓社头或议榔头将村民们聚集起来,在某个阴森的崖壁下或者古树前,高声朗读全部条款,然后征求大家有无不同的意见或新的补充,如果没有,巫师就开始诅咒。巫师身披红袍,头戴冠冕,手提一只大公鸡,挥舞跳跃一番之后便开始诅咒,咒词是:“此鸡此鸡!此鸡不是非凡鸡,王母娘娘送我的,别人拿去无用处,弟子拿来‘的得的。谁违规犯约,有地无人耕,有路无人走,有灶不冒烟,出门踩蛇,回家见鬼,断子绝孙,永不翻浪……”然后扭断鸡脖,鸡血没入酒碗,大家喝鸡血盟誓。议榔款约一经通过,就成了不成文的法律,上至榔头,下至群众,人人都要遵守,不得违反。
(四)绿色的生态禁忌
禁忌是关于信仰活动、社会行为的某种约束限制观念和做法的总称。它作为人类社会最早的社会规范之一,自产生之日起就与宗教、仪式须臾不可分离。弗洛伊德认为:“禁忌的来源是因为附着在人或鬼身上的一种特殊的神奇力,它们能够利用无生命的物质作为媒介而加以传播。”②禁忌通过仪式这一方式,使制度具有神圣的权威感,由此在人们心里形成约束力和限制力,进而规范人们的行为。
在苗族的观念习俗中,禁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禁忌的产生与苗族先民原始思维中的万物有灵观念以及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等生态伦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和祭祀、感恩一样,禁忌也是将人纳入大自然整体,限制和避免族人冒犯天地神灵而遭到灾祸的行为方式。这些世代相传的禁忌,告诉人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并从心理层面对人们的行为活动进行制约,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崇拜和祭祀是一种主观的对自然的感恩,那么禁忌则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从而使得那些最初缺乏相应自觉的人逐步回到敬畏自然的轨道上来。这种禁忌非常多,如苗族人过节时禁止杀狗和食狗肉,忌打癞蛤蟆,禁射杀燕子,忌深潭打渔超过一定的数量,禁止在村寨周围挖土和砍伐古树,禁止打蝴蝶,禁止砍伐风水树,等等。清水江流域的苗族习惯封山育林,并称这类山林为“禁山”。封山禁林的条款十分具体明了:禁止砍伐林木,禁止打柴割草,禁止放牧牛羊,禁止林地烧灰刨土取肥,禁止放火烧山。凡属“禁山”区,均立有禁碑,标明四至界限,周围树上扎好草标,或挂上涂上鸡血的白纸,以示此山已封禁,众人盟誓,不得有犯。从江岜沙苗族将神林划分为两种类型,即村寨神林和家族坟山神林,并规定:对神林中各种树木一律禁止乱砍乱伐,各个家族中的人自觉义务巡视守护,对私自到神林中乱砍乱伐者,一经抓住,则罚其祭山,并当众向神山道歉,祭山时砍牛的牛肉也逐一分到各家各户,以儆效尤。所有这些禁忌既有祖先崇拜的因子,也包含了对动物感恩的朴素心理,它在一个民族、一个社区中的作用不可低估。禁忌客观上抑制了人们对物质追求无限扩张的欲望,限制了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维护了山水和动植物的神圣性,维持了自然资源的永续性,充分彰显了苗族的生态智慧和生态伦理,对环境保护和维护生态平衡的积极意义不自待言。
(五)绿色的生态习俗
苗族有许多传统的民族节日,其中大规模的节日有“鼓脏节”、“四月八”、“过苗年”、“姊妹节”、“芦笙节”、“跳花节”、“杀鱼节”等。其节日活动往往选择在山清水绿的野外进行,人们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狂欢,力图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节日时间的选取依据是古代先民传承下来的自然天象、气候、物候的变化和生产的节律,节日活动的内容则离不开巫术及祭拜仪式,而巫术和祭拜仪式又源于远古的“万物有灵”观念。
从“人树本是同一心”的生态观念出发,岜沙和锦屏的苗族都有营造“儿女林”的习俗。
贵州从江县的岜沙是个坐落在半山腰上的寨子,由三个大小不一但基本相连的自然村寨组成。村寨全是木结构的倚山而建的吊脚楼,四周是葱翠的山林,有香樟、枫木、马尾松、台湾松、杉树、楠木等,大多是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树,这是被岜沙人视为护佑村寨的神树、风水树,因而被世代保护下来。在小孩出生之时,不论男女,父母长辈都要为其栽上一两片杉树,待婴儿长大成人,杉树也长大成材,儿女的婚姻费用和建房费用就不用愁了。由于过去苗家儿女大多在18岁时成婚,故“儿女林”又被称为“十八年杉”。人死之后,便用生命树作棺材,深埋于地下,不留坟头,不立墓碑,而是栽上新的树苗,因为在苗民看来,死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永恒连接的开始。在生命终结的地方栽上新树,培上新土,其实就是生者与死者、晚辈与长辈的一次灵魂交流,这既是生命的解脱,又是生命的升华。在这个意义上,一棵树就是一个灵魂,那莽莽森林中无数的大树便是无数苗民生命的聚集和再现。岜沙人发现,树被剪枝后会生长得更茂盛,但如果将四周和枝顶的枝桠砍去,树就会枯萎死亡。因此,岜沙男子自幼年就开始蓄发,平时将头四周的毛发剃掉,头顶的毛发则长留不剃,挽成一个发髻,岜沙人把这个发髻叫“户更”,它是岜沙男人最显著、最别致的外在特征。在岜沙苗人看来,其头顶上的头发相当于树冠上的树叶,象征着生命的长盛不衰,这种奇特的发型是苗族古老而朴素的树木崇拜生态观的反映。
苗族万物有灵的自然观、绿色的生态法制、绿色的生态禁忌、绿色的生态习俗构成了诗意栖居的绿色文化。以相信天、地、水、火、木皆有灵魂的自然观为核心,膜拜伟大的自然是苗族民众的信仰文化之心理基础。祭祀最直接的动因在于愉悦山水神灵或祖先的灵魂,祈求风调雨顺、人畜平安。这种基于人与自然万物同根同源的绿色文化,既反映了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和顶礼膜拜,也彰显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和谐共存的生态智慧和生态伦理,是一种对外在宇宙的绿色忧思。
三、苗族生态文化的当代价值
生态文明的缺失导致当代社会陷于严峻的危机。在全球性生态危机和发展困境的时代背景下,汇聚各方力量,共建生态文明,推动绿色发展,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实践证明,实现生态文明光靠科学技术和经济手段是不够的,因为技术并非万能,它不能解决人类生活中的一切问题。长期以来,生态文明理念的构建缺乏来自少数民族的经验和智慧。在新时期构建绿色的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应当将历史长河中不同类型的生态文化都纳入其思考的视野和框架之中,吸取其精华。在此背景下,苗族基于其独特的山地环境而形成的诗意栖居的生态文化,对于当下愈演愈烈的自然生态危机的启迪意义日益彰显。
(一)为优化国土空间、全面促进资源节约提供了重要参照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局”。①对此,苗族惜地如金、依山开拓建筑空间的模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苗族人深居山地,山多平地少,石多土地少,苗人往往在平缓的斜坡上开挖一小片平地作为房屋后部的地基,然后用穿斗式木构架在前部作掉层的吊脚楼,形成半楼半地的吊脚楼。这种吊脚楼房屋在结构、通风、采光、日照、占地等诸多方面,都优越于其他建筑型制,是一种省土、省时、省料而又稳固的房屋结构方式,因而可以把平坦的地方留下来做稻田,不致于占用坝子。其次,吊脚楼采用穿斗式结构,在柱与柱之间穿以短木或枋组成网络,不仅结构稳固,而且使全部杆件处于顺纹抗弯抗压和横纹切断三种受力状态,因而可以达到用小材盖大房的目的。第三,山地环境制约了苗族建筑像平原建筑那样横向的空间延伸,从而塑造了纵向空间的山地吊脚楼民居。吊脚楼造型的纵剖面,由于采用了架空、悬挑、掉层、叠落、错层、附岩、镶嵌、跨越、倚台和分层入口等方法,形成了“占天不占地”、“天平地不平”或“天地均不平”的剖面。第四,苗族的吊脚楼民居内部空间一般分为三层:楼板以下为“地层”,主要是牲畜杂物层;顶棚以上为“楼层”,主要是粮食贮藏层;中间层为居住层。这种有效利用土地的建筑布局,不仅充分考虑到了传统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需求,也考虑到了生态的、历史的、地理的文化要素。
(二)为构建自觉的生态文明理念提供了重要参照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②苗族人敬畏、顺从自然,让生态文化融入人们的生活,以及与自然融为一体、和谐共存的生态智慧,为当下愈演愈烈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提供了一个诗意栖居的参照。
苗族先民葆有千百年传承而来的人与自然万物同源的自然观,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看做具有灵性和感情或与人类有着某种远古血缘关系的生命存在,并以这种万物有灵的信仰为基础,形成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对于天地的崇敬与祭祀,是苗族先民社会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他们通过各种祭祀活动,维系着天地神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将浸染过敬畏、顺从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和谐共存的生态智慧全部融入到苗人的信仰和文化之中,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在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中代代传递下来,并由于长期的历史传承和积淀,历世相沿而成为风尚习俗。这种历世相沿、群居相染而形成的生态习俗,无疑具有巨大的群体凝聚力和激励作用。
锦屏苗族流传着“生活要丰盈,两手抓住林”、“家栽千蔸杉,子孙享荣华”、“家有千株桐,一世不受穷”、“山青水秀,地方兴旺;山穷水尽,地方衰亡”等富于哲理的林谚,以此激励子孙后代重视育林造林,民众由此自觉形成了爱林如宝的生态意识和爱山护林的良好习俗。村民们对于村寨边的风水林、风景林、坟山林都能自觉管理和维护,谁破坏了风水林、风景林、坟山林,谁就触犯了神灵,村民们都不能容忍,无论谁来主持正义都能得到大多数村民的支持。在苗乡,无论谁家山林失火,每家每户都要出动,集体义务扑灭,有时连相邻村寨都主动前来营救。对于失火者,轻则补栽树种,重则罚酒罚肉供全村及相邻村寨食用。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要实现“美丽中国”的梦想,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让大自然拥有更多的修复空间,留下更多良田美宅。生态文明理念的实现必须改变人们对自然生态的认识,提升人们对生态文明理念的觉悟。只有将生态自觉提升到文明理智的更高境界,才能培养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人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
(三)为循环经济提供了重要参照
人们通常认为,循环经济作为挽救高能耗、不可持续工业经济的良方,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其实不然,长期栖居在山地的苗族社区早就盛行循环经济模式。且不说山地农耕社会延续了数千年的“刀耕火种”的模式,贵州苗族的稻鱼循环共生系统就有好几百年的历史。苗族谚语说:“要得庄稼好,家肥不能少/人哄地,地哄人/包谷薅芽,黄豆薅花/田里养鱼,粮鱼两得。”这一谚语形象地反映了苗族水田放鱼的优良传统。
黔东南的锦屏素有“绿色山城”和“木头城”之美誉,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锦屏人住的是木屋,吃的是木饭(以木换粮),花的是木钱,靠的是地地道道的木头经济。”锦屏苗族自清朝以来就开始人工造林,至今已有300余年的历史。民国《贵州通志·风土志》载:“黎平(锦屏县属黎平府)山多载土,树宜杉。土人曰:‘种杉之地必予种麦及包谷一二年,以松土性,欲其易植也。”大面积种植杉林,使林山不致荒秃,常年青山绿水,如书上所载:“自清江以下至茅坪二百里,两岸翼云承日,无隙土,无漏阴。栋梁之材靡不备具。”①锦屏苗族在长期的人工造林实践中,摸索出了独具山地民族特色的的栽杉知识与技能,积累了丰富的养山护林、林粮间作等技术。这种“林粮间作”技术,学界又称之为“混农林生产”或“农林复合经营”,其操作方法在《黔语》中有明确的记载:“种之法,先一二年必树麦,欲其土之疏也。杉历十数寒暑乃有子,枝叶仰者子乃良,撷而蓄之;其罅而坠者,弃之;美其性也。春至,粪土、束刍覆之,媪火炳之,乃始布子,而以枝茎午交蔽之,固其气,不使速达也。稚者日杉秧,长尺咫则移而植之,皆有行列,沃以肥壤,欲其茂也。壮而拳曲,即付剪刈,易以他栽,贵在直也。”②由于民间造林的积极性普遍高涨,民间流传明清时期有关苗族森林保护和木材交易的“林契”多达三十余万份。这些“林契”如今已经成为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于山地环境的混农林生产模式,彰显了山地苗族与自然和谐相处、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生态智慧。牛津大学的中国史专家科大卫(Dawid Faure)教授在实地考察文书原创社区之后指出:“中国苗族混农林文书大量、系统地反映了一个地方民族、经济及社会历史状况,这不仅在中国少有,就是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完全有基础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③
责任编辑:胡颖峰